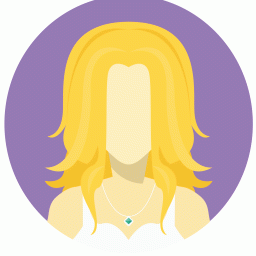“反乌托邦”:至极、至序、至死
时间:2022-10-28 02:02:34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王小波
人类对于乌托邦的渴求和设想并不是从莫尔写就《乌托邦》才开始,与空中花园一样和谐美好的乌托邦相反,《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所描写的都是秩序的世界―秩序之外,什么都不允许存在。
《1984》:2+2=5
“时间一年一年如逝水般流去,不会加快也不会减慢,并没有大的波澜,唯有1984年在人们耳边‘叮咚’一声,留下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来自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小说写了一个可怕的专制社会,电子眼、老大哥,还有‘青年反性同盟’。记得初次看到这本小说是在文化革命当中,社会上一片萧杀,这本书是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在一个小圈子里秘密地传看,当时读书的感觉就像耳边一声惊雷,每个人都惊出一身冷汗:作者简直是鬼使神差,在1948年就预言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分毫不差,鬼斧神工一般。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是上帝(或者魔鬼)曾在他耳旁窃窃私语泄露了天机?
“前两天刚刚读完了村上春树的《1Q84》,三卷本的大部头,仍旧纠缠在一个反面乌托邦的秘密会社的幻象之中,影射了一种原本出于善良意愿却最终陷入恐怖噩梦的现象:一群年轻人为了摆脱资本主义拜金社会的秩序,到深山老林中自耕自食,远离尘世的喧嚣,结果却沦为一个铁血的恐怖组织,草菅人命,杀人如麻。作者为小说取名《1Q84》,显然是在向《1984》致敬,并针对目前的社会现实对《1984》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呼应。”(摘自李银河博客)
现代英语中专门有一个词―“奥威尔式”:如果说一部作品是“奥威尔式”的,就表示这部作品表达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控制和组织的麻木而统一的世界的悲观看法。
对于《1984》,书评人止庵说: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写到什么,尽管那些描写惊心动魄;关键是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1984》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虚幻地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希望时,奥威尔指出,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这本书涉及科学问题,而科学进步的速度和程度是包括奥威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如果只是盯着书中“电幕”一类东西,那么现实中没有“电幕”时,对人的监控就真的不存在了吗?而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把“电幕”完善到了无法察觉和不留任何死角。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乌托邦意识都是历代作家、思想家心中一个难解的情结。在理想国、太阳城乃至桃花源中,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富于秩序、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这些正面乌托邦的意识代表了人类的理想模式与完美追求。作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下的产物,乌托邦的设想和实践虽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每每由于其自身的矛盾,使得最初的美好愿望在事实上发生扭曲。这也正如荷尔德林的名言所指,“总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反面乌托邦作家描述的却是一切都按完美的模式制造出来却偏偏完美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1984》也好,《我们》也好,由于外在制度的极端,人不再成其为人,变成了任中央权力操纵的机器和《动物农庄》里的羊群。
“反乌托邦”:秩序的世界
尼尔•波兹曼在其名作《娱乐至死》中,一开始就提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认为世界最终没有发展成乔治•奥威尔的预想,却越来越向赫胥黎所描绘的方向发展。《娱乐至死》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认为一切公共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政治、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成为了娱乐的附庸,人们的思考能力受制于此,最终娱乐至死。
《美丽新世界》中描绘的社会与其的确有共通之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设定好的机械化的盛世,英国作家赫胥黎将这种后工业社会的景象加以放大。
在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美丽新世界”里,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
这是一个号称快乐的社会,为了获得快乐还有保障措施:比如在婴儿时期就培养人们对书本和鲜花的本能厌恶反应,读书无用,诗歌没有了,历史更是废话;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唆麻的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正是在这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人类虽被分为五个等级,但却从小就以“睡梦教育”的形式被灌输了幸福的概念,从而热爱自己的命运。
他们被设计得厌恶书籍、厌恶艺术、厌恶独处,性滥交、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横行。即使出现最糟的情况,也还有唆麻这一“完美的药物”使人们获得。可以说,“幸福”在这美丽新世界中似乎唾手可得。
诚然,幸福是人类始终追寻的一大终极目标,然而,这样的“被幸福”却不等于甚至往往是有悖于真正的幸福的。就如同波兹曼描绘的“被娱乐”一样,新世界中的幸福成了人为的研究成果,而每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则消失殆尽。在这里被扭曲的不只是幸福的概念,这些新人本身也不同于我们如今定位的自由、正常的人,他们失去了灵魂。
相比较《美丽新世界》中人被技术改造,《1984》则侧重于制度对人的挟制。如果说在前者中描绘的人们是热爱技术而被技术改造的场景,后者中塑造的人则是被制度改造得热爱制度。老大哥在看着你,无法关掉的电幕覆盖着生活每个角落,新话和双重思想则成为人们自身的枷锁,营造出的极权恐怖更为直接。
“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当属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发表于1920年的《我们》。小说的背景被设定在26世纪,“大一统”国的居民在完全机械化的环境下生活:他们穿“统一服”,只能以数字命名,住在玻璃房子里,便于“护卫”监视。他们以合成食物为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那里当然没有婚姻,性生活实行计划制,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房子内的幔帘一小时,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簿,供在票根上签字。这是一个没有“我”,只有“我们”的社会。
扎米亚京是俄国人,但《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如此,由于其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它仍被禁止出版。“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和《美丽新世界》一样,《我们》的故事也描写了朴素、纯粹的人性对一个理性、机械、整齐划一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只是赫胥黎的书在政治目的上少一些,而更加强调技术的作用。
《1984》和《我们》有更多相近之处,比较而言奥威尔对极权社会的构想则更加完善和细致。两个故事同样描述了恐怖的极权统治,而冲破高压的都是男女主角的爱情,最终的结局也都是出卖和人的被改造。“他热爱老大哥。”――正如《1984》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