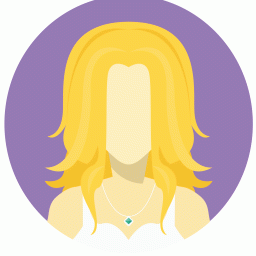天边外的契诃夫
时间:2022-10-27 09:33:04
1904年7月15日,在德国巴登威勒养病的契诃夫垂危。他用德语对医生说:“我要死了。”他拿起一杯香槟酒,带着奇特的微笑看着妻子克尼碧尔:“我好久没喝香槟酒了。”他把酒一饮而尽,向左侧一翻身,永久地沉默了。
契诃夫的灵柩放在一节运牡蛎的火车车厢里,由妻子护送回莫斯科。下葬时,送葬者不超过百人。队伍中,有人打着花哨的领带,谈论着狗的智能和舒适的别墅,很像契诃夫又写了一篇小说。以幽默小说起家,平时好开温和玩笑的作家,获得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
那年1月30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了契诃夫最后一部作品――《樱桃园》。在排练时,契诃夫就不太满意。首演也只取得了一般性的成功,观众的掌声更多的是给予站在台上咳嗽的作家,人们似乎意识到他已时日无多,而对《樱桃园》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
一百年过去了。
在中国,对契诃夫的理解似乎刚刚开始。
理解的难题之一是“喜剧性”。契诃夫的剧本里,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的卑微的生活,有焦虑的无奈的停滞,有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有人失去了一切,有人浪费了一生,有人杀人有人自杀,那为什么它们还是“喜剧”?
高尔基在回忆文章中记载过契诃夫的一件轶事。有位太太,“模仿契诃夫的样子”跟契诃夫谈论生活,她说一切都是灰色的,没有希望,充满苦恼,好像是得了病。契诃夫深信不疑地说:“这是一种病。用拉丁语说,就叫装病。”
这个故事是契诃夫戏剧很好的注脚。他对生活的琐碎煎熬,对人生的无力感有深入的体察,但同时他又能意识到这种原地踏步的无力感中包含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契诃夫不会忘记嘲讽人类这种“装病”的天性。
契诃夫嘲笑一切人,因为他们软弱、自私、虚荣、吝啬、幼稚、世故,贪图安逸、夸夸其谈、百无一用、自暴自弃,他们困在自我的迷宫里,每一个人都徒有梦想,却都因为个人的局限,没能成为自身想象或者期望中的人。
除此以外,契诃夫还是一个在垃圾堆般污浊的生活里也能感受到温暖的作家,他笔下那些慵懒、猥琐的人物,多半有种天真诚挚的性格,散发着温暖的气息。他的剧中人也总是置身于温暖的乡间,烛火、茶炊,琴声、美酒,花园、湖水,落日、晨曦,诉说着美好,也增加着惆怅。这层暖色,模糊了他对剧中人的讽刺,使角色的层次更丰富,使嘲讽变得多义而不确定。性格软弱、不健全的人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生活,难以实现的愿望成就了天边外的梦想。
生活是有病的,作为医生的契诃夫也开不出药方,然而他意识到,梦想永远飘荡在生活之上,属于天空中某个看不见的角落,即使永远不能实现,也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宽慰着受苦的心灵。契诃夫敬重这样的梦想。“幸福来了,它在走过来,走得越来越近,我已经能够听到它的脚步声。而如果我们看不见它,抓不住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别人能看到它的!”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今天重读契诃夫的喜剧,备感震惊。举目四望,竟然发现身边到处是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无数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来来往往,甚至自己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也早被契诃夫剖析过了,这种愉悦、羞愧和恍惚的感受也是微妙难言。只要去阅读,去体味,“永远的契诃夫”就永远地关照着我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