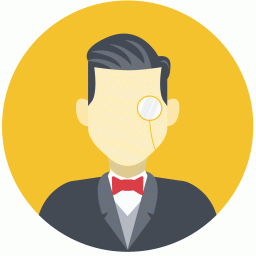音“韵”之议
时间:2022-10-16 05:32:58
纵观近几年“金钟奖”、“文华奖”等国家高级别的民族器乐演奏大赛,应该说我国当今民族器乐演奏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很快的,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非常令人担忧的偏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移植演奏小提琴、钢琴的曲目,似乎曲作者很想在技艺上与之媲美。这从乐器演奏与教学的角度来看,“增益其所不能”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选手在“龙飞凤舞”炫技的同时,演奏规定的传统曲目却显得不知所云、苍白、无奈、丧失民族固有的风格而缺乏表现力……究其原因,这些选手正是没能掌握民族音乐优秀传统中最为宝贵的“韵”。宏观地看,当今民族器乐演奏艺术许多独特的、优秀的传统正在逐渐地丧失。笔者以为,随着信息时代国际文化交流发展,我国民乐享誉世界并引以为自豪的同时,我们应该对自己民族音乐如何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深思,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对“韵”的探索、认知和掌握。
关于“韵”的历史文献记载非常之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音乐艺术、语言艺术中所指的音“韵”(这是本文的论域);其二,人物品藻中所指的“韵”,即所谓的“体韵”、“情韵”、“韵度”、“风韵”等。
“韵”最早被用于音乐艺术领域,是指音乐的音韵。例如汉代蔡邕的《蔡中郎集,外集三・弹琴赋》中的“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于是繁弦即抑,雅韵乃扬”;曹植《白鹤赋》中“聆雅琴之清韵”;晋代陆机《演连珠》写有“赴曲之音,洪细之韵”等,显然都是指古琴音乐的音韵,即音乐演奏中乐音进行和谐的音韵之美。
发端于音乐的“韵”,之后更多地被用于文学的诗歌词赋中,用以字音之间的呼应,即平仄、声调关系的“押韵”而造成语言艺术的韵律之美。
随着音乐演奏中音“韵”之美的历史发展,乐音运动这种和谐之美外化后又形成另一些审美范畴,诸如“意韵”、“神韵”之美,构成了艺术内容美的审美追求之一,也即有“意”、“味”、“境”等意义,这是人们对音乐感性层面的理性审美结果,是音乐的音“韵”之美所带给人们对音乐的遐想和回味(当另文讨论)。这种对“韵”喜爱的审美意识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对中国人的听觉审美习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中华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中,“韵”逐渐成为了我国艺术审美的重要范畴。明陆时雍《诗镜总论》就明确指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晌,无韵则沈;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这说的是“韵”在诗歌创作中的美学重要性。从民族审美心理角度来看,我国人民对音乐的欣赏,也特别要求有韵味。一些戏迷听京戏时,往往着意品评唱腔与胡琴表演中的韵味,到韵味极浓时,会高声喝彩;评论某人演唱、演奏时,常用“有味”与“没味”来衡量其艺术表现的高下。这种味,就诞生于表演主体在二度创作中对乐音及音与音的连接过程中,所做的一些装饰性、弯曲性的变化和力度、速度、虚实、音色等处理所产生的“韵”(一些学者和民间表演艺术家们又称“韵”为“味”、“腔”、“韵腔”、“音腔”、“腔音”、“摇声”、“花音”等,这其实都是从不同侧面对“韵”进行的表述)。
在民族器乐演奏艺术中,一个音、一个乐节、―个乐句有何音律特征?怎样进入?怎样持续?怎样进行与结束?都表现为一定的音过程和音与音之间的连接。对音头、音腹、音尾怎样处理?这在中国音乐中很重要,因为一种艺术现象总是与它所生成和发展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语音丰繁。众所周知,我国各地方戏曲、剧种就约有三百六十多种,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音乐都与其民族语言和方言紧密相关。由于各地语言音调的走向各异,也就形成了纷繁而多样的“声腔”,其“腔”的行“韵”过程也不同。如在方言不同的广东、浙江、湖南、河南、山西、四川。就分别形成了粤剧、越剧、湘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不同声腔的剧种。不同声腔的产生恰恰是由于其方言的字音调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说,一种声腔也就是受一种方言语音影响的结果。普通话有四声,浙江越剧的语音为九声,据说福建语音多达十一声。在声母与韵母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音过程与语意发生同步变化,声调(调值)不同,意义也不同。音过程错了,人们就无法听懂其真正的语意。这类语言就被人们称为“声调语言”,而重音变化与语意发生同步变化的欧美等国的语言,就被人们称为“重音语言”。后者则是:重音错了,就使人听不懂原意。音乐史家们差不多都公认这一点:语言早于音乐,语言也影响音乐。声调语言对于音乐的影响,主要在于旋律进行的音过程方面,重音语言对于音乐的影响主要就在于节奏重音方面。中国声调语言的音过程变化,自然要影响到中国音乐的表情达意即语义学意义,而音乐音调中乐音的装饰、音色、力度、音势的细微变化与布局,则影响着音乐的形式美。
特别是演奏地方色彩浓郁的音乐作品,“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的艺术。方言语音的声调直接影响地方性的民歌、曲艺、戏曲的韵腔风格,这点我们还可以从王光祈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中得到印证:昆曲的音乐旋律走向与其昆山地区的方言字音声调走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见字音调值对声腔的影响之大,不仅影响声腔的旋律走向,也使声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韵味。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许多器乐音乐就是在戏曲、曲艺、民歌等音乐基础上逐渐发展而形成独立的乐种的,其方言声腔很自然地被带到器乐演奏中来,在演奏中的“润腔”方式,如吟、猱、绰、注、滑音、打音、擞音、推拉弦等,都与演唱的“韵”“腔”习惯相符。例如广东音乐的装饰音的速度就比较慢,力度稍弱于旋律骨干音,但与旋律骨干音的力度相去不远,听来花俏、徐缓、委婉、深情;京剧的韵音装饰则速度较陕、所占时值短,而力度较骨干音为弱,不仔细听,几乎不大容易觉察,听来干脆、利落、豪放、热情,如此等等。
我国的地理环境对音乐“腔”、“韵”的影响也很大。如北方冬天气候寒冷,节庆欢愉之际,音乐表演也具有趋冷避寒的功用,因此,音乐在整体上表现为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粗犷豪放的特点。而南方,尤以江南为例,土地富庶,生产方式复杂而精细,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人们交流或表达感情时自然趋于温和,这样也就形成了该地区声腔旋律委婉而平和,音调适中,节奏规整,细腻而柔美的音乐风格,如江南小调、江南丝竹乐等。我国西北高原沟壑迭起,土地贫瘠,劳动、生产方式主要以赶脚、运货、放牧为主,粗放而单调,人们在交流或者抒趣时,也习惯高声而自由的呼喊方式,这就形成了该地区音乐旋律线条起伏大、音调高,自由而直畅的特点。再如,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形成了该地区悠长而深远的独特声腔――长调;奇异而变化多端的江河水,打造出了铿锵有力、激越豪放的号子 声腔――船工号子;跌宕起伏的山脉,灌木丛生的山林,孕育了高亢嘹亮、自由奔放的声腔――山歌。如果仅以南北为限,北方音乐整体上刚劲而热情,南方音乐整体上柔美而委婉;北方的民歌高亢而嘹亮,南方的民歌细腻而缠绵;北方的曲艺顿挫有力,南方的曲艺柔和灵丽;北方的戏曲高昂直率,南方的戏曲优美典雅。总而言之,地域人文的差异,形成了整体上南柔北刚的音乐特点。
语音特征、地域特征、声腔方式自然地沉淀在我们民族器乐音乐中。表演主体要演奏、表现民族器乐音乐的音调特色,把握纯真的音乐风格,达到二度创造艺术的成功,就必须研究地域、语音特征及声腔方式对民族器乐音乐的润腔,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韵”的过程。我们以二胡独奏曲《江南春色》来看音“韵”运用的实际情况。这是一首根据苏南民歌《九连环》的音调为素材的创作曲目,原民歌的演唱要用吴语语系的苏州方言,音乐音调与方言音调结合得非常紧密。应该说,我国民歌戏曲词和音调的这种紧密结合关系恰恰是通过“韵”这一特殊形式来体现的。有了“韵”这一特殊处理,音高与字调就能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不仅使歌唱中声音圆润、流畅、平滑、不间断地横向流动,还能使人们获得传统音乐审美要求“字正腔圆”的美感。俗语说:“愿听苏州人吵架,不听湖北人讲话”。“柔”、“糯”是苏州方言的发音特点,即所谓“吴依细语”,它的发音总带着由上下类似小三度音程的滑腔。如前所述,民歌曲调的进行与方言语调结合得非常紧密,因而《江南春色》的音乐风格柔美舒缓、委婉细腻,级进与小三度音程的进行比较多。这一方面是受地域、语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以五声音阶为旋律骨架的特点。所以mi-sol、sol-mi、la-do、do-la的进行相当普遍。在徐缓的音乐速度中,这种上下小三度的音程,多用滑音来连接(或用同指滑奏,或用异指、垫指滑奏),并且要求这种滑奏非常柔缓委婉。特别是异指滑奏中的垫指滑音,其技法很有江南音乐风格的特色,它增加了音乐进行的连贯性和音与音之间连接的粘性。另外,在音乐进行中丰富的装饰音、弓法上的跨拍弓等手法的运用,都很好地表现了江南音乐灵秀的特色。下面先列出《江南春色》主题的原谱、韵音实际音响谱。
笔者曾在拙著《音乐表演艺术原理与应用》第九章“音乐表演艺术中的虚与实”中说过:“由于每个表演主体的心理积淀不同,在他们各自的眼中的音乐符号虽然一样,但在他们每个人心中升起的音乐则是各异的。”进而言之,演奏者在解读乐谱时有没有相关知识及学养的积累,能否从内心听觉中听到(如上例)风格纯真的实际音响?是为问题的关键。接下来是如何设计运弓运指,请看演奏谱。
我们先比较主题的“原谱”与“韵音实际音响谱”,可以发现,在原谱旋律音的框架上出现了许多“小音”――“韵”,这些“韵”音装饰、润色旋律骨干音使得实际音响丰满而韵味十足,显现出了苏南音乐那柔美而典雅、丰蕴而灵秀的音乐风格。
那么,这些音“韵”是怎样产生的?其依据是什么?
如前所述,是与该音乐所属地域环境、文化样式、语言、声腔相关联的。通过考察,吴地的音乐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为“典雅”与“细柔”。早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这种显著特色的吴文化特征。试看吴地的各种艺术,无论是音乐中的丝竹、昆曲,建筑中的园林、民宅,美术中的绘画、书法,工艺中的刺绣、织锦……无不以精雕细琢为其艺术审美追求的目标。吴地的音乐特色正是含蓄、精致、优美、敦厚而意味隽永。江南水乡造就了吴人的灵巧秀美,大自然确实对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人文方面的原因。吴地人是在长期生产斗争中培养出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的。江南水乡的渔业要求细致复杂的生产操作,水稻生产比大豆、高粱的耕作要精细复杂得多,蚕丝生产更要求严格精巧而细密的工艺操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吴地人十分自然地养成了灵动、聪颖、精巧、复杂的思维习惯。艺术创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它与创作的主体即“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因此,《江南春色》在演奏本质上需要表现出水灵的音色、秀美的音韵、儒雅的情致、刚柔并蓄的格调。
在民族器乐的演奏中,对一个音的音头、音腹、音尾的不同处理,会产生不同形式的“韵”。通过对上例《江南春色》乐音运动中“韵”具体表现形式的探微(见“韵音实际音响谱”),我们可以把“韵”大体分为:音前韵(如上例“韵音音响谱”中第一个音、第二小节第三个音等)、音后韵(第一小节第三个音、第四小节最后一个音等)、音中韵(第六小节第五个音等)和两音间韵(第二小节第一、二个音之间)这四种形式。
这四种形式的“韵”音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音前韵”如广东音乐中的“帽头花”等,它有点类似于“前倚音”,但并不等于“前倚音”,仅是一种以“韵”带“声”、由“韵”人“声”,由虚人实的音乐过程。音前的韵音可以是一个音,可以由几个音共同组成,有点类似于单倚音、复倚音;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出现在句中,这些基本上没有固定的限制,但往往多出现于强拍或者强拍值的那个音上,使音乐呈“软进入”或“弧形进入”,同时也使音乐更具有灵动性,从而呈现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所特有的韵味。
“音后韵”与音前韵相反,是一种以“声”带“韵”、由“声”引“韵”,由实入虚的音过程。“音后韵”在民族民间音乐中较多用在句尾,起到收音、动力性进行、意犹未尽、补充情感的作用等,给听众带来回味,但也有用在句中或其他地方起润色的作用。
“音中韵”不像前两者是在音进行的前后出现“韵”,它是一个音在进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韵,这在草原音乐中尤为明显,其长延音的处理往往运用大、小三度的“tr”在头尾进行装饰。也正是由于蒙古族长调中“音中韵”的大量运用,我们能明确地判断出其音乐风格和特点。“音中韵”可以出现在乐句的句首、句中或句尾,没有固定的界定,仅由乐曲情感和音乐风格所定。
“两音间韵”是指不同音高的两个音在进行过程中不是阶梯式、两点式、由A直接到B的进行,而是一种平滑式、数点式、由A过渡到B的进行而产生出来的音过程。由于这种由A音到B音的运动态势,我们只能在听觉、心理上有明确的感觉,但一般不能用定量记谱法对其音高过程进行记谱。两音间韵的具体形式有多种,根据两音的不同音高关系,做上行或下行的滑动式进行。当然,这种滑奏过程中可能经过几个音也可能经过数个音,这就要具体音乐具体分析了。如秦腔音乐、草原音乐中的两音间韵情况和上例韵谱中不一样,两音(常相隔六度、七度、八度等)中间会经过无数个音,而这些“韵”音只有通过专业的测量仪器才能得知其具体音高,这是凭我们的耳朵所不能准确判断的。
上述四种音“韵”的形态仅是一个初步梳理,在实际民族乐器演奏中,是据乐曲不 同风格而灵活运用的。每一首音乐作品,它限定演奏者必须照谱面演奏的东西,主要是两条:一是旋律走向,二是时值的比例。这些都有着规定下来的“值”,但演奏起来,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演奏者艺术处理的自由――演奏的速度、力度、音色以及对旋律的细节装饰、变化,尤其是“韵”的不同润色方式等而变化。演奏主体一方面要掌握原乐谱上所标示的韵音,更需要根据音乐的情调和风格在“音”里行间适度地加入“韵”音予音乐旋律以润色,使得音响更加丰满、韵味更加浓郁、风格更加纯真。如果把上面的“原谱”与“韵音实际音响谱”的音符均用一条线连接起来,画出两个“曲线图式”进行比对,我们会发现其“微观世界”的差别较大。
我们再说“演奏谱”与“技法符号表解”,这里特别需要注意是一些音“韵”的演奏技法的运用。对于“韵”音,应该说一般演奏者都能演奏,但正如我们对《江南春色》分析的那样,乐曲的江南地方风格的特性要求演奏者在具体技法运用过程中,特别注意掌握其分寸感,重新调节滑音的运指运弓过程,使之平缓柔和,擞音和唤音等装饰润腔性用法也要清丽轻巧。同时这里还特别要强调,无论是加入“韵”音、还是演奏“韵”音,都要恰到好处,既不画蛇添足、油腔滑调,也不贫空干枯、索然乏味,以使自己演奏的“韵”音与乐曲的地域特征、语音特征、声腔方式、音乐风格相契合相统一,绝不能一概使用自已习惯了的韵腔技法,使千曲一味而达不到演奏艺术的本质属性――二度创造的成功。
“韵”体现于音过程之中,它属于“本音”的一部分,和“本音”一同常被看作是一个音,是音头、音腹或音尾上微观层次上的小音。我们可以给“韵”作个比喻:如果把旋律中的“音”比作树枝,“韵”就像是枝上的叶。在实际演奏中,“韵”以隐约、暗示的形态存在于音乐细微的“空间”之中,并不和盘托出,妙在“隐迹立形”,到处都有韵,又到处不见韵的痕迹,存在得自然协调。正如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中所说:“善用意者,使有意如无,隐然不见。造无为有,化有为无,自非神力不能。”演奏中,“韵”如果以“显迹”姿态出现,如同花枝招展,招摇过市,就俗,令人生厌。矫揉造作地追求表面上所谓的“韵”,既破坏了音乐进行整体的“气…势”,也反而无“韵”可谈了。在音乐演奏艺术中,“气”以不惑之势贯穿整体,“韵”以隐约暗示姿态弥漫细部,气韵默契则两全,以“韵”伤“气”则两败。
清人吴太初在其《燕兰小谱》中写道:“蜀伶新生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晤如话。”这里的“工尺咿晤如话”显然说的是乐器演奏对于唱腔的模仿。这也正是人们在民族器乐演奏中把握地方风格韵味的重要根据之一。当下,音乐学院民族乐器演奏专业学生的培养很注重高难度技术技巧的训练,缺乏的是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积累,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俄罗斯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学生,其教学内容中要求学生每年背唱五百首民歌,表演专业的学生每年也要背唱二百首民歌。由此可见,被世界公认的“俄罗斯乐派”是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音乐有着不同的“韵”,我们看历届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最出彩的还是“原生态”组,原因正是其独特的“韵”――音乐“活体”的存在,这是我们民族音乐的灵魂之“根”。另一方面,同一个乐种不同流派的声腔,其“韵”也不同,记得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已故著名民族音乐家甘涛曾说,若把京剧艺术中“四大名旦”的唱腔记谱进行比对,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旋律的差别并不大。而我们听这四个人的演唱明明有着天壤区别。同是“梅派”,如杜近芳与她老师的唱腔,也有着差别,其原因也正是“韵”――音乐“活体”这“微观世界”的差异。在演奏艺术中,“韵”属于具体性音乐思维的范畴,“韵”存在于音乐进行各细节处理之中,就如一个人的某一动作所具有的特征,它是一个人的气质在某一点上的具体表现。一个人的两次演奏,细节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如果不超过一定的“度”,对演奏的整体效果,并不必然导致“质”的差异。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决定局部,局部也决定整体。如果整体演奏中各局部的“韵”的差异明显超过一定的“度”,将导致整体的质变。本文开篇所说有些演奏者演奏规定的传统曲目时显得苍白、无奈而缺乏表现力,就属此况。
通过《江南春色》的例子我们还可认识到,任何乐谱都是作曲家记录自己创作构思的一种符号,应该说这些符号只能是从整体上大概地记录了作曲家的乐思和情怀,很难全面地、准确地记录下在他脑海里升腾的真实音响,尤其是地方风格浓郁的民间音调中的“韵”。就这点来说,笔者以为,我们前几年以巨大的人力财力做的“全国民间音乐集成”以乐谱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音响(音像)的方式存在,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工程,因为它剥离了音乐音响进行中最为精彩、最为闪光的“韵”。因此,在民族器乐演奏艺术中,演奏主体面对乐谱千万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而要在解读作品时去体悟、追索、再现作曲家脑海里升腾的真实音响,并注入自己积极的能动性和再创造性。这当然与演奏者艺术的敏锐性有关。
笔者不排除艺术感觉有天赋的差别,但更要强调艺术教育的作用,艺术感觉主要是后天学习与研究的结果。表演主体要表现出民族音乐纯真的风格,达到二度创造艺术的成功,就必须研究作品音调的地域特征、语音特征、尤其是地方声腔中的“韵”及其过程。要达到体会深、功夫深,就必须锻炼感觉和实地操作,只有艰苦锻炼,才能感觉到别人所不能感觉到的差别,实现别人所不能实现的创造。教师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学生缺乏艺术感觉,对于“韵”的演奏不是不足,就是过火,总也“不到位”、不是那个“份儿”。不要说在手上极有把握地做出非常细微的差别,就是要从听辨中觉察音乐的各种风格“韵”的细微差别都不容易。这就需要在锻炼感觉方面下相当深的功夫,否则,连听都听不出来,更何谈自己去做到它呢?而演奏中的艺术感觉、微观上对于“韵”的把握与表现,却是完全能够从研究与训练中获得、通过锻炼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