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五四”精英人士对中国戏曲的讨伐
时间:2022-10-13 02:3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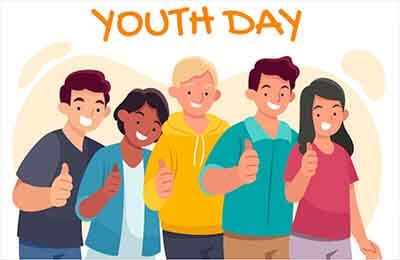
一
江西师大老教授刘世南先生,在看了笔者撰写的《不懂京剧的胡适与不看中医的梁启超》一文后,笑着对笔者说:“胡适那是不懂京剧,他不过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先进罢了……”真是一针见血!张志扬先生在张祥龙撰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封底之言中说的好:“四百年来,西学风潮席卷世界,中国亦在扫荡之列,学人为之正名曰‘启蒙’。然,启蒙如覆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启蒙如殖民,习以西方马首是瞻。”笔者以为,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故而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自卑感,并由民族自卑感而导致了民族的自虐,从而形成了产生洋奴思潮的肥沃土壤。中国的洋奴分为二种:一种是外在形式的,如一些清朝官员、民国官员等,在西方老外(包括东洋日本人)面前直不起腰,说不成话,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而另一种是内在形式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精英人士为代表,这些人士的自卑自虐心理,几乎到了“非全盘西化即保守”的地步(胡适曾毫不讳言道:“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云云)。所谓“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所谓“西洋文化比起中华文明来,实在是先了几步”“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傅斯年语)。鲁迅则在其《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说:“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在所谓“民族之魂”的鲁迅看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也弄到这模样”,以及大批文盲的产生,都是方块汉字的罪过,所以必须“牺牲”汉字,改走“拉丁化”的唯一正确之路,中国才有救。的确,正如鲁迅所言:“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见《古书与古话》一文)而“牺牲”了汉字,中国非但无救,且有四分五裂的亡国之悲!总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人士,视西方文化为无上珍宝,瞧中国本土文化为低贱的臭狗屎;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直不起腰,说不成话,所以只能卑躬屈膝地来一个全盘接受,亦即“全盘西化”或是“全盘俄化”。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戏曲遭受到了“五四”精英人士的猛烈抨击与讨伐。
新文化运动的喉舌—《新青年》杂志,曾不只一次地发表过抨击中国戏曲的文章。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该杂志第5卷第4号成了批判文章的专集。在新文化运动精英人士的眼中,中国戏曲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因此,他们主张以西方“先进”的戏剧来取而代之。胡适认为:“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黄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戏曲的乐曲、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历史的“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周作人则把中国戏曲一概指斥为“非人的文学”,没有丝毫继承的价值(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傅斯年觉得传统戏曲意态动作粗鄙,音乐轻浮,不过是“百纳体”“是下等把戏的遗传”“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在西洋戏剧是人物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所以“不能不”(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钱玄同更为直白地说:“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那么,中国戏曲要“全数扫除,尽情”,否则,“真戏怎样能推行呢?”(载《新青年》第5卷第1号)。谁都知道,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之一。而在鲁迅看来,“中国国粹……等于放屁”(1918年《致钱玄同》)。“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1920年《致宋崇义》)。到了1926年,鲁迅远赴厦门大学执教时,尽管人生地不熟,“语言一字不懂”,在北京待过的他,却因“有京调及胡琴声”,而“令人聆之气闷”(《致许寿裳》)。1934年11月,鲁迅专门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两文。他预言,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之光芒,将很快在中国暗淡下去,所谓“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可见,爱看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鲁迅,对中国戏曲厌恶到了何种程度。海外学人董鼎山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并不是一个地道的京戏迷,老实说,有许多京戏唱词如果事先没有读到,唱的是什么也辨别不出,更不知道什么叫西皮快板或反二簧了。”年轻时董氏住在上海,尽管也曾随家人看过不少京戏,但由于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当时的美国电影是每片必看。“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电影是越看越少,甚至到了逾年不进电影院的程度,可是一逢有看京戏的机会,哪怕是票友客串,也是每场必到。怪不得我的瑞典籍妻子要笑我:‘怎么你年纪越大,越是要做中国人,要吃中国菜,读中国书,看中国戏’……凡是中国的东西,都使我留恋不舍,甚至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而纽约的华裔学术界,“爱好京戏的也不少,他们组织了两个业余京剧团,常常公开表演,聊可解馋”。董氏的女儿是美国籍,但她“最爱看京戏,尽管她一句不懂。因为她毕竟是中国人”(载《艺术世界》1980年第1期)。将鲁迅与董鼎山二人一比照,就可得知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憎恶已深入骨髓了。必须看到,新文化精英人士在猛烈抨击中国戏曲的同时,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的乘机抬头,而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更是把这种倾向推至极端,对中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予以了全盘否定。然而,中国的土地仿佛天生就是孕育传统戏曲艺术的肥田沃土,中国的民众似乎与生俱来就有着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文化基因。正因为如此,源远流长而又独一无二的中国戏曲艺术才会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尽管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人士把中国戏曲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并展开种种搞臭中国戏曲的讨伐,却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好评,所以这种“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便很快破产了。这种情形,与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几次“根本提倡西药,中医中药”之荒唐决议案如出一辙。结果均在百万中医药界人士及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偃旗息鼓了。然而流毒所至,每隔一个时期,便有一些追随者会跳出来,以“语不惊人世不知”的求名作派,“耸动听闻,淆乱人心”(吴宓语)。有矛就会有盾,有打击就会有反抗,有贬低就会有赞扬。正是由于新文化精英人士的“全盘西化”主张,以及对中国戏曲的彻底否定,对西洋戏剧的一味崇拜,导致了一些热爱中国戏曲的人士奋起抵制,如张厚载、宋春舫、齐如山等。张氏首先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为中国戏曲辩解的文章,指出中国戏曲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是“自由时空”“假象会意”,指出戏曲具有“音乐上的价值”,认为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批评胡适等“大抵对于吾国戏曲毫无门径,又受欧美物质文明之感触,遂致因噎废食,创言破坏”(《戏剧改良平议》)。文学家兼音乐理论家刘半农,虽然发表过批判旧戏曲的文章(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强调:“……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但刘氏曾讲过这样的话:“能适用到中国歌唱里来的曲子,应当中国人自己做。”至于在中国音乐中所谓只有主旋律没有和弦多声部的问题,刘氏说:“譬如作画,大红大绿的油画固然很好,聊聊两三笔淡墨水亦未尝不可以绝妙。”“一国有一国特殊的语言,就应当自有其特殊的乐歌与戏曲。”(为《梅兰芳歌曲谱》作序)很值得一提的是,刘半农的胞弟——在“五四”中崛起的杰出教育家、中国民乐作曲家、演奏家刘天华先生在《国乐改进社》发刊词中说:“吾人一方面为黄帝的子孙,不能继续发扬家学,固无以对数千年来之先哲;一方面为人类一份子,仅能食西人造成之果,而不能贡献我先哲造成之果于人类,亦何面目与他国之人握手为俦哉?”他在《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中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他还对当时散布“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傅斯年语)的谬论予以抨击。难能可贵的是,刘天华善于用京剧曲牌的风格作曲,如二胡练习曲四十七,就是运用了京剧西皮慢板而写成。这首短小的练习曲,具有异常优美动听的魅力。1930年,梅兰芳准备赴美国演出,为了便于使外国人对中国戏曲音乐有谱可循,便请刘天华录写在美演出的曲调,如:《天女散花》《木兰从军》《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唱腔,用五线对照工尺译出。刘天华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写出了中国京剧第一部五线谱——《梅兰芳歌曲谱》,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见陈振铎撰著的《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1919年在美国留学的吴宓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1919年12月30日,吴宓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