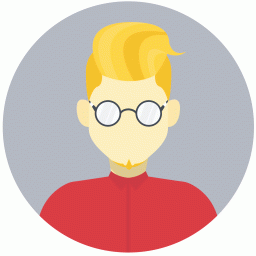一位学徒工被野兽包围了
时间:2022-10-04 08:53:57
天还没亮,灯只好亮着;面前太空旷,反而不知道怎么办。多纳泰罗在创作雕像时,有时会对着雕像大声喊道:“你说话呀,真该死!”五百多年后,一位用文字雕塑的学徒长时间捧着自己的脑袋,于凌晨时分想起这句话。他像一只夜行蛾子,费力寻找着对话的光亮。时光围坐在学徒身边,解衣般礴,坐等学徒来雕塑它。凌晨是没有故乡的。
大病初愈,学徒工每天在跟自己较劲,各项器官被培养得灵敏有加,整个人的注意力反而失去了凝聚力。失去,让人更敏感、牵挂。农历新年的最初时刻,也是凌晨,他收到来自济南、杭州、北京、巴黎几位朋友的问候。他们不知道他差点因内脏失血过多,过不了这个新年。学徒工已经历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二十多岁时被抢救回来的;这一次是他自己醒过来的。
学徒工出生于盛夏的子时,每年夏天他会魂不守舍,像一种注定。夏天闻起来像另一个野性的自己,坐不住,感知能力比手臂上的血脉还要发达,串游四方,行己有耻;看到别人脸上的汗水,嗅觉区会反馈出甘甜和亲切的气息;汽车的轮子,在他眼里是大白鲨的牙齿。这种跨形态的关联一直干扰着他的意识,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不锈的闪光,或者广播频道里永不消失的电波声。也许那应该叫作通感――那是人人拥有的东西。诗人在通感的路途上发现了隐喻,画家嗅到了色彩,多纳泰罗能跟一块石头交流心得。
每天的子时,他会特别清醒,这是另一个注定;子夜的真相,是一头困兽的孤独路程。用文字雕塑是一件苦难的事,身体摧残,灵魂折磨,一遍遍的自我解剖和缝合,困顿和探索;日历上没有节假日,没有工资和工友,精雕细琢换取的报酬也是最贱的(做一天小工起码能得到一百元工资)――那是最低层的工作,最苦难的一拨人;大同创作和利益创作可能跟私企老板差不多,反正是生产适用于时代的消费品――批量产品。
学徒工习惯把完成的毛坯存放起来,由时光去打磨、精工。他害怕被人看到,是真的害怕;这种害怕的上一层害怕是,他不得不将毛坯拿出去,借此卑薄地生存。肤浅地活着,是为了少犯一些生活属性的错误,少添一些肉体的罪孽。他害怕心灵的,远远甚于身体的裸奔――即便在大街上被陌生眼光瞥一下,他都觉得浑身不自然,何况心灵。今年,学徒工在一本杂志上专场裸奔,每一次出场都纠结万分,任何姿势都令他自卑和不安――那不是自信的问题,也不是生存意志的感光度太低,他感觉自己干净的灵魂沾上了世道恶俗的口气。
幸好他没有几个读者,也没有必须的理解需求。
(没有理解,就没有沟通,更不可能同心同德。“同心同德”这个词,是周武王发明的,他跟几路诸侯达成同一个志愿,要讨伐商纣王。它只适用于少数人的现实指向,如果用在成千上万人身上或思想蓝图、道德领域,那是一个笑话,否则就是一种野蛮的精神包围。人同时同等处在困境或危难时刻,才会同心同德。)
理解,是无边沙漠中的一只干瘪水壶。如果真有理解之水,就不太可能会有人为的兽险四伏,也就不易引发战争和离婚,人也更不可能成为世上相互残杀最狠的动物。理解,只是一个概念,类似彼此的精神安慰,它不会比哲学更有实际用途。换一种乐观主义的说法:理解,和学会理解,是人的自身修养之一。
人的精神世界,注定四分五裂。学徒工本人也是四分五裂的,器官各自为王,欺压其余;一颗牙齿的疼痛,就会令日子苍老得迈不动步。凌晨时他捧着脑袋,并不是谁在痛、在发病,而是各个器官太清醒、太活跃。有时房间里的蛾子不是一只,是一群,群蛾乱舞。没有出路的时间,清闲,集中,失去繁忙气息的诱惑。他上午起床时,通常会通感到一地蛾子的英灵,如此凄凉。这种气息会在一天中被无私地继承和延续。
一个人的分裂,也许跟所处高度有关,也可能是局部的蒙蔽。
所有的蒙蔽来源于自身的邪恶。
学徒工的邪恶,来源于身体的某种属性。比如他容易以貌取人,重视外人眼神里的品质、嘴角的性情、举手投足的教养……在人性的海岸线上,潮起潮落,皆有心律可循。即使每个时代也有其不可掩饰的邪恶。中世纪欧洲的人们日渐完善着生活上的细节,信仰上也被某种宗教“同心同德”了,心自生邪,反而认为之美隐藏着异教的思想,他们在雕塑创作上断裂了古希腊的人体艺术美德。学徒工所在的民族更是经历过多次重大的文明之根的断裂,秦、元、民国、“”……每一次断裂的恶果会延续好几代人,只能弥补,永远无法恢复如初(就像学徒工失血过后的内脏);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远远落后。唤醒或发现某种美,需要某些人的无邪和无私(那种效果永远滞后于所处的时代,除非那个时代也相对的无邪)。无邪,是个复杂的词;重点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就是不同的“邪”。在儿童的眼里,大人是邪的。多纳泰罗大概在与石头的对话中,排除了俗世的邪,也摆脱了宗教专制和哥特式形式主义的束缚,找到了独具活力的个人主义艺术手法;他在跟雕塑对象的心灵通感中,继承和连接了古典雕塑的根脉。
学徒工会对着多纳泰罗的作品长时间发呆,怀想。一个人知道得越多,越容易撒谎。就譬如多纳泰罗把基督先知塑造成容貌丑陋却气质高尚的《南瓜头》形象,真人大小般立在教堂的钟楼。先知没有具体风格,或者既定的教条形象。艺术的撒谎,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事物不会论说道德,存在即是;创造事物的人是有道德的,不能因此说创造出来的事物是无道德的啊。世人只缘听懂哲人一半的话、抽象地获取,或者迎合自身的蒙蔽,才有一茬茬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的相互仿学和讹传。所有先贤的一系列思想布设,是建立在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上,僵硬地搬抄他们的论据或论点,都是可笑的。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法无常法,常法无法――
行事的方式和度向,需要想象。想象会改变人和时代的生活、精神方式,没有比这更强大的了。如果是基于集体的想象,它倾向于谋害和占领;个人的想象又总是倾向于得失。幸好(或者是不幸)想象有潜伏期,它在现实生活这个稳定剂的作用下,会变性,会淡化,直至变成模塑的生活流程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它适用于极大多数人,会成为一类梦,被睡眠中的大脑皮层偶尔浮现上来。
学徒工最初的想象,一个也没成真。他在梦里守护着。梦里,学徒工会以多种方式飞翔,会做后空翻,会飙高音,会跟飞禽走兽对话……直到现在,他还做着跟二十年前差不多内容的梦。另外,他总是梦到自己在通往火车站的进站口的线路上,节外生枝,最后错过通勤车;也会梦见被野兽包围。
梦,跟现实和想象也有着承继的关系。最近他接连梦见一只蛾子,翅长无朋,在他面前炫耀。蛾子若即若离。那种蛾子大概叫帝王蛾。帝王蛾从幼虫期那个极其狭小的洞口拼命挤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周身血液在这个艰苦卓绝的洞口挤压出来后,才会扩充到双翼,发育成熟,帝王蛾才能由此获得新生,振翅飞行。大多数幼虫在这个洞口挣扎过程中力衰而亡。如果那个生命洞口被人为弄大,帝王蛾缺乏经受身心的苦难而轻易出了洞口,翅膀缺乏充血和成长的磨炼,便失去了飞翔的功能,只能拖着一双长长的翅膀在地上可笑地爬行。
能自由飞翔的帝王蛾,是少数。
“好了,想象也需要磨砺。”有一天,学徒工不耐烦地对自己说。他同时叹了口气说:“尽管想象本身就是磨砺。”
想象是出卖自我的过程。活着也是出卖自我的过程,出卖纯真、天性、青春,以及梦想和尊严;等美好的东西出卖得差不多了,才开始回忆。回忆的也大体是蒙蔽着的过去,以及倾向于自身的价值观。譬如层出不穷的名人们,他们的回忆里肯定不会有出卖父母的可有可无的教养、到处宣扬自身的无知和这些内容。
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堆见不得人的恶臭之事。
《大西洋月刊》猜测说,中国人内心强大起来起码还需要经过两代人。他不这么认为,这跟时间没必然的关系。他认为内心强大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有教养、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在艺术不成为艺术、文化庸俗化的年代,估计有着一大批学徒工不仅内心孤独,更主要是环境和生存的孤独,体会不到像1905年巴黎秋天沙龙画展上的“多纳泰罗被野兽包围了”的前沿艺术况味,看到的是真正野蛮人事和兽性之道;现世的情况是,人越是无教养、越是不要脸,越容易成功。
学徒工从来不介意生活中的孤独。如果环境容许,他更愿意一个人在凌晨静静打开,自然(这种感觉,只在一个叫南塘的地方体验过两三年),在静默中度过下半辈子。他的孤独感,是在他独处时找不到对话的亮光时才泛滥上来,这种情绪被白天继承,甚至是鞭策,每天铩羽而归。他身不由己一次次搬家,却再也找不回那种安静的生活和对话的时间;命比天大,命在限止他。学徒工的祖籍地、出生地、成长地都不在同一个地理名字上。这大概是另一种注定,注定要在精神和现实两个故乡同步纠结。
年纪越大越趋向平实,奇异的东西被时光冲刷圆润了,少了惊心动魄的邀请。这对学徒工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他可以相对平静地面对周围的咆啸和狰狞,把想象留给自己。人在凌晨,蛾在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