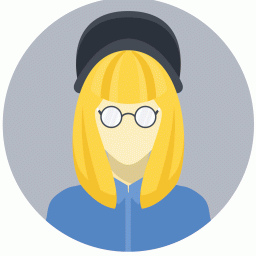我们还能期待更伟大的文艺吗?
时间:2022-10-02 03:24:46

电影《一九四二》的结尾,老东家范殿元搀起跪在母亲尸体旁的小女孩,白茫茫的大地上饿殍遍野,一老一少艰难地往回走,向镜头深处走去,仿佛沉重的苦难永远不得终止。歷史的真实是,3年以后,恰是作为背景的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让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7年以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国家诞生了。
现如今,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史诗题材文艺作品的自我沦丧。比如在电影《白鹿原》中,“皇帝没了”构成一个宏大歷史叙事的开篇,可是演着演着,全剧却改变了格调,如果说小说《白鹿原》还秉持了某种宏大叙事的冲动,并且响应了20世纪90年代“民国热”的风尚,有着讲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现代歷史故事的冲动,那么,改编后的电影就彻底变成了围绕一个心酸女人的艰辛歷程而展开的市民剧;再比如《一九四二》的开篇,地主少东家意欲对前来借粮的花枝(徐帆饰)不轨,灾害发生之际,地主东家不忘交待把细软送到城里。中国的近现代史原本正是从这些细节和关键的歷史时刻伸展开的——“皇帝没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进入口岸资本主义时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本来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士绅阶层迅速地土豪劣绅化,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被严重破坏,旧的乡村共同体分崩离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人民苦不堪言,这是中国革命正当性的逻辑起点,然而在这些公映的电影中,令人失望的是,内涵丰富的歷史时间转瞬就被抽象为一般的物理时间,苦难本身被抽象化为感官层面的痛苦,所有的诉苦和反思也脱离了它具体的歷史语境,迅速扁平化,歷史和苦难的讲述不再具有史诗性,用以承担起塑造共同体的责任,而是沦为观众自我投射的消费品,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平庸姿态。
所以果不其然,很快有人追问,20年以后的饥饿,要怎么算账呢?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歷史更真实”,文艺从来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的一种把握,可以看做一种回应,黑格尔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理想比现实更真实”。以为苦难的“真实”在于感官和知觉上的细致写实,那恰恰是最虚假的。
这正是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对于左拉自然主义的批评。所谓严肃地记录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并不是将痛苦和鲜血淋漓的伤口扒开,再展示一次就足够了,“诉苦”难道不一直都是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的一部分吗?但是在我们传统的文艺作品中,“诉苦”本身却并不依赖于感官上的刺激,不依赖于投入几千万或者几个亿来做好细节的特效,而是深知苦难的反思“在其真中”乃是对于造成创伤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揭露和认识。所以,1942年的苦难不过是前工业化社会常见的天灾,民国政府一方面根本无力实现中国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无法重新整合、组织中国的基层社会,换句话说,即便民国政府手中有粮且有心救灾,面对这样大规模的饥荒和骚乱,恐怕也无能为力。
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苦难的原因就复杂得多,温铁军在他的新书《八次危机》中,详细地解答了1958年开始的“自力更生”的路线转折的原因。根据今天的常识,这仍然被理解和贬斥为极左路线、折腾、激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灾”。温铁军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工业化路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即由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然而,一旦出于不能满足苏联的要求而失去了苏联的投资,在资本积累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工业化后续资本投入将趋零。从世界歷史上看,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宗主国停止投资后,都会出现经济崩溃、政治体系崩塌、社会动乱乃至国家分裂,种族屠杀,对于中苏关系来说,因为涉及到与独立等问题,并不存在妥协和商议的余地,因此中国必须寻找一条不同的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道路。要注意一点,这里并不是要否认这段苦难,而恰恰是要牢记,这段苦难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嵌入在我们共同体的歷史整体中,因而我们无法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方式去同情或怜悯。这里不仅是在说,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且在权力意志的意义上,中国仍然是自己的“主人”。
把苦难从真实的歷史语境里抽离,从我们承受的命运和共同的歷史与文化记忆中抽象出来,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史诗或者悲剧的情怀了,毋宁说,这是文艺在抛弃本来属于自己的伟大一面。
我的一位老师曾受邀去台湾讲学半年,其间恰逢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多年以来,台湾经济状况不佳,社会问题层出,基础设施老化,地区间竞争力也在持续下降,虽然怨声载道,但台湾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选举”制度倒依旧颇为自豪,若说到形式上,确实比美国选举更直接民主一些,每逢大大小小选举,蓝绿营都争个你死我活,热闹非凡。我的老师虽然并不真关心闹哄哄的形式民主,但对于选举过程中政党上街拉选票,群众参与等方式却格外留神关注了一下。回来以后,他跟我们说,虽然民主在台湾很无趣,但其中毕竟内含了些真问题,因为选举意味着政党毕竟必须同群众发生某种联系,说服以及动员群众,于是政党必须动用它所能动用的一切资源,包括文化资源。当绿营拉选票的时候,他们基本会在各种场合用闽南语天后江蕙的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显示自身本土的、在地的政治身份;那么呢?会选择什么不同的文化资源来表达自身的政治?
事实上,也选择了江蕙,而且是主动出击。江蕙更因歌曲《家后》被选中当竞选歌曲而备遭亲绿人士指责,她在博客上则澄清称,《家后》的版权属于前公司,所以自己无权过问。江蕙还称另一首歌《甲你揽紧紧》也曾有人想拿去当做竞选歌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文化政治不会撒谎,如果说在选举政治中,还存在着可以躲藏和欺骗的东西,存在着妥协和虚与委蛇,那么在文化政治中,政治诉求中最高的那部分,政治的全部理想和敌友之辨反而最显白地暴露出来。如果说蓝绿营在选择文化资源来讲述自身时缺乏想象力,那么毋宁说这首先来自于政治想象力和可能性的匮乏。
在某种程度上,危机对于拥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来说是同样的,制度、自由民主或者市场经济,如果最终不能落实到生活政治的层面,安排每个人寻求更好的生活,并且找到“形式”来表达自己,那么在一个“在民”已经被确立为基本原则的现代世界,它也无从实现自身。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一边鼓吹“纯文学”,“让艺术回到艺术自身”,以期解放小资产阶级每个个体的褶皱而纤细的灵魂,一边面对大众又丝毫没有文化资源可供动用;不能一边在《王的盛宴》里说项羽身上发现民主,一边又指责多数人看不懂自己高深的电影叙事技巧。反过来,对于左派而言更是如此吧,并没有理由怀疑今天许多人仍是心怀真诚去唱红歌,问题是所有的红歌都是过去创作的,为什么今天创作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红歌了呢?左翼知识分子又岂能在理论论战中变得越来越精英化?
艺术倘若要避免这样一种结局和命运——成为人们卧室中的摆设或者休憩前点缀自己心灵的小点心,就必须理解自身在文化政治上的内涵。
无论是前文提到的电影、音乐或是文学,“去政治化”了的扁平的文艺,都在强调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重要性。这样的艺术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产物,因此纯粹的文艺理想背后站着的,实际上是现代性政治。无论自觉与否,理解政治、想象政治的可能性并赋予之形式,才是文艺伟大的根基。
艺术沉溺在“小”格局的私人想象力领域,却失去了更要紧的文化政治的想象力。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尤其随着“八五新潮”的开始,中国文艺界展开了一场所谓的“拨乱反正”,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其诉求就是要让文艺回归文艺本身,大力提倡“纯文艺”,要求文艺的“去政治化”,强调纯粹的形式主义美学理想和“无用之用”。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纯文艺”的理想却逐渐遭到诟病,把人的自律性和规定性,从实际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大时代中,从中国所身处和融入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抽象出来,而去空谈个体的自由和解放、想象力和美,这在道德上就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
如此说来,在今天的文艺界,“批评”或者说“理论”,似乎走到了创作的前面,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我更熟悉的文学领域而言,那些曾经最活跃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者,今天都成了最具理论前瞻性的学术人。汪晖写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兴起》;张旭东写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韩毓海从《五百年来谁著史》一路写到《马克思的事业》;蔡翔写出了《革命/叙事》;罗岗写出了《人民至上》……由于文学本身无法磨灭的政治性,“批评”或“理论”对此也许更为敏感一些,并更能理解文艺要走出狭小的空间和格局的重要性。
那么今天我们还能想象更伟大的文艺创作吗?让我们略微绕远些。美国《联邦党人文集》,原本是刊登在报纸上用以说服民众接受“联邦制”的,因此主要是在政治科学的层面上,围绕着“联邦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来展开的,以证明它更能保护民众的自由、利益和幸福。但美国立法者们太清楚政治共同体仅依赖于此是无法持存的,当阐述到“美国例外论”这一关键的问题时,政治神学的原则就出现了:“思想虔诚的人不可能不看出这又是上帝在革命的严重阶段时常明显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救之手。”这里讲得最清楚不过的是,政治,最终仰赖于牺牲精神与神学,仰赖于能触及每个共同体成员灵魂的东西,任何政治的上层大厦,都需要搭建在这一基础之上。
倘若我们要期待更伟大的文艺,那么文艺工作者也必须将自己的目光向下、向着芸芸众生延伸开去,才能认清自身最坚固的政治性根基,就像说的,改变自己的感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因为政治并不是别的什么,恰恰就是每个人内心的文化认同,对于何为善好,以及更美好生活的共同理解、想象和追求。也许在一个现代社会,文艺可能恰恰在其最左翼的探索中恢复了某种古典的理解——“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