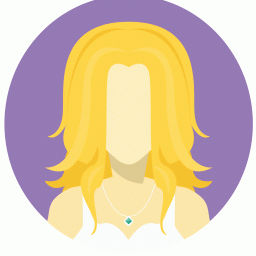芭蕾舞者:从飞蛾到天鹅
时间:2022-10-02 07:14:30

2011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黑天鹅》,犹如一面练功镜反射出芭蕾舞者鲜为人知的隐痛:对于完美的盲目追求,为获得黑白天鹅角色而栽赃陷害、明争暗斗,以及少不更事的少女所遭遇的犯。
主人公妮娜在饱受身心折磨后,产生幻觉――“黑天鹅”的羽毛,在她的意念里破肉而出。代表自己的“白天鹅”,随着谢幕慢慢死去。
现实的芭蕾舞台中央,也永远只有一只白天鹅。为了破茧成蝶,芭蕾舞演员们也会像妮娜一样选择飞蛾扑火吗?
不公平,早在大幕拉开前!
领舞演员胡甜甜,身高一直是最困扰她的问题,老师曾告诉她,只要再长4~5厘米,就能跳主演。为此,她吃了两年增高药。
群舞演员李怡燃,易发胖体质,为控制体重,长期节食减肥,后果是:20多岁的女孩已停经。“干吗要这么糟蹋自己,除了一身病,我得到了什么?”这是她的哭诉。
领舞演员刘爽,爱芭蕾,但不被芭蕾爱。对他而言,芭蕾的残酷就在于,身体条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己不能演王子。
芭蕾舞对舞者的身体要求非常苛刻。一方面,身体的韧性、柔软度、弹跳力要好;另一方面,对每个部位都有要求:头小,脖子细长,脚背有弧度,身体比例好。而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少之又少。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为例,每年的招生考试,老师不仅要目测,还要用尺子准确丈量身材的比例,淘汰率极高。即使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生,也很难有二十个理想的苗子。在经过7年的学习后,他们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二可以毕业,仅3~5人能进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在整个舞者生涯中,身体条件都是影响他们命运的决定因素。
不公平又如何?
自己是自己的魔法师!
――傅姝 (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的自身条件不算好,个子不高,直接影响了身体线条的美感,这很致命。在中国的芭蕾舞演员中,女演员的完美身高是165厘米,男演员要180厘米以上,可我从舞蹈学校毕业时才160厘米。校长劝我留校,因为即便进入舞蹈团,以我的身高也当不了主要演员。舞蹈团有不成文的规定,主演必须个头偏高,这样才能从群舞中凸显出来。但我还是坚持去了,已经学了七年,就算当不了主演,能上台就好。
我相信只要加倍努力,靠舞技和表演能力也能弥补自身的缺憾。事实的确如此,我用五年时间跳到主演,当然,这背后的付出只有自己知道。
除了身高,体重也是演员的悬顶之剑,一旦增重,一两天内必须减掉。我属于易胖体质,尤其在生理期时,喝凉水都能变胖。对于平常人,重两斤也许不会很明显,但芭蕾舞演员的增重是按两计算的。胖了几两,上台时你身体的线条就已经受影响,芭蕾舞演员都是皮包骨的,167厘米的个头,体重可能仅80斤左右。
瘦不意味不健康,控制体重也不是就要节食。合理的控制方法是,在活动量较少时,相应少吃,胖的时候,靠增大运动量、大量排汗减肥。平时的饮食没有特别规定,我现在早餐就一片面包;中餐吃水果、酸奶或面包,不会吃带油水的东西。因为中午只有一小时休息,吃饱了会有困感,而且腹部会有负担,动作幅度大时,甚至有反胃的感觉。晚餐要吃饱,补充一天的体能消耗,夜宵是决不能吃的。平常人们说健康的饮食是:早餐吃好,中餐吃饱,晚餐吃少。我们为了跳舞要完全违背健康规律。
还是不公平,机遇落在了谁的头上?
首席主要演员孙欣,宁可待在机会较多的广州芭蕾舞团,也不愿去声名在外的国家芭蕾舞团。对她来说,在有限的艺术表演生涯里,尽可能争取上台的机会,才是唯一的选择。
首席主要演员张剑,每一次排新戏都希望能做女主角,但最终发现,跳好每一部戏着实不可能,芭蕾舞者要面对太多不可控因素:随时会来的伤病,随时会走的机会。
普通人的职业寿命大概是35~40年,而在芭蕾这一行,除去学习的时间,真正的职业年限不超过15年。通常情况下,一个芭蕾舞演员需要跳三年群舞、三年领舞、三年独舞后,倘若表现极为出色,才有可能升至主演。可当你终于找到跳芭蕾舞的感觉时,你的职业生涯也快结束了。机遇,就是芭蕾舞演员的金苹果。它会砸在谁的头上?
等不及机遇,就去争
――梁菲(香港芭蕾舞团演员)
1997年初,我刚进香港芭蕾舞团不久,团里打算再排芭蕾舞经典剧作《天鹅湖》。那时我还是群舞演员,但这部剧中的黑白天鹅是我一直想演的角色。我就“自告奋勇”,跑到港芭艺术总监办公室,直接对谢杰斐总监说:我喜欢《天鹅湖》,想演奥吉塔,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结果就让总监笑话了:你只是刚进团的新演员,在你前面还有那么多比你资深的舞蹈演员,怎么都轮不到你演奥吉塔啊。
的确,世界各地芭蕾舞团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演员必须从群舞跳起。这一条,很难逾越。但我始终都抗拒不了奥吉塔的诱惑,一有空就去主演的练功房偷师。当时的我只想圆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根本不在乎别人的不解与嘲笑。
结果,到《天鹅湖》的排练后期,艺术总监终于发现了我,看了我的表演后,就决定让我在学校教育场的演出中饰演白天鹅。后来又破例让我在3月的正式演出中饰演全剧黑白天鹅。就因为这次演出,我在港芭不到一年便从群舞演员升到了领舞演员。
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朱妍(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演员)
2005年,我们团排演《卡门》,请了芭蕾舞大师罗兰•佩蒂作指导。外国人选角,不会考虑你是群舞演员还是主演,大家就一起跳一次,由他从中选出他觉得合适的演员,所以这仅有一次的表演特别重要。
当时,团里原定的主角是我,但就在还有三小时要表演给老头(指罗兰,下同)看时,我扭伤了脚。团领导带我去医院拍片――骨裂,当晚肯定跳不了。领导当即决定让孟宁宁替代我完成主演,她上台跳的时候,我就在侧幕边看,心里五味杂陈。作为主演,我已经习惯了被关注,当所有人忽然开始关注别人时,那种失落真的挺可怕我努力了,但现实中很多事不由你控制。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休息调整了几天,我听说老头要再看一场演出,突然觉得还有机会,就赶紧带伤去练功房准备。晚上我表演的时候,伤痛全抛在脑外,能用的力全用上了。哪知,那天罗兰临时有事,根本没来。我是一场空欢喜。
《卡门》的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女主角是张剑,我和孟宁宁备选。排练中,孟宁宁最先放弃,改跳《卡门》的女强盗。而罗兰基本没看我几眼。
编排完全剧,老头就回国了,留下我们自己练。等他再回来,就是检阅我们表现的时候。罗兰回来的第一天,先看了张剑表演的卡门。刚跳完,老头的助理就冲上台质问:卡门在哪儿?显然罗兰不满意,临时决定下午看备选的表演,也就是我。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看完我的表演,老头竟然说“非常非常棒”。 第二天剧组就贴出了新的表演名单,我成为女主角,张剑变为替补。
这就是芭蕾无情的地方,它若即若离,有时候你觉得可以控制它,但有时,你越想那么做越达不到。那天张剑状态不是很好,罗兰就觉得她不合适。但假如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出现了不到位的表演,一定也会像张剑一样被毫不犹豫地换掉。《卡门》选男主角就出现这种情况。先是由团里同事担任主角,罗兰不满意,回国后带来一位美国的舞者替掉了我们的演员。但就在彩排阶段,老头突然觉得我们团的余波更合适。结果,美国演员在临上台时被告知不用他了。我们当时觉得他特可怜,大老远从美国来,练了那么久不能上台。大家看着他坚持上妆,穿好演出服,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一旁拉筋,希望能有备演的机会。但罗兰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个安慰都没有。
伤痛――那些躲不开的
独舞演员腾树源,十个脚趾全部被僵硬的足尖鞋磨得淤青红肿。有时,晚上睡觉一蹬脚,指甲盖就翻掉了,直到最后十个脚趾全部没有指甲。她每天要先用皮筋把脚趾绑紧,让它血液不通,没了痛感才能跳舞。对她们来说,只要脚没崴着,没残,都得继续跳。
领舞演员刘洋,曾经脚伤疼痛难忍,在母亲的陪同下去医院,被医生告知将来可能会坐轮椅。母女二人一路哭着回家,母亲说:不跳舞了,改别的行吗?她说:不行,不跳舞,我就去跳楼,我去死。
主要演员冯英,因跳芭蕾舞,肩部变形,胯部变形,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穿裤子时,总是一条裤腿被自己踩得很脏。
伤痛是芭蕾舞演员职业生涯中躲不过的梦魇,如饮鸩止渴。美丽的芭蕾花朵,需要无数年轻的生命用肉体去浇灌。美之极致,飞蛾扑火,只求绚烂……
前半生立脚尖,后半生“坐轮椅”
――黄怡(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从上海芭蕾舞学校毕业时,膝盖软骨磨损,只能走平路,没法上台阶。2000年,从上海芭蕾舞团调到广州芭蕾舞团,还是团里的大夫带我去广州体院、二沙岛中医院做理疗,这大概用了四年时间才慢慢好。
现在身上最严重的伤是腰椎间盘突出。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桃李杯”芭蕾舞大赛,临行的前一天,突然趴在床上动不了了,那是第一次发现腰有问题。后来,我把腰部的X光片拿给医生看,医生问这片子的人呢?我说我就是,医生说你还能站在这里啊,这片子的主人应该是坐轮椅的。医生让准备手术,可我跳舞不能停啊,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出了问题就靠打封闭来解决。
到去年,我的脚也出问题了。腿上这条韧带,打过八九次封闭,已经脆了,一使劲就可能撕裂,后来只能静养。今年我做了微创手术,医生用小刀片戳进40几刀,把韧带和骨头的粘连刮开,这才好点。我们这些跳舞的,老了可能就走不动了,五六十岁都得拄拐杖坐轮椅。
可以痛,但不能不美
――孙欣(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这双脚,光封闭就打了十几次,明明知道打了封闭后韧带或肌肉就越来越脆,但你等着上台,想要脚伤短时间内恢复,就只能打针。记得第一次打的时候,可以管三个月不痛,后来就慢慢的只能一个月不痛,一个星期不痛,最后效果就越来越差。刚打完这针不久又痛,痛得比之前还厉害。前年,我再去找医生,他不给打了,他说已经不能再打了。
伤是好不了的,它只能越来越严重,可只要你想跳就得坚持,但有时痛得特别厉害,没法跳。我不想让别人说你状态不好,就开始自己吃止痛药。连续吃了近三年,一直吃到胃出血,溃疡,进医院。医生才知道我是每天都在吃止痛药,演出前甚至要加大药量。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在每天晚上12点睡前吃药,那时胃里早已消化空,一吃药就刺激胃。但只有睡前吃,才能保证晚上休息好,第二天上午能正常排练。
谢幕――走下舞台,生活继续
首席主要演员傅姝,今年31岁,希望自己还能多跳几年,等不能跳了就去当舞蹈老师。
首席主要演员黄怡,对于“不跳了能干什么”一脸茫然。郁闷的是,国家艺术演员同国家运动员待遇差别为何那么大!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因伤退团后,哭了五年,始终舍不得离开芭蕾,最后进入芭蕾舞团从事行政,直到成为团长。
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舞台中心,甚至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舞台上,无论在舞台上赢得了多少掌声,谢幕后的寂寥只能一个人承受。
把芭蕾种在心里
――王志伟(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有个朋友在惠州开舞蹈学校,有五六百个学生,一个月的收入颇为可观,远不是现在的我能比的。他也曾经是广芭(广州芭蕾舞团)的演员,和我一样,当时都是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平时一起上课,一起排练,暗地里两个人还互相较劲,谁都不愿落后。很难说这样的选择谁对谁错,于我而言,我在舞台上得到的东西,是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不过,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离开,是个永恒的话题。到今天,我跳芭蕾舞已经20年。从12岁开始为期六年的专业芭蕾舞学习,至今,一起入学的12名男生只剩下我。我没有走,是因为相信它能成就我对舞蹈,对美的追求。
在广芭的13年,目睹了很多同事因伤病,或怀疑自己能否获得好机遇,而纷纷离开。而对于我们这些坚持下来的人,剧团也会为我们考虑好后路,就是让我好好跳,等将来真正退役了,可以把我转为事业编制,在团里当个芭蕾教练。
我跟妻子在芭蕾舞台上跳了十几年,一起面临伤痛、挫败,也将一起面对跳不动的那一天。就像妻子说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出路,尽管这么多年,我们很少接触社会,尽管从小到大除了跳舞,我们别无所长,但我们依然相信,就算有一天,一切要从头开始,我们一样能做得很好。
(感谢广州芭蕾舞团提供采访便利)
上一篇:《赢未来》杂志携手各大高校,集合至top精英,打... 下一篇:对话“未来中国”助学联盟总干事王红:智力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