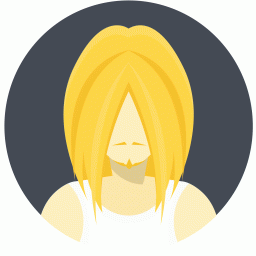尝一口20年影像史
时间:2022-09-07 02:01:41

9月,陈劭雄大剌剌地在新浪微博上批判了民生现代美术馆的策展方式未与他沟通完满,之后便单方面表示退出本次“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展。
转发与评论的看客们,自然也不乏赞赏者,但揣度、质疑其用意者也绝不在少数。但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艺术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妥帖――当历史在场,艺术家冷嘲热讽,一颗红心地以老拳相搏;当历史离场,艺术家亦复如是,坚决捍卫自己当年以老拳相搏的“历史语境”。
历史的纯文本
其实任何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其尴尬可能与“时间性”“空间性”有关。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诚也。但对后来者而言,提供任何一套历史陈述,就是提供多一重的理解之可能,在不同代际观念、日常本质、城市经验的差异化探讨中,爬疏历史线索本身应该有其客观价值,不便随意弃绝。当然,本次展览在以5年为一个代际的手法之下,硬生生划分出了4个中国当代影像发展的转捩点,不免让人感觉刻意;但反转而言,不应小觑观众对于历史的呼应能力,更何况,优秀的作品显得极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这种艺术与公众的互文、时间与现实的对话之中,惊喜不一定姗姗来迟。比如周铁海在1996年即用胶片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短片,以一种近乎顽皮的方式大大地讽喻了“爱闹情绪”的艺术生产者,艺术生产热衷圈地与垄断、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展览收藏体制关系。该默片不仅让人“哑”然失笑,反思了艺术生产流通环节的本体论,而且就“戏仿”不同电影场景、历史桥段而言也属于一部构思出彩的佳作。《必须》之作能轻易“把”住观众的视线。此外,张培力的《30×30》、林一林的《安全渡过林和路》等早期作品,都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烙印,其影像叙述手法几乎都以一种循环、重复的机械动作中,逼迫观看者提炼出一种更为本质的内涵――那就是,影像并不是提供一种画面式的欣赏,坚决沥干分散注意力的可能,更像是一种纯文本的叙事。
嘹亮的身体
“身体”恐怕是与“艺术”挂钩最密切的关键词之一。在不同背景、叙事策略、表达器材甚至是不同性别的艺术家身上,会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崔岫闻的作品《洗手间》在特殊的空间中摸索到了一根身体之藤,在日常生活的暗面中,性工作者在卫生间大大方方地检视自己的妆容、调整亵衣与身体的关系,甚至因为同性而显得无所顾忌。但有意思的是那个清洁工,她的表情在镜头的暗角显得无法预测。但不妨将“清洁工”的存在作为一种参照系。“清洁”一词暗示了管理与规训;而清洁工作为被日常生活规训了的人众之一,私下也会对这些性工作者进行道德和伦理的判断。而这个原本模糊了阶层的空间内,一种同为底层、边缘的风向标又隐约抖动起来。
黄然的《危险愉悦》则显得更具美学趣味――徘徊在简洁但不乏深刻的感官体验中,充满了一种“欲说还休”的气质,意蕴层峦叠嶂。短片开首,一人行径在莽莽丛林之间,这敛默的黑衣者带着猎物“游山”,而猎物则着白色蕾丝束裤,性别不明,施然尾随其后。若行若止间,镜头切换到了另一重向度的场景中:一间白色微光的室内,黑衣者颈项被缚,已无声息。屋角,一堆了无生命脉象的躯壳。在这里,暗示了在任何一种关系中,也好,性别也罢,强弱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随时可能翻转。而作为一种博弈,即便表象再怎么诗意、耽美,也仍然搅缠了惨烈的、甘愿式的受虐和服从。片子在整场哑剧中推进,最终在笼中雄鸡食其伙伴之尸蛆中,猛然抵达视觉高潮,男性白衣者也终于露出了脸庞上,诱人、富有攻击性的双唇。清凉的、舒缓乐声的响起,片子重回到“前叙事”的阶段,首尾相衔――两人从滩涂上泥泞走来,在波涛声和配乐中,缓慢地走入森林的入口出,也即将走入片子的肇始处。
背过身去的爱
历史中,血缘、亲缘以及基于中国历史的传统革命经验,在不同作品中以多种表情和复杂的情绪盘根错节在作品内部。宋冬的三部曲《抚摸父亲》中,起码跨越了三种维度:长达14年拍摄中的“时间性”、亲人生死的“在场”与“离场”,以及那盘与其因为悲伤不如因为爱戴和敬畏而永远不再打开的封存录像。第一次抚摸中,在影像中宋冬的手投射在父亲的身上,就像一枚烙印――一定程度上,反转了父子的上下关系。而2002年的录像中,宋的父亲正在太庙教孙女玩一种父辈的游戏――抽陀螺,太庙也呼应了君臣、父子的层级身份的传统空间。宋冬缓慢地在倒映的水中抚摸父亲,水面扩散开的涟漪作为一种“血线”,血缘与爱在水中无法被稀释。同样的,李永斌的《脸》则在纪念母亲,同样呈现一种“时间性”的维度中,但时间缩减为一昼夜:儿子与母亲的脸因为夜晚而叠合、因为白天的到来而消失。在这场画面带有鬼魅色彩的个人化纪念中,却呈现了一种古典的诠释:“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周啸虎的作品以泥塑搭建了一个戏拟革命乌托邦的场景:借由纪念历之名的政治作秀、千人一面的政客表情、延安窑洞与911大楼的拼贴穿插。但《为长征延长一公里》的植入,却意外偏离了某种嘲讽的口径:那些在行进中出乎意外被沼泽吞噬下半截肢体引起了令人错愕的恐怖感。但借助于泥土材料,身体重新被接出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意志极限,继续向不可知的革命行进。
也是在这里,似乎提醒我们绕过某些障碍:历史的叙述策略、真实和历史之间虽然本身总是一种“当代史”,但某种意味上,在历史的既成现实面前,类似“慎终追远”的情怀和历史的多重叙事策略之间,并不是总是“麦芒与针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