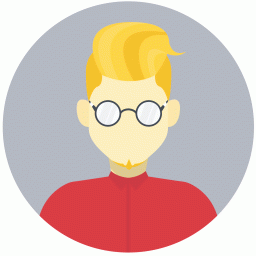余世存学习就是一种价值
时间:2022-09-01 05:10:21

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架构,其实都是西方式的。再讨论中国传统或中国方法,是可笑的。这个不是谈的,是要靠你去生活,去实践的。
一位朋友评说余世存,说他有一张“未受折磨的脸”,我们在这个初秋下午见到这张脸,它温暖、淡然,确乎跟欲望无关。在这张脸上看到一些我们久违的表情,在这张脸上看不到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情。照余世存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张“超脱了的脸”。
他戏称自己是“知识暴发户”,称自己少年时代在穷乡僻壤能够得到的读物一度曾经是《读者》,故而当时兴趣的范围或热爱的自由也不至于太大。他云淡风轻免我们于某种惯常的不自由:当习惯性地生起膜拜别人的冲动,难免以为人家天生伟大,一贯完美,不惹凡尘。事实不是这样。9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余世存此后体验过各种行业,看见过缤纷黄昏里的野,而立之年就曾真诚地探讨过生命的重建,解析中国男,注译《类人孩》,并在此后不断对照现实发展这一概念;对《世说新语》体情有独衷,他编了两本书《非常道》和《非常道Ⅱ》;去大理乡下蛰居两年,他说他确信老子确有其人,始为老子作传。
知识分子的意义高于知识本身
《东方养生》:您是不是精英?
余世存(下称余):很难讲。我觉得我在某个范围之外。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我不是回到北京,现在还在乡下。
《东方养生》:您似乎自外于“知识分子”,同时许多人认为,你是当代“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是不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大家现在还没有厘清?
余:我的生活里,有一些时间被耽误掉了。但是很幸运我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至少能够表达一些生存的真相。为社会,至少为读者提供一些温暖。还能够为社会做一些命名,做一些审判性的工作。很多学者,他只是学者,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只是把知识谱系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不能对我们现实的生存处境做一些命名和判断。我回了北京,感觉像一个布道士一样,有一些焦虑,有时候生气。对于一些年轻的孩子,我跟他们说,你不要急于给自己定性,也不要急于设定什么生活目标,也不要着急去追随谁。我建议他们大学之后一定要有五年到十年左右的游学时间,你多听就行。一定要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现实。
《东方养生》:良知很容易被遗忘,重提,有多大市场?
余:不是有没有市场。它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参照。比如说当中有许多人自杀,我们现在自杀的人也很多,没有偶像,没有价值。我侄女都在说,现在中国有什么值得尊敬的行业,从医生,到老师,到律师?期间的事,现在还在发生,两个时期基本是同构的。安身立命的东西没有做得很踏实,某人今天是开放的,忽然明天信佛了。后天又去信基督教。
《东方养生》:这种现象固然说明有一些东西大家没搞清,但这是不是也恰好证明,大家都在试着努力搞清呢?
余:我不觉得。我更认为是因为缺乏知识的尊严,做人的尊严,是没有知识的自尊、学术思想的自尊。固然我们不应该用恶意去揣测别人。但是至少一个人在知识的道路上,理性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假如你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不够理性的时候,你必须检讨你的学术和思想根基。
真正的生活与生命的质量
《东方养生》:你曾经说,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在你看来,怎么才算真正的生活?
余:我觉得一个人从自己受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得到对于世界的基本判断,无论是伦理的,还是善的。现在这个时代,我称为经济,跟前些年的政治,类似点非常多。像我的兄长一代,八十年代看,他们非常有才华,无论是研究的才能,还是创作的天赋。后来纷纷下海挣钱,等到挣了一二十年钱,确实成功了,也回到某些领域来附庸风雅,但是再不可能有创造力。这样的人生是被耽误了。从目前六十岁的人,到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都在不同的阶段耽误过时间。一些青年跟我说,我一定要先去打工,同学谁谁买房了,我女朋友逼我贷款买房。那么至少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要做这个,他就没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中断自我教育。从前是政治耽误,现在是经济绑架。
《东方养生》:你说你自己非常快乐。有没有可能,那些早年下海经商,并获得了这个社会追捧的那些东西的人,他们也很快乐?
余:不是。中国社会学家、学者、学生,应该做样本调查,就比较清楚了。从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子来说,中国人的生命质量是出问题了。一个财经杂志的记者,或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很可能会比某些地方社科院的研究者视野开阔,阅读量大,研究能力强。我见到的很多驻北京的路透社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一个记者比社科院的许多学者要强。这是生命质量不同,五个学者,不如人家一个记者。中国13亿人,在2004年前后一年的出版总值比不上欧洲一个出版社。同年中国人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年平均读书是45本,而同期犹太人是64本,美国人是50本。许多人并不读书,甚至许多公共知识份子,只是翻书看书。现在的大学教授都不敢去休学术假,怕许多消息接收不了,怕失去一些机会。但民国时像朱自清动辄去欧洲休一年,他确信他自己的研究和认知,总是前沿的。这是一种自信啊。
《东方养生》:现在为什么大家没有这种自信了?
余:因为他被这个社会游戏裹挟去了。
能力在于主宰自己的生活
《东方养生》:看起来问题不是出在个体。
余:首先是制度环境。但从历史的角度,我跟年轻人说,既然这是一个次法西斯时代,就意味着这个时代一定会过去。一定要乐观,你还是要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最好不要参与这个时代的游戏。你参与了,就被左右了。
《东方养生》:但是你不参与,难以了解这个游戏。不了解,怎么玩?
余:这是不同年龄的问题。所以我跟年轻人说要有十年游学时间,到中年再立论。不要急于找方向,找目标。有一些年轻人甚至跟我说,我一定要在五年内买房子。
《东方养生》:你是不是因为参与了游戏,看清了游戏,你选择了退出这个游戏?
余:我觉得都体验过了。比如当官、当老师、当志愿者。
《东方养生》:你做了这个选择,你成了现在的自己。
余:人到了某些时候,就不愿改脾气了。
《东方养生》:但是我们终究是要修改自己的。成长不就是这样吗?
余:我觉得至少要变得越来越有能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比如我们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信心和温暖传递给周围,让这个世界不那么险恶,不那么冷漠。还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思路和思考。这也是力所能及的。可以种树啊,育人。现在打开微博,到处刀光剑影,我想至少我赞美了许多普普通通的人;赞美过那么多人,还从很多精英身上看到了优点。虽然有时候我也批评,但对他们身上的每个优点是不放过的。
《东方养生》:你刚才说假如你是大学教授,可能你也不敢去休学术假;刚才又说,要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生活。
余:这个问题好。其实我知道体制内有许许多多非常优秀的人。比如说某区有一位建委主任,他说只要他在,某个古迹就不会被拆。不像有些人,进到那个游戏里,彻底身不由己,唯唯诺诺。这样正面的例子,我是知道很多的。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身边的年轻人,要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不要那么太绝望。
《东方养生》:您是说绝望?
余:有的人得了抑郁症,这个社会有许多人不快乐。我记得哈佛大学的黄万盛教授曾经跟我谈到过。西方人也在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在关注生存的非经济价值。比如学习就是一种价值。孔子的弟子在最后回忆老师那么多言论的时候能把“学而时习之”放在第一句,那不是没有深意的。
在生活中努力
《东方养生》:你所倡导的这种生活态度或方式,是不是基于某种的想象?会不会即便放在相对完备的社会里,也是一种过于理想的范式?
余:也不是。我们还是换一种说法,还是用我的那个类人孩的概念。一个成年人,肯定是有责任感的,而且他会尽可能地去认同并习得人性那些美好的价值。比如他会对周围的人尽量负责任;第二,他会去吸取新知识、新智慧;第三,他对这个社会怀有很通达的态度。这个成年社会是哪里呢?我们可以说,较理想的社会,比如现在的西方社会。我在长沙时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聊起来。他说有一次去麦当劳吃饭,吃完,他打算抹抹嘴走了。这时看到邻桌有三个韩国人,让他非常感动。三个韩国人吃完饭,用餐纸把桌子擦干净,并且把椅子归回原位,把垃圾倒进垃圾箱。他就觉得,这种细节都是举手之劳,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包括他个人,都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成年社会或理想社会跟一个专制或一个由类人孩组成的社会的不同。学者在台上讨论学问,同时对听众或读者的处境漠不关心,毫不同情,这就是缺乏那种成年理性。它并不是可望不可及,事实上这东西就在我们生活里,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