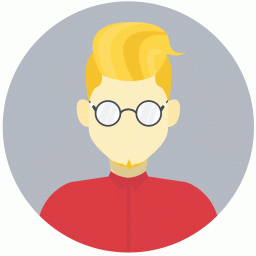南非:寻找曼德拉的足迹
时间:2022-07-20 08:04:59
第一次去南非是2001年。回程时照例转机约翰内斯堡(Johanesburg),只觉得机场与两周前不大一样,拥挤不堪甚至有几分混乱,休息室里许多人围在电视机前七嘴八舌,只听得三两零星的词句:美国、事故、恐怖袭击。环顾四周,人群中不少乘客开始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在不大的空港内漫无目的地打转,所有飞往美洲的航班取消或转航,许多乘客只好在空港内等候,迷茫的眼神中充满不解与无奈。重返南非时已是距离“9·11”事件发生的许多年之后,又一次感受南非这个彩虹之国。 约堡南郊寻找曼德拉生活的地方
人们喜欢将约翰内斯堡这座非洲南部最大的城市简称为约堡(J’burg),约堡市内像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一样,街道笔直、高楼林立,购物中心人群熙攘。我一直想去约堡南郊的索韦托(Sweto,Southwest Township),那里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大主教图图和已故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都曾经在此住过,并从此开始他们漫长的反种族隔离长征。听说我的出行计划,客居此地的友人雅克琳建议我一定要去参观海克特·彼特森(Hector Peterson)纪念馆。
我跟着一位叫普勒的黑人去索韦托。普勒和大多数黑人一样,一直居住在黑人社区,五十多岁的他穿着利落整洁,修长的身形在阳光下更显得风度翩翩。我问他年轻时是否想到过南非的今天,他说:“怎么可能?我年少的时候觉得这只是一个梦啊。”见他一路用不同语言与人打招呼,我便问他会说多少种语言,普勒掰着指头数:茨瓦纳语、科萨语、祖鲁语、英语,南非荷语也会,但是一般不说,因为那是南非白人的语言。我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发现索韦托和一般大都市边缘的贫民区有所不同,没有弯弯绕绕的街道,布局好似棋盘,平直的道路把简易低矮的平房分割得方方正正。见我疑惑,普勒解释说,这是最早建立该区的白人政府故意为之,这样一旦怀疑黑人聚集、策划示威抗议时,警车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社区,开到家门口抓人。街边高大的路灯最初用的是白炽灯,黑夜里又高又亮,正好给警车照明。
约翰内斯堡意为“黄金之地”,金矿开采的历史已有上百年,出城不远便可见露天金矿。相继发现的铂(白金)和钻石,一直是南非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控制矿业的少数白人需要大量黑人矿工,而南非(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ty)从1948年开始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为矿主雇用廉价矿工提供了方便。黑人从乡村被征招到索韦托这样的“保留区”,而家人则在稍远的大农场里,任何黑人不得在规定时间内离开居住区,否则按违法处理。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普勒,记忆中满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时全南非的学校、医院、公园、沙滩、电影院、体育馆无不分为黑白两类,白人的场所黑人不得入内,就连火车车厢、公园里的凳子也分类,标明“白人专用”, 每个黑人从15岁起出门必须随身携带护照,否则算违法。普勒回忆说,我那时还小,只记得大人说起有个叫曼德拉的黑人律师带头烧毁自己的护照以示抗议,后来又听说国大党什么的,可一直到1992年吧,国大党都是被禁止的。说话间我们来到一所学校前,我不禁问普勒:你的中小学里使用什么语言?他说先是茨瓦纳语,后来政府规定要说南非荷兰语,因为索韦托抗议的影响,又改回茨瓦纳语和英语。
这所学校对面便是海克特·彼特森纪念馆,纪念的是一个叫海克特·彼特森的学生。1976年索韦托黑人中小学抗议政府强行规定在学校使用南非荷语,年近13岁的彼特森遭遇枪杀。纪念馆只有两层,展览有大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图片和新闻稿件,以及隔离时代的法律文件,通过多媒体展览,参观者可以短时间对南非黑白隔离的教育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彼特森中弹后被游行者抱在怀中的照片,奔跑的游行者脸上写满愤怒与悲伤。这张照片也曾传遍并震惊全世界,由此开始引发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非进行制裁,制裁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
临出门时,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段彼特森忌日时他姐姐说的一段话,大意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彼特森当烈士(martyr)看待,他被枪杀时只是一个孩子,因为被剥夺在学校使用母语学习的权利,跟着比他大的同学抗议而遭遇不幸。他是种族隔离制度下失去性命的千万黑人之一,今天对他的纪念是让我们不要忘记那黑暗的年代,使之不再重复。在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有关语言的政策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否认个体或群体的身份文化认同常常从对其母语的蔑视、侵犯甚至剥夺开始,以自己的语言为工具来同化他人的实践往往被冠以堂皇的理由,而随之引起的矛盾与冲突比比皆是。彩虹重现南非后的1996年,南非新宪法终于承认十一种官方语言,废除隔离制度的同时,将对母语的尊重和人的尊严还给千千万万的南非人。 在佩托利亚的农场穿越历史
佩托利亚是南非首都,距离约堡四十多公里。这是一个一眼望去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城市,城市中心的楼房与四周缓坡上的别墅构成这座城市的面貌,街道宽阔,除清晨和傍晚等候公共车到白人家做工的黑人外,几乎没有行人。
友人推荐的客栈位于一处环境优雅的小区,车行缓坡时,只见红花绿叶出墙而来,鸟语不断。当然,住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安全。主人若娜一边带我参观房间一边和我聊天,我拿到名片时,感x娜说她的祖先原为法国南部的胡格诺新教徒,16世纪时逃至南非这片被荷兰新教占领的荒芜之地,几百年过去,同一姓氏的人在南非几乎上千。我只是从书上知道16世纪的那场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派的战争,以及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赦令》,从此结束长达30年的宗教内战,哪会想到在地球的南端碰见与这历史相关的人。若娜中学毕业后离开父母的农场来佩托利亚上大学,在这里结婚生子,生活了快30年。她告诉我,客栈的每个过道房间都有电子警报,佩托利亚家家户户都装有带电的铁丝网,每一道院墙外必见“武装回应”(Armed response) 的标志,一旦有人触摸,铁丝网便立即启动电击和警报,持枪保安会在数分钟内赶到。南非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受累于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实,以至于高科技作后援的私营保安业在南非发展蓬勃。
在客栈逗留期间,我时常与若娜聊天,她与女儿经营着三家客栈,与丈夫分居后,独自住在水坡这边。母女负责客栈的财务和采买,雇员都住在城外方圆数十公里的黑人社区(township)。平时往来客栈的南非人不少,但是很容易区分,干活的是黑人,住店的是白人。我问若娜,你有黑人朋友吗?她想了想说,谈不上朋友,只是黑人常客,圣诞时去太阳城(Sun City)时总来这儿住。佩托利亚往北一百多公里处的太阳城是南部非洲的拉斯维加斯,加上紧邻国家公园菲拉奈斯博格(Philanesburg),不少人喜欢去那儿度假。若娜告诉我,1994年以后很多白人对南非的未来产生怀疑,担心黑人执政后对自己不利,便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若娜的小儿子也不例外。若娜说她和儿女们虽与黑人共事,但也没有黑人朋友,因为他们成长在隔离时代,不过将来他们的子女上混合学校,会有黑人朋友的。
若娜坚持请我去一个典型的南非农场吃早午饭。在能容下几百人的露天花园坐下后,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环顾四周,仿佛一部殖民时期电影的场景,不卑不亢、彬彬有礼的服务生不是有色人便是黑人,而携家带口来此享受周末的是清一色的白人加上我这唯一的异乡人。我第一次对人的肤色如此关注。这场景让我想起库切(J.M. Coetzee)的书和他笔下那个伤痕累累的新南非,小说《耻》中理性而又失落彷徨的白人教授,那个愿意把自己的身心一点点熬进这片土地的教授女儿,不也和若娜和她的家人一样,来自眼前这样的群体吗? 从德班踏上曼德拉“真相与和解”之路
对德班的记忆总伴着若有若无的甘甜味,每个清晨与黄昏,伴随着海风穿过鼻腔浸透心肺,回甜是那种甘蔗刚出榨糖机时特有的焦糖味。这是德班特有的味道。印度洋广阔浩瀚,平缓的海岸无限延伸,端头的两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出产国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从古至今一直靠着德班这个重要港口把甜蜜送往远方。自18世纪后期以来,德班周围也开始甘蔗种植,大量印度的契约劳工来此从事制糖业,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人、银行家等,他们大多是穆斯林,给南非带来规模可观的清真寺。海湾和商场人头攒动,到处是咖喱的芬芳,银雀般婉转的印度方言,妖艳女人额头上的一枚红豆,让人恍惚是到了孟加拉湾。
德班一带本是祖鲁人(Zulu)的故乡。15世纪时,葡萄牙伟大的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去印度的海上航行中发现了德班,这里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由此开始。1994年后,德班省更名为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除印度裔和祖鲁人外,南非的有色人(colored people)也有不少在此生活。有色人多为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后裔,比例不算大,在种族隔离期间,他们被白人划为比黑人高一等的居民,享受黑人不能享有的部分权利,但又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近年来,大量祖鲁人从乡村迁居德班,毗邻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甚至更北的刚果人也陆续来到德班,使这个城市变得五颜六色,也增添了些许迷茫与混乱。
生活在德班以及周围小镇的印裔南非人共有80万,当代印度之父甘地便是德班人。南非的各行各业里都能见到印裔的身影,想起一位南非印裔同事曾说过,南非的印裔人十有八九来自德班。此话果真不假,我在开普敦遇见一位印裔雅斯米纳,从前是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谈论德班让我们马上亲近三分。
1994年,南非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从此告别血腥的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总统的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积怨甚至仇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是德高望重的大主教图图,他倡导在古老的非洲观念“Ubuntu”之上实现宽恕,从而达到和解。有位茨瓦纳(南部非洲民族)母亲解释何为“Ubuntu”时说:“Ubuntu的意思就是同村人,你存在,所以我才存在”。以牙还牙固然解恨,但无助于和解,唯有宽恕下的记忆才是不重蹈旧辙的良方,但宽恕的前提是恢复真相并对过去有所悔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决定对1960年至1995年间白人对黑人所犯的罪行以罪者悔悟,通过获得受害者宽恕和司法赦免的方法来弥补伤害,以达到最终的和解。
雅斯米纳曾经作为委员会的十七名成员,为了寻求真相、悔悟罪行、宽恕过去,踏上了一段长达三年的漫长旅程。她说:“我们最初不知道从何开始,图图主教告诉我们不要情绪化,才能理智地倾听。可是你想想,对黑人来讲,任何一个穿制服的白人,可以以你进了白人的商店为由,在大街上用皮带抽扁你的鼻子;如果你是女性,被任意关押在警察局,一阵毒打之后很可能是犯;几个白人风高夜黑时在荒郊野外枪杀你的儿子,因为他拒绝给白人让座………然后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些人对受害者、对死者的母亲悔过,说声‘对不起’,往事便可一笔勾销?如何做到理性?”三年中,委员会成员、律师、记者等利用一切交通工具走遍全南非,举行了三千次听证会,倾听了近两万名受害者的故事,有时还需要警方合作开墓验尸,寻找死者遗骨。这期间,好几个心理医生随队提供心理服务。宽恕旨在使民族保留记忆的同时放下包袱,促成曾对立的双方互相宽容地共同生活下去,面对伤痕累累的新南非,对诚心请求宽恕的人实行大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试图以和平方式达成民族的和解,以避免将“胜者之公义”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杜绝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图图说过:“只有通过宽恕才能真正解放受难者。”可是,宽恕的力量真的如此之大吗?几十年的黑白鸿沟真的可以通过公众形式的听证和解来填平吗?很多人审视南非经验时提出,法制社会中司法应起的作用不应忽视,但在南非当时的情形下,和解与宽恕似乎的确是智慧与明智的最佳选择。 再见!Bafana
《再见!巴法纳:曼德拉,我的囚犯,我的朋友》(Goodbye Bafana: Nelson Mandela, My Prisoner, My Friend)是一位南非白人留下的回忆录,作者是原监狱看守詹姆斯·格瑞戈里(James Gregory)。书中讲述的是格瑞戈里在罗宾岛监狱与他看守的囚犯曼德拉的一段往事。格瑞戈里在南非的农场长大,童年与黑人孩子交往时学会了曼德拉使用的科萨语,这使他与曼德拉之间建立起某种默契,继而受曼德拉影响,开始对自己服务的种族隔离制度产生怀疑,以至于最后参与改变这一制度的运动。在当时的南非,普通白人从小对白人高人一等的观念坚信不疑,重新审视甚至否定自己过去的价值观并非易事,任何同情、理解、支持黑人的抗争都意味着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背叛。当格瑞戈里被告知重新回到岗位,再次监看曼德拉时曾犹豫不决,想起妻子曾问他:你不是说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吗?格瑞戈里从一个监狱看守的视角,目睹了曼德拉书写当代南非的历史,自己也曾经是其中一部分。曼德拉告别监禁生活时,用科萨语对格瑞戈里说:再见,伙伴!(Goodbye Bafana)
今日的南非,人们引以为骄傲的黑白足球队以“Bafana”为名。翻开报纸,尽管有关种族关系的报道和评论仍然占据一定篇幅,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话题,记者、读者关心的更多是各政党腐败的丑闻、不断上涨的油价、令人忧心的治安、不足的供电以及政府对艾滋病预防的不力等。将近二十年过去,南非的确告别了那段曾剥夺黑人尊严的屈辱历史,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面临各种困难,民主的完善和民生的改善是南非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在南非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南非伟大的作家库切,他貌似平静的叙述背后却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让人们对南非的伤口进行冷静地剖析。黑白两个种族之间曾经充满隔阂,又不得不共同生存,他们对历史的忿满交织着对未来的希冀,对自身的无可奈何混杂着与他人的隔膜。因为祖先的罪孽,南非白人的命运和社区里为争取饮水供电的黑人、金银矿井下的黑人、德班的印度人、有色人、为生存空间土地而挣扎的桑人、来此谋生的他国移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密相关,唇齿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