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法的名义“撒野”
时间:2022-07-08 02:3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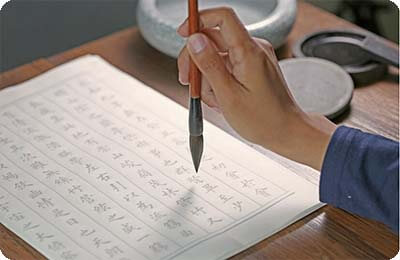
郑孝胥有一段很出名的评语,涉及到“学术”二字:“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张之洞闻后曾笑答:“袁世凯何止有术,简直多术;我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至于端方有学有术,不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是无穷的,谈何容易!端方不过喜欢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陶器,附庸风雅而已,怎么能说是有学有术?”
如今“学术”一词常常挂在嘴边,岂知二字含义悬殊。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和“术”属于不同范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严复曾分析过二者的关系:“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王国维进一步认为“学”之义,古今不同,古包括“知”和“行”,今主要指“知”――“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观照时下,应该区分学问、知识、信息,大多数人了解的是信息,少数人掌握的是知识,很难谈得上学问。中国一直罕见“科学”而推崇“技术”,普遍存在重“术”轻“学”的倾向。虽说学术并称,现实中一直是“术业”高度发达,而“学业”正好相反。个人成就以“学”为标准,通常评价一个人会说学业有成。反之,批评一个人,就会说不学无术。眼下书坛中“学”和“术”的背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将学术作为外包装,有学术样式而无学术内容和学术精神,只是学术灌水。二是追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学”本身,而是为了获得“术”,以技术、技巧、实用等为目标,赚钱是实用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三是以“登龙术”求捷径,乃学与术相背离、脱节最严重的情况。关乎各类“术”的培训,十分火爆,哲学、文学等“×学”渐成冷门,远不如美容和厨师的经济效果立竿见影。学子越来越少,术士越来越多。
书坛中的“术”主要有两类。一是“正术”,如技术、技巧、实用、提高;二是“负术”,如权术、骗术、耍术、邪术等,“登龙术”即其中之一。研究、追求“正术”尚能理解,无可厚非。如今却是施展“负术”者趋众。玩权术者自视甚高,身居高位,熟练地进行权力资本的转换。骗术在书法圈中屡见不鲜,低级一点是帮助出作品集和发证书,高级一点办强化培训班,赠送成功法宝。邪术、耍术易于施行,成本最低,只需费一点口水。书坛遍布“话语英雄”,“我说故我在”,不断抛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鄙人独创一格,几千年没有还没这种写法呢!”实质是一种“审美暴力”。行“负术”者常常毫无顾忌,可名之曰“撒野”。说到“撒野”,多半会想到牛二,与书家扯不到边。然而现在赤膊上阵的,无一不是“大”人物:大官到处题字,臭不堪言,却是一片叫好声,反正不敢讲。大明星知名度高,偶尔有一些批评,可以充耳不闻,小人物的话不过是挠痒痒,反正管不着。现代派大师玄妙之极,说了也很难明白,呆一边凉快去,反正看不懂。江湖大侠至贱无敌,死猪不怕开水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无所谓。
借书法的名义“撒野”,最大的好处就是看起来文雅、风雅。伪装的撒野比正常的撒野更可怕。“名不正则言不顺”。凡事都得有一个名义,如此,便可名正言顺地做并非名正言顺的事。“丑书”便是极力安排出来的一个“名义”,把徐渭、傅山、金农拉上做垫背。傅山的“四宁四勿”完全被扭曲,比天津大麻花扭曲得还要狠,被绑架成“丑书”宣言。岂知“丑书”是个大杂烩!有的功力不济而百病丛生,有的故作姿态,不惜丑相百出,有的面目丑陋狰狞,令人恐怖,有的恶俗欺世,却大言不惭。凡此种种,混作一谈。书法不完全以美丑来衡量,主要以“真”为标准,是否写出个人的心灵情感。“丑书”当以广义和狭义区分。广义的是样式,丑拙、丑怪,丑而不恶,狭义的是精神,心理肮脏不健康,既丑且恶,已成“恶臭”。狭义的“丑书”应更名为“臭书”。以“臭”相喻,古已有之,“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广东有一道名叫“臭豆腐炖猪蹄”的菜,正式名为“中国足球”,寓意是“臭脚”。根源都在于思维腐臭。书法当走正道,寄希望于奇巧秘技之类,不过是“一招臭棋”。时下有些人动不动就说,“让历史来评价我吧”。想遗臭万年,还没那个资格。
古人之书写个人性情,不存在媒体的放大扭曲。现在很多是炒作,从娱乐文化中找到了商机,以“出位”吸引眼球。艺术和娱乐之间没有了界限。艺术就是娱乐,娱乐就是艺术。丑角与臭书相伴而生。臭书是书家丑角化的见证,按照一定的市场规律所炮制出来的。既是幕后推手的共赢,也有娱乐文化的胜利但和书法无关。审丑是一种现实心理,通常是对心理脆弱者的抚慰。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一个丑角进城,胜过一打医生。”现实社会的各种压力之下,有很多的寂寞、无聊、疲劳、郁闷、焦虑、失意、挫败的情绪需要加以缓解排遣,等待爆料和丑角。需要一批更倒霉的倒霉蛋,比自己经历更悲惨,长得更难看,抬高自卑的自己,俗称为“心理学上的垫脚石”,由此获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满足感。书法被视作一种发泄方式,专意寻求精神的狂野释放,一些人不惜刻意装扮成丑角,以“臭书”来撒野。“臭书”非书,已经不是审美意义上的“丑”,艺术夸张已成现实的变态,书写行为成了出乖露丑的恶俗举止。就好比人与死人不是一回事,活的叫身体,死的叫尸体。前者有生命迹象,后者没有,这是根本差异。“书法垃圾”和“垃圾书法”严格说来是缺乏逻辑性的。书法与垃圾扯不上边,垃圾如果成为书法的修饰语,就已经是垃圾而不是书法。
退一步来说,有一个哪怕十几个跳梁小丑,也无伤大雅。如果变成一种“生产机制”,甘做臭料,出产“小丑”,打扮成生正逢时的“乌鸦”,好像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就涉及到了审美品格问题,远离艺术和学术。集中表现为官员书家的自大心理,现代派的逆反心理,江湖耍术的迎合心理,无知愚昧的盲从心理。书法需要正本清源。很多缺少思考的争执,已使得真正的要旨边缘化了,表面化缺乏深度,片面化缺乏广度,简单化缺乏逻辑,情绪化缺乏理性。通常习惯会问一个书家是什么级别,却不问是什么水平?类似“书家文人化”之类的口号震天响,多半是光打雷不下雨。一来已没有文人,二来最多只能做做“文人的样子”,长发、长袍、长须之类。“文人化”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拿来的“嫁衣”。与“丑书”利用“四宁四勿”做幌子是同一个道理。这不禁让我想起顾颉刚先生所说过的,“要做学人不做文人”。真正的学人是有思想的。缺乏思想,学术变成心术,书法仅仅是技艺的较量,甚至沦落为耍术、邪术。对“学术”二字理解的粗疏,本身就见证了缺乏细致化的体验。不仅“学术”二字截然不同,“贫穷”二字差异极大。章太炎曾说:“所谓贫者,以其贝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从字的形体来看,“贫”字中“贝”表钱财,越分越少就是“贫”,主要指缺乏金钱,不得温饱,反义词是“富”;“穷”是人字洞穴中弓着身体,表示到了极限,不得伸展,主要指仕途坎坷,不得升迁,反义词是“达”。在物质方面很穷但精神上富有便不算贫,物质富有但精神匮乏,穷的只有钱。学术取舍与贫穷选择存在关联。商业利益让人无法阻挡,是所有书法家所面临的挑战。一切物质化,心中没有了爱和恨,只为了钱。书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心灵沙漠化问题。
也有人认为,写字不必上升到思想道德的高度。现在的确不必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连基本的都已经做不到,“上无君子,下无底线”。话说回来,凡有丑角,并不一定就是道德败坏、社会堕落,但反过来一定成立,如果道德败坏、社会堕落,就一定会出现丑角。正常的价值观颠倒了,可以毫无顾忌“撒自己的野,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本质其实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对于这一类人,可以“不敬而远之”。“艺”要虔诚,“学”要敬畏。说到底,与“耻文化”的丢失有关。知耻和有耻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渗透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方方面面。孔子云:“知耻者近乎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老子》中讲“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管子》里讲“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耻文化对国家和个人至关重要。通常强调要修身,到底修什么?当然和“耻文化”有关。掌握权力的士大夫阶层知耻、有耻,国家的尊严才能维护。就个人来说,“耻”乃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知耻”方能有节制,行为有度,取用有节。做人、做学问,要求辨知荣辱,守仁行义,行己有耻。所以古人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