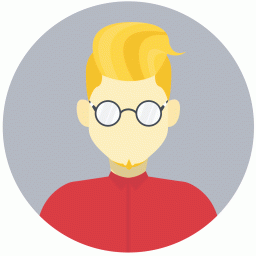那张逝去而生动的脸
时间:2022-06-26 11:13:41
十多年前,台湾的朋友秀兰给我带来这本《明室—摄影札记》,之后,已反反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虽然只有一百七十一页,但总有那么一股吸引力,使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情不自禁地翻开读几页。可以说,它是引导我理解影像的指南。
过了那么些年,在影像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才感到从中悟出了点什么,开始动手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想法只能是我从书中“读”出的,不一定是作者的原意。 马尔巴的典故
在台湾译本的封底,引用了一段的典故,往往被评论这本书的人忽略:
马尔巴因儿子被杀害而伤恸无比。一名弟子说:“您常告诉我们,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岂不也是一种幻象?”马尔巴答道:“你说的没错,但我儿子的死是一种超幻象。”
这故事讲的是:
藏传佛教塔布噶举派的祖师马尔巴修得一门大法,叫“往生夺舍”,可使灵魂脱出自己的身躯,进入另一具尸体,使之复活。他的儿子塔玛多德跟随父亲修行,成为此法的独门传人。
一次,塔玛多德不听父亲的劝告,参加赛马,坠落悬崖,头颅摔成八瓣,伤势严重。马尔巴事先已看出征兆,得知噩耗,忙赶去半路看望儿子。弟子们请师父行往生夺舍法,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马尔巴把儿子破碎的头抱在怀里,哀痛不已。
恰在前些天,一对老夫妻死了独生儿子,马尔巴以佛理相劝,说得子丧子,犹如梦如幻,不要太过悲伤。此刻弟子以同样的道理来劝马尔巴,于是有上面的对话。 关乎个人的学问
上面这段典故与罗兰·巴特以及他谈论的摄影有何相干?
依鄙人理解,《明室》的寓意实在包含在此典故中。罗兰·巴特开篇便舍弃学术的立场,申明只“以对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义的几张照片作为研究的根据,完全不关文本总体,只谈这些个体”。他甚至倡导开创一门个体的学问,不关乎普遍性的“知面”,只关注打动个人的“刺点”。所谓“知面”,即那些分门别类的普遍性知识;而“刺点”,则是与个人情感息息相关的关注点。马尔巴为儿子的死悲伤,而佛教要世人不必执著于死亡,这中间的张力,正是刺点与知面的冲突和纠缠造成的。罗兰·巴特选择了超越幻象的“刺点”,不单出于深究学理的本分,更来自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 寻找她的脸
罗兰·巴特之所以生出谈论摄影的念头,并非要再次阐发学术,而是恰恰相反。他抛弃关于影像的学术讨论,一心要透过对照片的凝视,找到记忆中母亲的面容。
马尔巴丧子,当暗喻着罗兰·巴特的丧母。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无法在母亲的一堆留影中寻回与他记忆相符的那张照片。每张照片只保留了她面部的一点片段,一个局部,显现各个不同的母亲,而非她的本质。
以致“因为我错失她的生命本质,所以我错失了全部的她”。
罗兰·巴特独自待在母亲的屋子里看照片,企图跨越分隔在两人之间的时光。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母亲冬日花园里的一张小照,才认定,就是她,她就是我的母亲。 《明室》插图
母亲那时五岁(1898年),“两手相握,一手以一指勾住另一手,像小孩常做的稚拙手势。”
此刻,死亡的幻象终于被一张小女孩的照片驱散,那是一幅既公正又正确的图像,罗兰·巴特说,他从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剧(父母离异)以及任何体系所约束的善良。
于是乎,影像超越了时间:
总算这一回,摄影带给我仿佛回忆般确定的感受,正如普鲁斯特曾体验过的:有一天,他弯下腰来脱鞋,忽然从记忆里瞥见他祖母的真正容颜,“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从不经意而完整的回忆中寻回了她生动真实的面貌”。其他的相片,仅有类比而无真实,唯独冬日花园里的母亲,在化学处理的纸片上显出了“本质精华”。这是罗兰·巴特企图寻找的“独一生命体的科学”。 唯一的相片
从临终前的最后一张相片,一点点回溯到孩提时的留影,罗兰·巴特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找回了“原原本本的她”。
找回的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孩子,正如同母亲垂危之际接受罗兰·巴特的照拂,使两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母亲变成了女儿。罗兰·巴特以他的寻觅,让母亲在一张童年的照片上重生,也让自己面向死亡:
那么没有下一代的我,在我母亲卧病时,我孕育了她,她去世了,我也不再有任何理由去配合至高生命的步调。我的个体永远不能普遍化,我只能静待我自己的死亡,完全的,没有死生延续之辩证的死亡。
书中没有展现冬日花园里的母亲,因为它只属于寻找相片的儿子,是他的创伤,他的刺点。而对于一般的读者,那不过是“随便什么”的又一幅照片而已。所以,读者只会看到,而没有看见。
因而“家”不可以化简为“家庭”,“她”不可以化简为圣像画中的“母亲”,“这张”照片不可以化简为“一般”的照片。母与子这两个生命体均独一无二,彼此牵连,犹如倒影相互映照,“并非不可或缺,而是不可替换,”此一消逝,彼“一下子便永远失落了”。
所谓影像,尤其是家庭的影像,根本上是无法对他人展示的。除非有一个巧遇化解了相框围成的屏障,让观者的记忆与这张相片彼此牵连,形成独一无二的联系,沉睡在影像之中的生命,一经凝视,便悄然复活了。 此曾在
罗兰·巴特从一己的体验出发,却得以窥见摄影的真谛:
若与绘画和文章这两个“模仿体系”比较,照片里总有个东西曾在那儿,被作者命之为“此曾在”。
他在这里,现在时;却已逝去,过去时。相片记录了真实的存在,但又把那真实带回往昔:
死者的相片如同发自星星的光线越过时空,延迟而达,触及了我。被拍者的躯体和我的眼光之间有某种脐带相连:光线不可捉摸,此处却如一肉身实体,是我与被拍者的他或她所共享的一线皮肉。
这并非哲学的譬喻。是奇异的针孔镜头吸收了过往事物的光线,那发泽,那肤色,那眼神,再显影于底片,经由光的转换抵达观者的眼睛。为此,罗兰·巴特与母亲的相会,是往昔与今日真实的相遇。由光的牵引,此刻与曾经共存于同一个表面。犹如抵达我们眼睛的星光,发自于若干光年以前,却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刺痛,让我们有了穿越时间的幻想。 像
于是,观者欲与对象对话:
若你健在,尚在何处?
却没有声音从另一时空传来,空谷并无回音,影像沉默不语。这令观者怀疑起自己的身份:
我究竟在此时,或在彼时?我是生者,或是往者?
倘若某人被拍了相片,被锐利的针孔凝视片刻,他便被锁定在非此即彼的缝隙里,往昔和今日两个世界将它相互拉扯,毋宁说他被抛弃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在纸的媒介上,见证了自身死亡的事实:
当我在这道手术后(指被拍摄)的产物中发现自己时,看到的是我已完全变成了像,亦即变成了死亡本身。别人—他人—将我从我自身剥夺而去,他们残暴地把我变作物体,任意处置我,摆布我,存放入档案中,准备随时施用各种狡诈的弄假伎俩。
“像”和“人”经摄影的瞬间一分为二,像被装入镜框,装入身份证,装入档案,装入视频处理软件,它成了众生的一张脸谱,与那个人不再相关。
一声短促的“咔嚓”,即宣判了个人的死亡。 摄影的背景
有读者被罗兰·巴特的论调惊骇,惊诧于他把摄影的本质追溯到死亡。可罗兰·巴特还要说明:正是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死亡危机”,催生了这种新的影像。死亡亦为社会的基本元素,必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特定的位置。以往,宗教和仪式容纳了死亡,使之与私人生活隔绝。可现代化的潮流让宗教式微,让仪式堕落,因而死亡得以突破原有的禁锢,在日常生活里处处显形。“摄影或许正应合了死亡向现代社会的入侵,一种缺乏象征性,且脱离了宗教、脱离了仪式的死亡,好似突然潜入了原原本本的死亡。生命/死亡,这一选择范例已被化简为简单的快门启落,分隔了起初的摆姿照相与终了时的相纸。” 命运
死亡被罗兰·巴特讲得如此单调乏味,可它本身便是单调乏味的。相片又何尝不是如此?沉淀在纸片中的影像渐渐发黄,渐渐模糊不清,终有一天被丢进垃圾桶,不在你生前,或在你死后。更不要提及那些数字化的拷贝,纸质的图像还可以跟随时间老去,而电脑里的文档,若不遭人糊里糊涂删除,则因硬盘的损毁而不知所终。有如车祸,有如猝死。又如镜子打碎,镜中的幻象顷刻瓦解,踪迹全无。
摄影之诞生,得益于穿透时间的光线。而那时间,也把摄影的肉体穿透。无法永生的人,拿命运和时间无可奈何。当相片被时间燃为灰烬,伴随其中的爱,也烟消云散,化作虚无。
诗人马骅生前有短歌云: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
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
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前面四句,是德钦藏族的民歌。最后一句,是马骅的感悟。自然的色彩反射在他的瞳孔里,他看到的是色彩消失后的“空”。 狭缝
或许正由于影像之倏忽,呼应着生命之短暂,它才能刺痛心灵,令人流连其中。也或许影像与生命如此形影相随,人们才企图进入相片的深处,活在幻影当中。它构筑起一个虚拟的世界,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被繁杂的现实干扰,亦不被天堂的享乐诱惑。心理学称此状态为“阈限”,佛家称此为“中阴”,人类学称此为“过渡”,混沌而不纠缠,困惑却充满希望。
就在非此非彼的狭缝中,影像为人生立起了两面镜子。 快镜和慢镜
阿捷赫是古代欧亚大陆“哈扎尔王国”的公主,每晚她的左右眼睑上都要写上毒咒字母,谁见了谁就要死。一天:
为了给公主解闷,奴婢很快给她拿来了两面镜子。这两面镜子表面上与其他哈扎尔人的镜子并无不同,都是用大块盐晶磨成的,但一面是快镜,一面是慢镜。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将其照出,慢镜则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慢镜落后的时间与快镜提前的时间相等。两面镜子放到阿捷赫公主面前时她还未起床,她眼睑上的字母还没有揩去。她在镜中见到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便立刻死了。因为快慢两镜一前一后照出了她眨动的眼皮,使她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写在她眼睑上的致命的字母,她便在这两个瞬间之内亡故了。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下与世长辞的。(引自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词典》)
相机是眼睛的延伸,亦是镜子的延伸。慢镜仿佛人生,快镜仿佛照片。人生倏忽而过,其影子借图像暂存。但二者均不能永久,人惶惑其中,“便在这两个瞬间之内亡故了。”
照片又如往生夺舍的那具尸体,无论如何仍是一个会腐烂、会消失的血肉之躯。皮之不存,魂将焉附?所以,照片在见证生命的那一刻,也见证了死亡。 结局
书快结尾处,罗兰·巴特写道:
从一张张相片,我越过了非现实的代表事物,疯狂地步入景中,进入像中,双臂拥抱已逝去者或将逝去者,犹如尼采所为:一八一月三日那天,他投向一匹遭牺牲的马,抱颈痛哭,因慈悲而疯狂。
我由此页翻到封底马尔巴的故事,方明白尼采拥抱的马儿,恰是马尔巴拥抱的塔玛多德。
《明室》的读者都知晓,写完此书后的次年春天,罗兰·巴特在车祸中丧生。他进入景中,却因没有子嗣而无人拥抱,无人恸哭。他的幻象即使进入照片,也没有他人凝视。可怜他立在冬天的花园里,却找不到后人的思念,再也不能转换为超幻象。
马尔巴的故事,为罗兰·巴特揭开了蒙蔽图像的帷幕,也预示了他的命运。 对影三人
镜子仿佛照片,它们随时在等待“影像”的进入。
很久前的某一天,住院三年多的母亲让我拍张父亲在家里的照片给她看看。于是我拍了父亲在书桌前坐着的像。拍了两张,一张镜子里映出父亲的脸,另一张没有。冲洗时我选了前一张。
正巧那天看了一眼电视,央视戏剧频道,正在播一个新编的京剧舞蹈,取李白《月下独酌》的诗意。舞太新颖、直白,不习惯,却勾起对此诗的兴趣,诗云: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连续数日,这首诗歌一直萦绕在怀。一月一影,让醉酒的孤人刹时间有了相期对饮的友伴。再看给父亲拍的两张照片,倒觉得镜中无容貌的那张更有味道了。那空的镜子并非一无所有,它提醒我用观想而不是观看,把父亲的影像印到脑海里。 作者为父亲拍摄的照片 秋日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描述的正是身体和他的影子。分散后的影子留在相册里,成了残存在我们身边的魂魄,与下一代的生命伴随始终。
为父亲挑选遗像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在跟卧室里母亲的那张遗像作比较:他和她来自不同的照片,却好像出自同一个季节。那背景和主体都是秋天,鬓发有点萧瑟,精神却还矍铄。这也是我的唯一,有如罗兰·巴特选择了冬日,我选择了秋时。
对照镜中的我,居然和照片里的他们处在同一个年纪。我们都回复到了一个天高云淡的收获时节,只不过他们是在死后,而我是在另一个死后的生前。我们都已逝去,我们还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