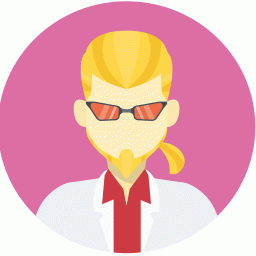济慈――“自然”与“天然”的体现者
时间:2022-06-03 02:17:48

摘 要:在济慈短短的一生中,对人生的意义和对美的强烈追求始终是他生命的主旋律。正是由于这种积极的人生追求和认真的处世态度,济慈才具有了对自然界的强烈责任感,才能够怀着一颗慈善之心去关爱自然、赞美自然,不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形成他的自然观。
关键词:济慈 自然 天然 美与真
约翰・济慈是英国19世纪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济慈在家庭悲剧、经济破产、无望爱情和事业挫折的一系列困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济慈以他诗人独特的处境、诗意的多面性、经验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矛盾性、语言的限制力与可能性给我们展示了其作品独特的魅力。诗人在诗歌里赞美、歌颂大自然的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没有单纯地沉浸于自然的美景中,而是利用在自然中汲取的力量乐观地面对人生的苦难。“真与美的统一”的美学想象是这种美丽意境内涵的指导思想,“天然接受力”是其美学理论与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济慈自然观的诗性内涵与精神形态
1.自然的美的真谛。“想象中的美即是真”。济慈才华出众,才思敏捷,他在诗歌创作中高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就是他特别强调“真美统一”的思想。“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在这世界这就是你们所知和需知的一切。”在济慈看来,诗歌创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通过“想象”创造出更好的诗篇。“想象”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把空间放大或缩小,把时间延长或缩短,“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它不同于胡乱的假想,“想象”发展到极致便是美。“让生翅的幻想,在不断伸展的思想中徜徉”。但“想象”的翅膀不管放飞多高,在济慈手中终有一线――它是真的,即不能凭空乱想。
2.具有东方神韵的自然与艺术之美。在群星灿烂的西方诗坛历史上,济慈不同于英国诗歌史上的其他诗人,也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在于济慈诗歌里独特的东方个性特征。我们可以借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把握其诗歌品味。《诗品》的根本思想认为好诗是自然之作,是天籁之音,而绝非人工所能比拟。天籁、地籁、人籁之区别就在天然还是人为,天籁不仅不依赖人力,也不依赖任何其他的外力,所以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希腊古瓮颂》与《诗品》的第一品“雄浑”有异曲同工之妙,济慈为至真的情感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达到永恒,达到至美;而“雄浑”的阐释是“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二者对诗歌的认识完全相同,即从本上都认为:诗人真挚的情怀是创造诗歌真品的原材料,艺术的本真是自然性、自然的率真,由本真的情感才能达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境界。济慈不也说:“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希古瓮颂》)。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3.生于自然,归于自然。遵照济慈的遗嘱,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个名字用水写成的人。”济慈遗言的本意不在于表现他诗人的独特风格,其深刻的寓意在于他要告诉后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地球上最多的是水,水是生命之母,生于水又复归于水。正如弗・卡普拉所说,“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
大自然不仅给济慈带来了美的享受,大自然所蕴含的蓬勃旺盛,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更是给诗人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和直面人生的力量。《蛐蛐和蝈蝈》一诗中,诗人以精细的观察抒写了夏日郊外的蝈蝈与冬夜炉边的蛐蛐交替唱歌的场景。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小鸟晒得发晕,躲进了清凉的树阴”之时,蝈蝈却在带头歌唱;在一片萧索,天寒地冻的冬天,其他动物蛰伏之际,蛐蛐却在引吭高歌,奏响自然的乐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生命的顽强的生命意识触动了诗人的心弦,诗人也像这些小昆虫一样,虽然现实生活面临种种磨难,但是,并没有向现实低头,而是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在给友人海登的信里,他写到,“不过我想,困难也能给人类精神增添勇气――它使我们将激情倾注在首要目标上。”
二、济慈的“天然接受力”
在理论上,济慈提出:诗人要有能力经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而不是烦躁地要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一些事情开始在我思想上对号入座,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种品质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像莎士比亚就大大拥有这种品质――我的答案是天然接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这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对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虑。
1.“天然”与“自然”。诗人幼时失去双亲,成年后又遭失弟之痛,小妹寄人篱下凄凉度日,二弟移民北美陷入经济危机,他寄予很大希望的诗作饱受批评家攻击,身患重症无法与心爱的姑娘结为连理,悲惨的人生遭遇使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饱受折磨。品尝着生活这杯苦酒,体验着个体生命的脆弱与无力,诗人需要汲取力量去与命运抗争,而亘古不朽,广博包容的大自然成为诗人的关注的对象。它的神秘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诗人,于是,济慈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在大自然的世界里寻找现实中缺失的美与命运斗争的力量。
2.“天然”与“真、美”。追求诗自身不受现实内在和外在生活的挤压,直入隐藏事物表象后的精神世界,完整地捕捉生活的真和美。诗之美,决定于诗人之美,诗人之美关键就在于人性的素养。诗的崇高与否,取决于诗人心中人性之塔的高度。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济慈告诉我们的不单是如何面对人世间的痛苦、丑恶、及黑暗等事物,“而是在精神上如何驾驭、超越这些事物所具有的‘不如人意的因素’,从而把这些事物和快乐、光明、美好的东西一起作为‘真’来认识、审度和观赏,以此取得心灵的宁静和愉悦。”而超越的关键也就是理解“美即是真, 真即是美”的关键。正是由于艺术家具备了此种质素,就没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因素”是不能“消散”的了。
3.“天然”与“淡泊”。济慈的《夜莺颂》与《诗品》里第二品的“冲淡”不谋而合,都有着同样的言外之音和韵外之致:诗人既不是想要责怪夜莺的欺骗性,抱怨尘世的苦难,也不是在做徘徊在二者之间的悲怆而徒劳的跋涉,整首诗歌只是诗人一种极其淡泊自足的心境写照而已。著名济慈研究者福格勒(Richard H Fogle)就认为:“济慈在《夜莺颂》里描述了一种强烈的美感的和想象力情感的状态,太炽烈了难以持久,它随夜莺的歌声升腾而起,消退而去,诗人记录下他的情感和踪迹而未作什么评论。”诗中“骗人的妖童”等语词是诗性语言使然,“骗人”指想象力与现实相撞后消失的情景,并无甚深意,不能纠缠于“幻觉”真的是否“愚弄了他”等;至于为何诗歌中出现诸多二元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起诗人情感平衡器的作用而已,是一种手法或诗艺个性特征,也是诗人自诩的“天然接收力”的思想体现。
济慈过了曲折但却诗意的26年,作为一个激情彭湃的年轻人,当伟大诗人的理想躁动于腹中,当世俗、私妄还未能太多干涉他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遗憾却将济慈生命的真实之魂永系于美的自然世界之中。在残酷的现实中,济慈把他的“心智”锻造成了独特的,求索的伟大诗人的“灵魂”。他曾躺在草地上让“灵魂”去与蓝天上飞过的鸟儿对话,他曾在月夜里用“灵魂”倾听夜莺的歌唱,他拒绝大城市,却体味着苏格兰一路的风景之旅。借问济慈“魂归何处”?与自然相融的“天然”――“积极”的诗之美的灵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济慈:《济慈诗选》,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司空图:《诗品》,杜黎均译注评析,北京出版社,1988。
[3]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东方出版社,2002。
赵玲洁、赵彦荣: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外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