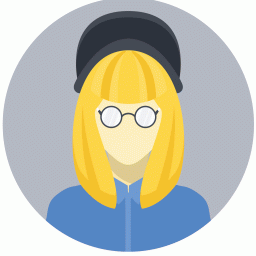王安忆:我们的工作就是制造幻想
时间:2022-04-29 01:11:00

最近,由王安忆编剧,吕凉导演的《发廊童话》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虽然与奥运“撞上”了,不过剧场依然座无虚席。王安忆似乎对此剧很满意,特地邀朋友再次观看。剧终后,一直很低调的王安忆热情地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记者:《发廊童话》似乎有这样的寓意: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然会丢失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就像剧中的妙妙对生活有了幻想之后,差点失去了爱自己的男友吉姆?
王安忆:我并没有想放入说教的东西,我觉得各个阶层都有各个阶层的困惑,我个人觉得,第一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幻想,第二不能有太高的幻想,而且不少这样的幻想是有模本的,是对另一种人生的模仿。
记者:观众看了戏之后,觉得这部戏很温情。
王安忆:这是吕凉的功夫,其实剧本里面还是有一些不那么温情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大款没有娶妙妙,这些很现实的东西被吕凉用很温和很巧妙的方式解决了。
记者:《发廊童话》的故事是否有宿命的意味?
王安忆:我不太用“宿命”这词,从一个起点又回到一个相似的起点,做一场梦,有一点意境,这不是很好吗?
记者:排戏前,好像有一些争议,认为你不太熟悉发廊的生活,《发廊童话》也没有反映出现实发廊中攸关利益等复杂关系,是否“发廊”在你剧中只是“底层社会”的一个代表?
王安忆:我的目的不是表现发廊的各种具体问题,我想表现的是里面发生的困惑,具体是哪个地点不是太重要,也可能是其他的小店。不过发廊更加好,因为它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系,会有邂逅发生。但是我承认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虽然演员演得很好,但是发廊妹的职业特色表现得还不是很鲜明,毕竟发廊妹与学生妹还是有差距的。
记者:刚才谈到了幻想,那么你自己会有怎样的幻想?
王安忆:我的幻想会用我的小说表达,所以我对我的生活挺满意的。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制造幻想。
小说是我的本业,编剧更像是做功课
记者:《发廊童话》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外在的冲突。
王安忆:对,这里的冲突不是太激烈,悬念不多,那么就应该用语言来取胜,想要吸引读者,就要把话说得有趣,要用对话来推动一些内容。
记者:剧中一些话是否引用了你下乡当知青时的语言?
王安忆:不是,这些都是生活经验中的话。其实戏中的对话不是那么生活化,我有意做得有点书面化,很多趣味是一种交锋,你想说服我,我想说服你,包括大款关于化妆舞会的双关语,是用了些心思的,不一定是哲学的高度,但都是些生活小道理。我看戏时发现观众对这些话有反应,说明都听进去了。
记者:写小说与做编剧有怎样不同的魅力?
王安忆:小说是我的本业,编剧更像是做功课,是一种训练。戏剧需要冲突性很强的核,这对我来讲不是很擅长,我比较适合做一些微妙的表达,那么这在戏剧里面就不是很合适。所以《发廊童话》也是根据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改编的。但是戏剧的魅力在于有充分的空间,让你创造对话。
记者:你曾说过:话剧是一个作家的最终完成?
王安忆: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话剧是一个作家的新高度。如果遇到合适的作品,我还是会改编成话剧。
记者:今后你也不会原创话剧?
王安忆:目前看来是这样的。
写作要与我的心理经验有关系
记者:你一直说小说技术很重要,甚至承认自己写作有些匠气,但是“技术”对于很情感化的写作来说,似乎不是那么褒义的词。
王安忆:一般作家对于技术这个词很警惕,因为很怕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才华、没有想象力的人,所以不提技术。其实技术是很重要的。情感人人都有,为何有的人能写小说,有的人写不出呢?情感最终还是要以叙述的方式来表现,要有语言能力、写作能力,这是最基本的,其实我们就是在用技术。
记者:那么情感的重要性呢?
王安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没有这些情感你根本就不能写小说,才华灵感这些都是没法谈的事情,天赋是上帝给你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可以商量的唯有技术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你是天赋型的作家吗?
王安忆:那我不敢这么说,只是我觉得我写小说还是比较胜任的,还觉得有点得心应手。
记者:你一直承认自己是“书斋型的作家”,那么是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你经验的缺陷?
王安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记者:有些作家在寻找经验,比如进入艾滋病村,进入另一个圈子,您会有这方面的举措吗?
王安忆: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合适,因为我写作的东西一定要和我本身的心理经验有关系,即便某一天我去采访调查,忽然知道某些事情,最终写和不写还是由我本身的心理经验来决定,如果引不起我的共鸣我也不会写。其实我曾经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就扔在那边了。作家类型不同,有些作家特别能把客观事情做一种描述,有些作家一定要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联系。
记者:那么在书斋中的话,您如何寻找创作的灵感?
王安忆: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再说“书斋”那个说法也不能那么绝对的看,我也在生活、在经历很多事情,我说我在书斋里,只是区别社会意识比较强的作家。
记者:一些作家出了成名作后就很少有新的作品,为何你一直能保持你不间断的创作激情?
王安忆:因为我一直在写作,没有放弃,没有受到其他东西的吸引。
记者:年轻读者关注大众小说,通俗小说,那么你在这个时作会感到寂寞吗?
王安忆:不会,因为我比较好命吧,通俗小说时代来之前,已经有了稳定的阅读群,读我小说的人不会特别多也不会特别少。
上海是我无法选择的存在
记者:你曾说上海的城市形态和话剧形式并不太契合,你觉得上海更适合滑稽戏,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我指的是上海的市井生活更适合滑稽戏来表达,因为话剧样式中地域性是很难存在的,要表达上海的地方色彩、风俗,话剧有点力不从心。
记者:生活于上海对你和你的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
王安忆:上海对我来说是无法选择的存在,它是我写作唯一能获得的材料、舞台、空间、故事、背景、情节、人物等等,上海不存在对我有什么影响,有影响就说明我跟它太疏离了,因为我是在这里生活的居民。
记者:大家都说,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很讲究很精致,在你看来上海的特色在哪里?
王安忆:都是从广告中得来的吧,我不晓得怎么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不觉得上海特别的精致。城市生活都有它的粗鄙性。生活在这里边那么深,在我看起来所有的人都差不多,我并不以为地域性有那么大的差异,生活的本质、要求都差不多,有时候在外部的生活上会有不同。所以关于上海特色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一个外地人,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是不可能用“特色”两字来认识她所生活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是同你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记者:为何你的小说中描述的大都是上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这大概是我生活在上海的缘故,我接触到的都是日常生活,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上海的一些外部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