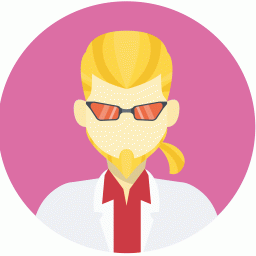“乐”的道德象征意义
时间:2022-04-18 08:38:54

摘要:《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电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关键词:《乐记》;道德象征;乐;德;个体人格;社会人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5-0107-04
《乐记》是先秦儒家遗留下来的关于音乐和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与总结性著作。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乐记》的研究甚多,在作者与成书年代、哲学思想体系、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教化等方面有了深入挖掘,但关于“乐”的道德象征功能及其意义则较少有人进行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乐记》及相关文献,以期阐明“乐”作为道德象征载体,对个体人格完善与社会人伦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乐”象征“德”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中,“象征”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传述手段。可以说,自《周易》开创“象思维”以来,象征成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要表达方式。如王夫之云:“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王夫之认为备受古代仁人圣贤推崇的“六经”莫不以“象”明义,其中《周易》更是这一思维模式的理论纲要。我们注意到,《乐记》在论述乐的功能时多采用象征这种思想传述方式,比如:“乐者,所以象德也”(《乐施篇》)、“乐章德”(《乐象篇》)、“乐者,德之华也”(《乐象篇》)等,通过“乐”的表象传述着人格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可见,“乐”决非仅是一种艺术形态,而是暗含着道德意蕴、彰显着道德功能的象征符号。以下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乐”与“德”的密切联系。
其一,“德上艺下”的审美传统。从审美伦理学角度看,“乐”与“德”体现为美与善的范畴。陈望衡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善与美的统一,美不美,其前提是善不善。”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乐”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富有“德”的特质。孔子在论及《昭》时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谓《武》时则遗憾道:“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原因在于孔子认为《昭》是赞扬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体现了“德”;而《武》是歌颂武王讨伐商纣,有宣扬征伐之义,虽为正义之战,但依孔子之意,它是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的。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强调人如果不仁不义,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没有仁义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礼乐背后之“德”的。
《乐记》总结并发挥了儒家“德上艺下”思想,提出:“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乐情篇》)所谓的黄钟、大吕是律名,干、扬皆为舞具。乐律、弹瑟唱歌、手执干扬而舞等外在形式,仅作播扬乐声之用,故日“乐之末节”,因此让儿童来表演舞蹈,让只晓声诗的乐师,面朝北面弹瑟歌唱;而“德成”之人君,因以道德成就的而能居于上位,此即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儒行》也指出“歌乐者,仁之和也”,歌舞音乐的和谐悦耳是因为有“仁”这一道德意义。“歌乐”的形式是服从于仁义道德之内容的。由上可知,在中国古代传统美学中,音乐承载的伦理意义远高于其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
其二,“德”是古代乐教的核心。在中国古代,音乐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使民众在音乐的濡染中完善自我,友善他人。而乐教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正得益于“德”这一重要内核。最早记载乐教的《尚书・舜典》中提到舜帝命乐官夔作乐,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乐”的道德核心作用,促使“胄子”们具备“直而温,宽而栗,刚而不虐,简而无傲”的品行,使情感、行为平和而适度,形成良好人格。《周礼・春官・宗伯》在记录古代音乐教育制度中,更是将“德”的重要性展现出来: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
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大武》……大合乐以致鬼神抵,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由上可知,承担乐教的教育者必须是“有道者、有德者”,教育的内容是“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德”――中,和,祗,庸,孝,友这些具体的德目是其教育的核心,是培育品德高尚的理想继承者的理论依据;“乐语”、“乐舞”则是以语言手法、艺术形式将“乐德”表现出来,目的是“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因此,在古代的音乐教育中无论是教育者、教学理论抑或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都与“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孔子尤为重视乐教的道德内容,《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推崇《韶》、《舞》,舍弃郑声,孔子的根据就是音乐是否具有道德意义,因为他主张的“乐”是融透了“仁”的音乐,是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的自然融和。通过“乐”的传播,道德以情绪的方式流出。徐复观先生指出:“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在艺术的熏陶中,实现崇高的道德人生,这也许就是孔子将“成于乐”视为最高修养境界的缘故吧!
二、“乐”的道德象征对个体人格完善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乐”具有象征“德”的功能。从个体修养的角度看,通过象征,“乐”确立了个体人格完善的坚定信念,并昭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据笔者统计,《乐记》中“君子”一词出现频率较高,达15次之多。这些“君子”精通礼乐文化,并善于利用礼乐以提升自身人格修养,达至“反情以和其志”的境界。
首先,“乐”是君子完善人格的象征。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应是品德高尚,又要精通“六艺”,德才兼备之人,即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在《乐本篇》中,我们看到了“乐”对于成为君子的重要性: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如上所言,其一,懂不懂得欣赏“乐”是“众庶”与“君子”之问的区别:众庶“知音而不知乐”,“唯君子为能知乐”。一般人只会沉醉于“音”的听觉享受,唯有具备道德修养的君子才能领略“乐”的内在韵味。其二,由于“乐通伦理”,“君子”“审音”进而懂得伦理政治,具有治国之素质。其三,君子懂得了“乐”就
“几于知礼”,于是就能“礼乐皆得”,而礼乐皆得到了,就是“有德”之人。孔子在谈论射礼时亦谓:“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礼记・射义》)也就是说,只有贤者才懂得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发而射中靶心。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那他怎能射中?《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亦谓:“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由此可见,能否听懂“乐”成了评判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标准。
在《乐记》的语境中,上古时期的帝王将相,德高望重、功业显赫,属“君子”之列。只有这些具备崇高道德操守的君子才能获得“乐”的歌颂与赞扬。《乐施篇》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大章》是用来表彰尧的德行的。《咸池》是用来歌颂黄帝的德行完备的。《韶》是用来颂扬舜能继承尧的德政的。《夏》是用来赞美禹的行政发扬光大的。殷周两代的乐都是赞扬能够尽到人为的努力。由是可知,君子不仅懂“乐”,还成为“乐”歌颂的对象,“乐”成了象征君子人格境界的符号。
其次,礼乐修养是塑造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乐化篇》中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能使人的内心十分平和,礼能使人的外貌十分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貌恭顺则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亦指出:“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而“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中论・艺纪》)这里的“艺”主要指礼乐。礼乐虽是“德之枝叶”,但德行的修养又必须以礼乐为途径。礼使行为面貌表现得文饰有度,乐能化育人的内在情感。《乐化篇》将礼乐之人格修养功能阐释得清晰透彻:“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可见,“乐”之修养以“治心”,“礼”之躬行显“庄敬”,礼与乐里应外合,相辅相成。但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先贤们似乎更重视“乐”的内在修养,“乐”能“至于天且神”,而礼却不能。陈来先生指出:“用伦理学的话来说,礼之性质与功能是使人得以‘他律’,而乐的性质和功能是使人得以‘自律’。”梁漱溟先生对此也有一段论述:“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因此,在礼一乐结构中突出“乐”的意义是不无道理的。“乐”能促使“他律”上升为“自律”,通过内在道德情感的激发,使外在礼的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
“乐”的这种诱感的功能,对于造就完善的人格境界是相当重要的,可能惟其如此,才备受儒家的推崇。那么,“乐”是如何激发人的道德情感的呢?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清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指出:“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也就是说,情感生活是音乐描摹的主要对象,情感的表达也是音乐最强有力的功能。人心感受外物形成各式各样的情感,在音乐的流动中直接地显现出来,引起人的联想与共鸣,无怪乎先人感叹“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篇》)!
然而,一般的音乐也只能激发、显现一般的“七情六欲”,对个人的修养并无益处。因此,古代的君子们尤慎“奸声”的侵入,试图在“乐”的陶冶中,激发内在的道德情感,不断地完善自身: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乐象篇》)
这是《乐记》比较集中论述君子如何进行“乐”之修养的一段话。由上述可见,君子从内外两方面进行修养――“反情以和其志”与“比类以成其行”。“反情以和其志”即是复返人的本性来安和人的心志,就是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让耳目鼻口和内心理智以及身体的各部分“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还需“比拟善恶之类,去其恶而从其善”,才能完成正心修身之事。然而,自我修身的完成并不是君子行为的终结。君子自觉本于自身之德行以教人,通过声音、琴瑟、干戚、羽旄、箫管这些符号形式将最美好的德行发扬出来。在音乐的推广中谐和人之心性,激发道德情感,使“民乡方”,从而移风易俗,天下安宁,这就是儒家所谓“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三、“乐”的道德象征对社会人伦和谐的作用
“乐”的道德本质作用于个体修身,可使人“心平德和”;而推广于社会则能“乐行而伦清”。因此,君子贤人“奋至德之光”于“乐”以教人;古之王者,更是制礼作乐,充分发挥“乐”的符号象征功能,传递着儒家传统的宗法伦理价值观,以期达至“天下之大齐”(《吕氏春秋・仲夏纪》)的社会理想。笔者拟从如下两个角度说明“乐”对社会伦理秩序之和谐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一,从先王圣贤对“乐”教的重视来看。《乐本篇》云:“乐者,通伦理者也。”在古代的养老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乐舞中体会尊卑上下之义:“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礼记・文王世子》)古代先王、圣贤素来十分重视“乐”的这种社会教化功能,《周易・豫卦・大象》日:“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君王期望通过“乐”这一载体来推崇“德”,因为“乐”不仅能使道德人格不断完善,更多的是它能唤醒潜藏于个人中的德性,使人“领父子君臣之节”(《乐情篇》),亦如《魏文侯篇》所言:“德音之音……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魏文侯篇》)。可见,“乐”这一道德主旋律,是凝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
第二,从“和”这一音乐的最高境界来看。“乐”将“和”视为最高境界。就音乐的形态构成而论,“和”是音乐成为艺术形态的基本条件。春秋齐相晏婴对音乐的界定生动地体现了“和”这一特性:“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乐之“和”境界不仅是音乐形式的“中和”之美,更在于可通过“和美”的音乐培养人格之“和德”,促进社会人伦的“合和”。《乐化篇》对这种社会人伦和谐的景象有如下描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是可知,“乐”所到之处皆可见“和”的印迹。在以血缘为脉络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体系中,宗庙的“和敬”、乡里的“和顺”、父子兄弟的“和亲”是社会最大的“德”。先王制乐之用意,就是为了使“上下相生”以“合和父子君臣”从而达至“附亲万民”。不难看出,“和”不仅是音乐本身的艺术境界,更是“德”这一“乐”的内在价值的充分体现。
但必须指出,“乐”具备社会伦理功能,其前提是音乐应当合于道义。因此,自《周礼》规定“凡建国,禁其淫声、放声、凶声、慢声”到孔子所言“放郑声”、苟子的“禁淫声”,都对“乐”作了严格的道德规定。这使得“乐”的道德特质更加清晰,道德象征功能更为突出。《魏文侯篇》中子夏在回答魏文侯时说:“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魏文侯所好的郑卫之音“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表演者男女混杂,父子不分。这是为先王、圣人所不齿的。反之,“德音”的舞蹈动作整齐、乐曲中和平正,其内容都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只有这样的“德音”才能发挥和谐人伦秩序的作用。因此制“乐”应“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化篇》),以避免“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使音乐符合“德”的要求,让“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从而“教民平好恶”、“感动人之善心”,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透过上述行文,我们可以看出“乐”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形式,《乐记》就明确地指出“乐”是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象征的文化形态。就历史发展来看,从原始社会时期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相关的乐、舞到西周以降,逐渐与礼相联并用,发挥着完善个体人格、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礼乐教化,“乐”承载着超乎其艺术本质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乐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