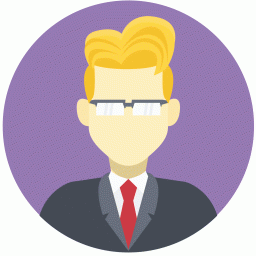斯里兰卡火车之旅
时间:2022-10-27 03:50:09

马克·吐温在《赤道环游记》中视斯里兰卡为“一成不差的东方”,那时,这里还叫锡兰。出于一种故弄玄虚的神秘感,很多人喜欢“锡兰”这个名字,符合西方人对东方异域的想象。
在马克·吐温眼中,这里的确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大文学家当年并未踏入斯里兰卡内陆,仅从首都科伦坡沿着西南海岸线转了一小圈,就凭借想象勾画了全貌。况且,以当年的航海技术,欧洲人能抵达的最东方也就是南亚半岛。再往东行,要靠运气和风向。根据马克·吐温的写作时间推断,他登陆锡兰应该在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刚刚赶走荷兰人,连同印度独占了整个南亚大陆。
斯里兰卡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在此期间建成。英国人的锡兰铁路公司从中部山区横劈出一条铁路,直抵科伦坡港。上等的茶叶、橡胶和椰子装箱入船,从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抵达地中海。
和中国一样,斯里兰卡的铁路算算也有100多年历史,但现实状况却天壤之别。这里的火车内燃机基本是上世纪50年代德国、英国的遗留物,最高时速80公里。
但是在斯里兰卡旅行,除了火车,也没有更优的选择。首都科伦坡到佛教古都康堤约有140公里,为了勘察路况,我花500元人民币,包了一辆面包车,一路暴土扬尘,整整6个小时。不包车更惨,从中部山区小镇埃拉到西南沿海的加勒,我鼓足勇气选择当地的大巴,整个车厢被挤成了一包衣服,即便这样,司机还在不断招揽乘客,直到把大家塞成照片。就这样走走停停,150公里的路从清晨开到日落,以至于晕头转向的我已经搞不清具体坐了多少个小时。
斯里兰卡没有真正的国道和高速公路,A级公路指的也不过是连接重要城市之间的唯一的一条双车道公路。
火车是仅剩下的,最可靠的选择。已经很久没有坐过这么慢的火车了——慢到看着天空的云朵跟着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慢到瞅见沿途低矮的草棚里本地人在熬制一种玉米浓粥,慢到仔仔细细擦亮沿途的风景,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是不是中国太快了?
康堤—努沃勒埃利
从古都康堤到山区小镇努沃勒埃利的这条铁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铁路之一。在关于斯里兰卡的各类旅行书里,穿越于崇山峻岭和高山茶园间的红皮火车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影像。
火车从康堤站驶出,窗外的佛塔和平原湖泊是古城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康堤依湖而建,是一座可爱的佛教小城,这里的佛牙塔保存着释迦牟尼的牙齿舍利。斯里兰卡有70%的人信仰佛教,对他们来说,康堤有如沙特的麦加。
当椰林与湖泊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山峦和梯田时,火车驶入著名的高山茶园区。绿油油、沾着露水的茶树铺满视野,它们整齐划一,生机勃勃,山腰间升起团团雾气,远望如《绿野仙踪》的奇幻梦境。
60年前,英国的立顿先生也是乘火车途经于此,从此正式展开他的茶叶事业。大大小小的原始茶园里,穿着彩色纱丽的采茶女像攀附在树上的蝴蝶,用长木棍小心地将最鲜嫩饱满的茶叶摘下,放在身后的竹篓里。
驶入原始森林后,天下起小雨,时缓时急。这条铁路线最高处达到6226英尺海拔,有无数坡道和急转弯,以100年前的铁路技术,建设难度可想而知。坐在两列车厢的连接处,我小心翼翼地将头伸出去,闻着雨水裹起的茶叶清香。
康堤与努沃勒埃利,这趟线路的起点和终点,连同科伦坡东北部城市锡吉利亚,构成了斯里兰卡著名的文化三角洲,也见证了古锡兰国昔日的辉煌。我读过一些斯里兰卡的历史,和世界上所有富饶肥沃的土地一样,这里自打分封划地,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复仇和死亡,循环反复,极庸俗的人类故事。
这片最繁华的北部区域也是最先被外来者垂涎并且征服的:16世纪葡萄牙海军登陆后,用枪和火药胁迫当时的科提国王投降,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殖民者砍伐树木,开垦成咖啡园,后来尝试种茶叶——殖民扩张使大规模的茶叶贸易成为可能。历经各种艰苦的试验,终于在1867年由英国人成功种植了20亩的茶树:这意味着,他们不用依靠中国的茶叶产量了。
今天的斯里兰卡,采茶依然秉持着当年英国人制定的严格标准,只有顶部在同一高度的嫩叶—当地人又称“嫩芽与两片叶子”—才能摘取,而且必须手工完成。一位当地茶农告诉我,1公斤新鲜茶叶卖150卢比(15元人民币)。
谈论艰辛的采茶工作,大部分当地人有一种“甘愿如此”的口吻,我曾试图探寻这种性格背后的成因: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让他们与世无争?还是400年殖民史造成的习惯和麻木?
总之,在斯里兰卡,外来者会受到上等的礼待,有时,他们的殷勤让我如坐针毡。他们谦卑地微笑,观察你的每一个需要,他们似乎认为“他者”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当你喝茶时,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当你入睡后,他们在屋外守候着,随时等待那扇门打开,有人向他们发号施令。
加勒—科伦坡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有一列令人难忘的水上列车。水天一色的奇异世界中,千寻和无脸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伴随着久石让的钢琴变奏曲《海》。其他乘客就像相机底片中人的阴影一样,安静地上下车,或在站台上等候着什么。
有迹可循的资料中,宫崎骏没有来过斯里兰卡,但这条沿着海岸线的铁皮列车的现实版本,却出现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城市加勒和首都科伦坡之间,一路沿印度洋北上160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沿海岸线铁路(全世界的沿海铁路只有4个。)
这条铁路途经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被视为斯里兰卡西部和南部出入科伦坡的主要交通线路。我提前一天去加勒火车站买票,被告知:不预售。问到具体时刻,售票窗口里的小哥摇摇头:“明天过来看。现在不知道。”
第二天一上车,我傻眼了:严重超载。过道、行李架、厕所里挤满当地人。想找到容身之处,要凭眼力身段还有运气。恰好一对父女下车,腾出了他们的位置:两列车厢连接处的上车口。即便如此,我的一半身子还是得挂在车厢外。
火车几乎每隔20公里就要停站一次。一路的风光谈不上旖旎,倒是令人难忘:一侧是椰林和村落,一侧是碎石海滩和大海。离海岸线最近时,距离不过3米,水花拍在脸上咸乎乎的。很快,我挂在车外的身体被晒得通红。
从加勒古城开出不久,一位胖胖的西方老太太挤上了车。她恳求我再往外“挂”一点,为她的两腿腾出站立的地方。广播里开始报站名,我一句也听不懂。“到科伦坡应该还有3个小时。”她提醒我。
“你听得懂当地语言?”
“简单的日常用语我听得懂,但是不会读写。”她用手绢擦着汗,亚麻衬衫开始出现汗渍。
老太太自我介绍是苏格兰人,18岁前在斯里兰卡长大,父亲是斯里兰卡茶园的殖民主。在斯里兰卡被英国殖民期间,成千上万的大不列颠官员被派到这里。
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住英式别墅,去专属的俱乐部,夏天打猎冬天品酒。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他们全家搬回苏格兰,她在那里成家生子,她的父亲去世了,几年前她的丈夫也去世了。“我特别伤心,决定自己出来走走,第一站就想来斯里兰卡看看。结果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觉得这里才是我的故乡。”
她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科伦坡一所国际学校做数学老师,因为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又搬到加勒附近的小镇,买了一栋隐匿在一片树丛背后的小别墅,雇了几个当地人照顾她的起居。白天上课,晚上喝茶读书,隔上几个周末去科伦坡采购,和朋友约会。
“每次去科伦坡的火车都是这么拥挤。”她安慰我,“而且爱晚点,今天这趟还算好的,最多时,能晚点一个小时。”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讨论这个国家给她的感受,大意是说,自从“我们”(殖民者)离开之后,这里就没有明显的变化。她指着沿海一栋漂亮的小房子:“你看,那是我姑姑原来住的房子,还在那里,一模一样,我18岁离开,现在再回来,这里似乎就没有变化过。”
我听不出她的语气背后到底是骄傲还是惋惜,的确,沿海一路西进,有很多破旧的棚户,瘦骨嶙峋的当地人坐在门口发呆,光着屁股的孩子在海边瞎跑,衣服晒在堆积成山的垃圾旁。2004年印度洋的那场海啸重创了这里。可是10年过去了,为什么还像是一片临时避难所?
斯里兰卡政府归咎于从1983年开始的内战,泰米尔猛虎直到2009年才宣布投降。(他们一直渴望在北方建立独立的国家)内战结束后,政府展开重建计划,中国是背后最大的援助人,前后大概资助了12亿美元。在我乘坐的那趟航班上,就有三四个工程师模样的中国男性。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援建的工程师。
一些看上去极漂亮和规整的海滩,隶属高档酒店和俱乐部。围墙内,有椰林和鲜花、躺椅和香槟酒,还有穿着白衬衫的当地侍者。本地人蹲在酒店门口,大门打开的一瞬间,他们立刻收起脸上困顿的表情,热情招揽游客乘坐当地的TUTU车:10块人民币10公里。
“斯里兰卡人数学好不好?”我问苏格兰老太太。
“很难说。这里很多孩子都无法上大学。”她谈论起自己曾经的学生:一对兄弟,哥哥很笨,弟弟的数学却极好,“弟弟现在在阿联酋航空做飞行员,他是家族的骄傲。”——她在强调,这是斯里兰卡本地人能找到的较好的工作之一。
此时,Google地图显示:火车已经驶入科伦坡。120多公里的路,又晃悠了4个小时。“科伦坡是这里最繁华的地方,大城市。”老太太强调。她推荐了一些地方,大概是她和她的朋友常喝下午茶的餐厅。直到快驶入科伦坡火车站,我才嗅到了一点城市的气息:三四栋高于6层的建筑物。
“再见。”火车还没停稳,苏格兰老太太就被人群冲下了车,她狼狈地卷起布袋子,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走出车站是科伦坡著名的贝塔区。街巷中挤满了棕色皮肤的当地人,穿着半截裙子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僧伽罗人,剃光头的泰米尔人,戴小白帽的摩尔人,来自印度大陆缠头巾的印度人,卖马匹的阿富汗人,以及其他形形的东方商人。烟叶的辛辣气味,丢弃的椰子壳的酸味,还有其他算不上好闻的种种气味遍布街巷,做衣服的印花棉布,粗陶、瓷器、大米,味道浓烈的咖喱、水果、蔬菜,令人眼花缭乱。
我没有在科伦坡过多停留,当晚就乘飞机离开了这座城市。从空中俯瞰,科伦坡的灯火真的很耀眼,在其他绝大部分漆黑一片的地区的衬托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