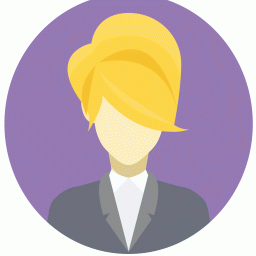川上:在沉默着的怀抱中的水静静地流
时间:2022-10-18 04:04:09
川上是个有故事的人,除了偶尔的只言片语,那些故事在静默的地方静默着,不为讲述,不为讲述中的流传。在川上那里,故事的内核不是传奇,是回味,在它们自己提出回味的请求的时候,分行的文字被写下来。
一个有故事的、情感丰厚的人极可能是内敛的,内敛的方式在诗中因人而异。川上的诗大多短制,不仅篇幅短,而且句子也短。比如曾入选《湖北新世纪十年诗选》的《尘埃》。尘埃一直在“自由地飞舞”,在空气中,在无形中,无论“我”是否看到。“我”必得感谢光漏,这被大光明“所漏掉的部分”;“我”也必得感谢尘埃,这被“我”所漏掉的部分;更多的感谢还是要给予“门外的大光明”,不是因为它普照众生,是因为它的无心之举照见了尘埃,让“我”看见了尘埃,也就看见了黑暗中的自己,也有一颗尘埃之心。
诗人川上是极其专注的,专注于某一对象,专注于某几个对象的某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专注带来/需要的是沉潜,是耐心。如里尔克所言,在耐心的尽头,是一整个世界。《脚印》与《尘埃》一样,显示了川上在写作中寻找/创建世界的基本方式:具体场域中的事物的踪迹,并最终让它们消失无踪。在《脚印》中,任何一只脚印都可以被诗人调换来充当诗的结尾,但唯有这只不知名的鸟留下的难以名状的脚印是最有意味的:你知道那是一只鸟的脚印,但若认真去看,又不知道是哪只鸟;它在那里,但早已离去。这种寻找/创建世界的基本方式,在《深夜》一诗中出之以看见、追寻,却一无所得,却心不甘情不愿的狗的视角。在我看来,诗人太像这条嗅觉灵敏、忠贞不贰的狗;诗歌就像是在那样一个时刻被抑制住的长吠。诗人反身追赶着生命道路上渐行渐远的脚印,又被那些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光与影从背后追赶着,它们请求被关注并给予意义。文字的王国终究是个虚幻世界,每一首诗都是自己的一只脚印,无从知道它们通向哪里。
“看见”是川上诗歌的核心词汇,目击道存则不妨看作是他追求的写作的理想境界。从发生学的角度说,目击是诗歌产生的基本前提;目击是否可以经由盘桓于事物或穿透事物而抵达道,或者让道在事物之中、之外浮现出来,并让人有所感知,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看见是具体的感官行为,道是近乎虚妄的心念;看见是肉身的功能,道是精神的诡异的氤氲。道不能直接被看见,也很难被词语锁定。就像川上说的,你若认真去看,很难辨认它是什么;你嗅到了它的气息而狂吠不已,到头来只能自怜自哀。
在看见对象的选择上,川上的诗大多取自平原乡村。他极少写城市,这一方面与他的成长背景和人生阅历有关,一方面可能与他对道之所存的理解有关。他的诗并不属于“乡土诗”,主要原因不是他的冷抒情风格,是他并不在意乡土的变迁及其折射的时代内涵,以及因此投射其中的或欣喜若狂,或悲痛不已,或追忆美好童年时光的情感(这是一般“乡土诗人”的写作路数),毋宁说,他更关注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的个人记忆,和在不断返回、重新看见中所得印象;尤其是,他更关注乡村中不变的那些部分――那些部分也不可能不变,只是他想赋予它们永恒的面孔,至少在诗中。比如《白夜》即是诗人“看见”的结果,是孤独的(“没有人/轻易出门”),也是微醺的――“越来越轻/越来越醉”既写人也写月光,人与物浑融一体,没有界线。月光是古典的,稻场既古典又现代,是两者交融的一个场域;“前世”牵引出此在的“稻场”,两者无非是“空无一物”。道可能在前世,也可能在此地,但谁能说清“空无一物”的意指?
当川上在诗里使用“我”,他通常是在强调看见及其对象,由物及心;当他使用“他”,“他”其实是“我”的他者化,即诗人用以反观、反省自我的一个虚拟主体。这类诗有《发光体》等。它们并没有改变川上诗歌冷静、抑制、持重的风格,但句式往往在不经意间拉长,犹如“在沉默着的怀抱中的水静静地流”。他者化的方式使诗人可以暂时出离虚空/虚无感,在反求诸己的过程中,那双“内视的眼”不可能不带着“我”的人生感慨,像许多先辈诗人在水边、在风中、在明月下发出的如许感慨。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