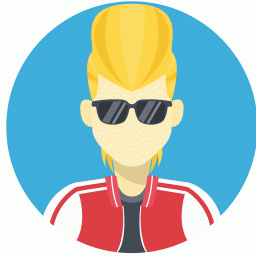家伙们的反抗
时间:2022-10-02 02:24:18
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出版于1977年,迅速在社会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如果今天它尚未被正式冠以“经典”头衔的话,也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研究、教育学和民族志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作者:[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华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
1970年代中期,威利斯来到英格兰西密德兰郡的一个小城市――书中称之为汉默镇(Hammertown,意为锤子城),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自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此城一直以制造业立命,是当仁不让的螺母螺钉镇,彼时也同样陷入了整个中部腹地的工业衰败。威利斯深入城内的一所全日制高中,与12个不爱学习、不服管教的工人阶级子弟――即他所称的“家伙们”――深入相处,通过观察、采访和组织讨论,记录他们的言行,进行个案研究并加以整体分析,试图以此解答“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书的副题。
现代公共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所宣称的受教育权利或文凭供给上的人人平等,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家伙们却不领情,他们以自己的种种反叛行为让上述目标落入了空谈。在威利斯的书中,家伙们对文凭缺乏兴趣,他们拒绝完成功课,并嘲笑爱学习的循规生(书呆子)。他们以一种仪式化的风格和热情“找乐子”,处处与制度作对。他们上课睡觉,穿奇装异服,脏话连篇,抽烟喝酒(“他们大部分都抽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人看到在抽烟”),打架斗殴,欺凌弱小(尤其对少数族裔和女生严加排斥),在性方面亦屡屡犯禁。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两个人由于青春期的躁动或某一天心情不好而产生的偶然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生存常态。威利斯称之为“对抗性的文化”。
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主动放弃了成为白领并迈入中产阶层的机会,从而选择了子承父业,从学校一步跨入了车间。换言之,他们的机会并非被外力剥夺,而是主动放弃。
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家不会喜欢这样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共教育的目标在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身上落空,首先应该从社会,甚至从教育制度自身上寻找原因,而不该拿学生是问。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地给家伙们挂上了失败者和受害者的标签。
威利斯的观察提供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校园里的对抗性文化与工人阶级对知识权威的反抗一脉相承。“工人阶级文化普遍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一个工人从火柴盒背面抄来一句话,写成很大的标语放在车间里:‘一盎司的直觉可以媲美整个图书馆的学位证书。’”
对这样的口号,我们并不陌生。就道德至上的教育环境而言,“学校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威利斯写道,“学校里几乎没有直接的强制或压迫,但对道德可能性的范围进行了极大的限制。每件事都紧凑有序,每个故事都有相同的结尾,每个类比都用相同的类比物。”
家伙们的种种反叛行为有一个中心点,即男子气概的张扬性外露。殴打男同学如此,在女生面前的污言秽语亦然。父亲回到家时,不可避免地带回了自己的车间文化――工友关系同样以男性气概为主导,同样充斥着对新工人和瘦弱工人的肉体欺凌。“男孩的成长和他日益增长的文化信心,通常把他置于同父亲竞争、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母亲的位置上。他变得不再喜欢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父亲处于同一个世界:那是崇尚独立、身材健硕和象征性威胁……的男性工人世界。”与此不同,威利斯看到,“中产阶级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依赖性的。”中产家庭的目标与学校的目标一致,甚至比学校更重视文凭教育的重要性。
家伙们对文凭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他们而言,正如制度界定的那样,‘文凭’就是知识权力的爪牙。因为他们反抗知识,所以他们也必然抵制和怀疑文凭并使其失去信用。”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背离了公共教育的“好意”,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生活,进入车间,“体力劳作是代表、表达男性气概和反抗权威的途径。”
威利斯的观察并未局限于学校。他注意到,进入就业市场后,家伙们往往比循规生更受雇主们的欢迎,因为他们对工作抱有相对较低的期望值,更容易对自己的岗位和工资产生满足感。相反,“循规者也许会发现,他们最终的职业‘体验’非常令人不满,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也许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幻灭感’,而‘家伙们’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对劳动制度进行分析时,威利斯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沿袭。他使用我们熟悉的剥削和剩余价值概念,也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强调工作在本质上的无意义。他指出目前各种文凭的激增,实乃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束缚。
总体上而言,《学做工》是本非常好读的书,文笔鲜活而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干劲十足的青年学者(威利斯出版此书时只有32岁)的敏锐观察,也不乏70年代的嬉皮特征――它本身也有某种反抗习俗的味道。前勒口上印有作者小照一幅:长头发,小胡子,黑眼圈,工装布夹克,不打领带,时代特征鲜明。
但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不以怀旧的眼光看待此书呢?或者说,它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独特的意义?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由我们的社会学家(也许还有教育学家)来回答,但我希望有。至少我希望,我们能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中学里的“差生”――我们自己的家伙们,不把他们视为受害者或失败者,承认他们也有选择的权利。谁能否认呢――也许他们只是更早地看透了那些注定无法实现的承诺。
《学做工》中译本收入了威利斯1981年所写的一篇后记,他在其中就女性主义者对本书的批评做了较多的辩解。此类批评认为,他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在学校和就业市场上受到的歧视着墨太少。这是事实。但是让威利斯这样一个白人男性学者对女生做如此近距离的调查,是不是太艰难了?
在范立欣2009年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女儿不顾父亲的反对,坚决辍学,像父母一样前往广东打工。她在影片中最后出现时,是在一个舞厅明灭的灯光下,在一群青年人中间跳着舞。她没有表情。许多人也指责刚刚出版的《打工女孩》一书,认为作者对弱势群体的悲惨命运视而不见,而重在记录女工们对实现自我、改变命运的自信。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此书的真实和受访者的真诚?
威利斯对家伙们的观察,或许也可以作为参照,让我们对当前中文政论作者对下流语言的偏好有一个类弗洛伊德式的解读。在通常发表于互联网的文章中,所谓意见领袖们大量使用与性有关的词汇,来阐述其政治主张,或与对手展开辩论。在威利斯的书中,家伙们使用的语言“比‘书呆子’所用的要粗暴得多,充斥着随口而出的咒骂,用起本地方言和隐语时亦力道十足”。某些政论作者和家伙们一样,想必将污言秽语视作男性气概的重要表征。他们也经常使用“常识”这个词,来嘲笑对手的理论体系。
常识即直觉经验,正如那句在车间里放大的火柴盒背面的口号:“一盎司的直觉可以媲美整个图书馆的学位证书。”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一周书情
《经济学原来这么有趣》
作者:钟伟伟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这是一本介绍经济学大师及其思想精华的图书。它虚拟了18堂神秘课堂,邀请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18位经济学大师逐一走进课堂,讨论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话题。
《春天在哪里》
作者:阿乙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本书收录九个故事。故事的原型大多来自作者与闻的民间轶事,情节急转直下,带有一种原始的恐怖;而作者则像悲伤的猎人,埋伏在这些故事的转角处,等着给你当头一击。
《致青年电影人的信》
作者:[美]霍华德・苏伯,赵晶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本书是UCLA电影学院教授霍华德・苏伯为初入行的青年电影人答疑解惑的一本书信集,涉及了导演、制片、编剧等各领域,可以帮助你了解业内规则,抛开偏见,正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从新手成长为一名专业电影人。
《越弱越暗越美丽》
作者:李淼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本书从生活的最细微处开始着手,用生动有趣的语言为我们揭开了物质世界中那些简洁又美丽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