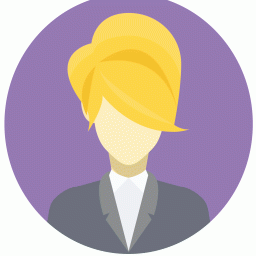射电天文学在中国的爆发
时间:2022-09-27 10:17:56

今日世界千变万化,讲话得分外小心,否则很容易闹笑话。上月底我对一群商学院的校友介绍过去一个世纪宇宙论的飞跃发展,“想当然”地加了一句:这一切虽然精彩万分,但看来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国人绝少感兴趣,科研投入更是空白一片。当时前排有一位学员很礼貌地轻轻嘟囔“不是的,不见得……”,我没有在意,他也不好意思继续发挥。短短一星期后,报上刊登出全球排名第四(在亚洲则排第一)的上海6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落成的新闻,证明自己孤陋寡闻,大错特错,但后悔已晚,因为课程已经结束,要更正也来不及了!
但即使是“想当然”,我的直觉为什么会错得那么离谱,其根源到底何在?这倒要好好研究,好好恶补一下。其实,只要看看排在前五六位的同类望远镜(所谓指向完全可调控的单碟射电望远镜totally steerable single-dish radio telescope,即锅底状的巨型无线电波接收或者发射天线)是何时何地落成,中国又是从何时开始建造这种天文仪器,那么真相似乎也不难明白。
这类望远镜最庞大,堪称“老大哥”的,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位于“绿岸”Green Bank的100米口径大碟,它在1962年落成,那是美苏展开太空竞赛的产物。排第二的,是1972年落成的德国波恩艾浮斯堡Effelsberg 100米口径大镜。排第三的,是1957年落成,口径76米的英国Jodrell Bank罗威尔(Lovell)望远镜。它曾经一再被用作美国太空计划的通讯天线,包括接收信号和发射重要指令;它又是西方国家监测苏联太空计划一举一动的间谍天线,曾经接收苏联无人登月器Lunar 9所发送的月球表面图片,甚至将之在报上抢先发表!至于排第四的,其实还轮不到10月落成的上海大镜,而要数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近郊所建立的太空远程通讯中心(CDSCC)大镜,它在1965年落成,口径本来只有64米,但在1987年扩展到70米。其实,在1960年代,这中心一共设有3个太空跟踪站之多,它们都是为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其他太空探索计划的通讯需要服务的,计划完成后,跟踪站随而关闭,只有这70米镜和苏联在克里米亚地区的Yevpatoria 70米镜(它的特点是具有极大发射功率)一样,成为那个火红年代遗留下来的见证。
除此之外,在澳洲新南威尔士还有一台64米口径帕克斯Parkes射电望远镜,它在1961年落成,本意虽然是为天文研究,事实上也多次在美国阿波罗计划和其他太空计划中担任通讯接收天线任务。由此可见,射电望远镜一方面是研究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的仪器,但更是推动太空计划不可或缺的基础通讯设备,以及了解、窥探、监测其他国家太空计划、设施的基本手段。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是太空竞赛的产物。
从这角度看,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轨迹就很清楚了。它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以至20世纪末那20年可以视为起步和学习阶段,它以学术研究为主,而颇受资源和技术能力限制。例如,科学院在北京密云设立射电天文观测站是60年代的事情,到1985年方才建成以28台9米镜为基本元素的1.1千米直线镜阵,1990年建成第一座15米镜;上海畲山的25米大镜于1986年落成,主要是作为“超长基线干涉仪”的一个元素,参与国际合作;科学院乌鲁木齐天文站在1993年建成的25米镜的功能也相同。但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积蓄足够经济和技术力量,在嫦娥探月计划(2003年正式启动)的强大刺激下,在过去10多年间,射电天文学就迎来一个爆发性阶段了。它的主要标志是密云的50米大镜在2002年设计,2003年选址,2004~2005年组件安装,2006年和昆明凤凰山的40米镜同时落成;它们的主要用途除了原来设想的脉冲星观测以外,就是负担与登月计划特别是嫦娥一号和二号相关的通讯任务。
至于上海65米大镜在2008年立项,2012年落成,则可以视为这第二阶段的完成,因为它连同畲山(原有的25米镜)、密云(50米镜)、昆明(40米镜)、乌鲁木齐(25米镜)等其他4台口径大致相当的射电望远镜,正好构成一个立足中国本土,整体口径达到两三千公里之巨的超长基线干涉仪(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eometer,VLBI),其作用的原理是:通过将这些散处远距离的望远镜同时接收到的无线电信号,以原子钟调校到同步而相互比对参照(也就是所谓“干涉”),那么整个系统对于所接收信号的方向的分辨能力,原则上将与一个口径两三千公里那么大的射电望远镜相当。例如,倘若所接收的是3厘米波长的无线电波,即所谓微波(microwave),那么这干涉仪对来自月球那样距离(约40万公里)的信号,其空间位置分辨能力大约可以达到5米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望远镜的角度分辨能力大致等于信号波长与望远镜口径比例的1.22倍。这样的方位分辨能力对于登月器位置的测定、控制和调整,大体上已经足够。当然,它是可以通过应用更短的无线电波,或者更长的干涉仪基线,而改进的。无论如何,从以上射电望远镜发展的简略历史可见,毋庸讳言,西方和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都和太空竞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说在某一阶段是由其拉动也不为过。换而言之,射电天文学的技术和太空计划是孖生兄弟,因此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那是我“想当然”之际所完全忘掉了的。
不过,这倒也不能够说是真相的全部,因为科学可以从原理走向实际,也同样可以因实际发展而反馈纯粹学术。例如,德国的艾浮斯堡100米大镜,就始终是完全为学术服务。同样,中国科学院也并没有以最近10来年的发展为满足,而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雄心勃勃地更进一步,争取全球射电天文学领先地位。这可以从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两个最新发展看出来。其一是已经在贵州大窝凼一处克斯特(Karst)球形低洼地动工建造,名为“FAST”的500米口径固定单碟天线。它从1994年开始考虑和研究,2007年正式批准,预算7亿人民币,2011年动工,预计2016年落成,构想 和美国波多黎各300米Arecibo射电望远镜相同,但规模更大,设计更先进精良,落成后无疑即将取代后者已经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龙头地位。其次,2012年11月底在乌鲁木齐所召开的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正在论证一台110米口径全方位可控单碟大望远镜的构想,它计划投资16.5亿人民币,将坐落新疆东部的奇台县石河子村(因此称为QTT,奇台望远镜),预计2020年底落成。很显然,从规模和设计看来,它也同样是要取代美国Green Bank100×110米椭圆镜已经维持了60年的老大哥地位。
关于这两个设计或建造中的巨大望远镜,还有几个基本观念需要在此厘清一下。首先,它们的功能并不是要更精确测定远方信号的位置,那基本上是由众多望远镜所组成的“干涉仪”的基线长度决定。它们的真正作用是在于增加灵敏度,以接收、分辨和分析来自太空深处极其微弱信号(例如宇宙形成之初的各种信号),因为信号收集能力是与望远镜的面积亦即其口径平方成比例的。其次,这两个耗资十数亿的巨大计划并不是以投入更多资源的方式来建造比前稍胜一筹的同样仪器,而是以更新、更精良的技术来全面提高、改进这些仪器的效能。举个例子,由于过去数十年自动化技术的飞跃进步,所以这些新望远镜的镜面都已经不再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些以静态钢筋铸造的网状曲面,而是由数千块各自以传感器和计算机自动调节其位置和取向的金属面板,这样无论风速、温度、整体指向如何,望远镜都仍然可以维持其抛物曲面形状,而将误差保持在毫米范围以内。因此它各方面的性能比之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后,中国虽然对这些巨大计划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但发展方式与策略却并非着重独力推动,而一直强调全面的国际合作和参与。事实上,开放和国际化可以说是它的主导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射电天文学在21世纪的“爆发”不但是中国的更将是世界性的,它将带来宇宙论、物理天文学,以及射电探测技术等各个前缘学科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