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20年转型为何难实现
时间:2022-09-23 09:47: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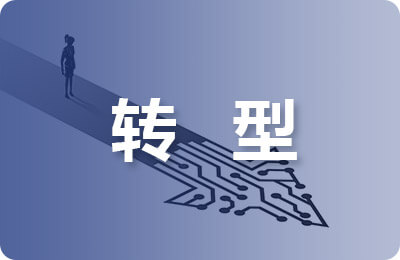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这两年来我们的改革还是有进步的,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但是根据我们21世纪初期做过一次,那个东西很容易走回头路,还是要把它制度化。
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
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用20分钟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有一定难度,从哪里讲起?我就用了我们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主题,按照逻辑顺序稍微做了点调整,把动力和创新的地位调了一下。能够解决前面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所以又加了一个改革。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五个问题――“危机、转型、动力、创新、改革”。
高杠杆率加剧系统性风险
从2008年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起,对于避免危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方略。这两种方略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是不一样的。根据今年在金融40人论坛的一次讨论,把它归结为两种:一种分析的思路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外一种分析思路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09年中国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长速度顶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增速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于是就引发了一个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系统性风险。怎么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是最近两三年大家讨论的一个重心。
从需求侧进行分析这种思路,通俗的说法叫做“三驾马车”,总需求是由三驾马车组成。其实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是四驾马车,我们一般说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进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增速下降?是因为三驾马车的动力不够。
在2009年财新峰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三驾马车这个分析框架有很多缺点,它实际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出来的。按照凯恩斯主义来说,是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和财政赤字决定的。
当时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有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不是正确,现在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的分歧也很大,但假定它是对的,在理论上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分析。
可是我们这种意见好像没有多大用处。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很重要的资信机构,它们的分析都是依据三驾马车,由这个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就很明显了,就是增加投资。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能够增加消费吗?不能。能够增加进出口吗?不能。最后就落实到一点――增加投资。
但是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限度,因为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结果就使得我们的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按照各种各样的分析,大概三个方面的负债: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已经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从政府、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还是从这里分析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主管这方面的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地批项目、找钱。过去批了项目,地方就上,但是现在有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有进步,不但要批项目,而且要找钱。所以这个路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路子是从供给侧、从供给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以前用一个函数来表达这个分析框架。今年4月,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余永定教授和刚刚故去的青木昌彦教授认为,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供给侧去分析,提高供给的各种因素、各种动力去分析。生产函数无非是三个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余永定教授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青木昌彦教授转用了一个所谓库兹涅茨进程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指出了现在存在的问题(网上能找到这篇论文,大概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这个题目)。
在现存的问题上,我们三个人的分析几乎是一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个非常明显,从2009年到现在,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它的效果急剧下降,现在增加投资几乎对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杆率不断提高,所以造成了危险。
以投资为动力,转变为创新效率提高为动力实现增长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因为劳动人口红利的减少,由于――用青木教授的话来说,库兹涅茨进程――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效率有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结束。
剩下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计算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实现增长。也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按照这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转型,也就是我们题目的第二项。
怎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呢?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
这个源泉因素是什么?刚才已经说了,从过去以投资为动力,转变为创新效率提高为动力实现增长。但是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没有实现呢?其实我们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就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的一句话,“存在体制”。九五计划有进步,十五计划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有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