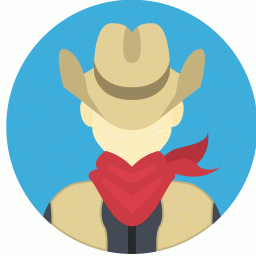“远哉遥遥”与“苍凉从容”
时间:2022-09-15 09:50:12
摘 要 鲁迅在其小说《社戏》中书写了一段“我”幼年月夜乘船观社戏的难忘经历,张爱玲在《异乡记》也书写了一段异乡聆听绍兴社戏的独特感受。同样是社戏,鲁迅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回忆表达了对民间淳朴文化的肯定态度,而这种文化作为另一种“呐喊”的声音已经不复存在。张爱玲则从旅途中这段不和谐的歌声里体味到现世的苍凉与历史的悠远。
关键词 《社戏》 《异乡记》 社戏
一、《社戏》中的社戏:另一种“呐喊”的声音
在对待传统戏曲的问题上,鲁迅一方面坚持对其思想内容的批判,即批驳其中宣扬封建奴隶思想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大团圆的腐朽内容,反对这种“瞒和骗”的艺术;另一方面,鲁迅又对其故乡的社戏极为推崇,他认为这种民间艺术不仅显示出底层人对正义和美的追求,更包涵着不屈不挠的复仇精神。
这两种态度映射到《社戏》这篇小说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构,首先是回忆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两次看中国戏的仓惶经历,终于与中国戏“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掀开这不愉快的一页,记忆里埋藏着幼年月夜乘舟观社戏的难忘经历,在追忆过这些美好记忆之后,在结尾“我”又感喟“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在文本中,“我”的关于幼年看社戏的回忆:并不翻跟头的铁头老生、被打的红衫小丑和执马鞭的花白胡子、唱起来没完没了的老旦,似乎观众们关注的重心也并不在于舞台多么优美或演员的表演多么精湛。而“我”的欢欣则更多地来源于与小伙伴们的陪伴和类似冒险的航船外出,而综观全文,“我”所年年不忘的好戏与好豆也有一个存在的背景,那就是“我”在平桥村里向来所受到的优待和无需用功读书的轻松自在,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作为铺垫,再精彩的社戏恐怕也难以令“我”终生难忘。
而如今,这种自然而富有乡野灵气的戏剧却要局限在戏院中演出,“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观戏的人全然已没有乡民们的悠然洒脱,观众们大多是为了一睹名角风采而来,看戏成了表明风雅的一种方式,艺术水平的高低并无号召力,让人们聚集到戏院的是他人对自己的品味的评价,焦点不在于演出的戏曲,而在于观戏的这种行为。
在封闭的剧院里上演水乡的好戏使看客头昏脑眩,那么在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中猛烈“呐喊”会不会一样让人吃不消呢?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卓越旗手,从《狂人日记》开始,他以笔为刀,对中国“吃人”的封建旧伦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态度上亦是如此,只是,在这呐喊的最末,他大概想起,这锐不可当的呐喊声潮是否也会像剧院里的“冬冬”,让听众头昏目眩,因为自己也曾是这铁屋中的一员,自己深知,这“大叫大闹”分明是不适合的。真正的好戏,只好到野外去上演,但昔日那淳朴的乡民之谊和月夜豆麦的清香也都消失不见,鲁迅只好借着营造回忆来发出另一种“呐喊”的声音,不仅仅是社会的腐朽黑暗值得斗士们为之振臂高呼,传承数千年的民间文化的衰落同样令人痛心疾首,这淳朴自然的民间文化的呐喊声音却无比微弱――“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怆然。
二、《异乡记》中的社戏:“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
张爱玲曾谈过,自己虽然听不懂戏曲的唱词,对表演的妆容和衣饰也颇为外行,但是关注的焦点在于戏曲的传承性和象征性。在她那里,传统戏曲唱成了何种腔调并不重要,她关心的是这古老的声音是如何唱出来的,唱出来些什么样的故事。
《异乡记》里的社戏是由被请到民宅的绍兴大班表演的,同样是月夜的环境,张爱玲写到这社戏时只有听觉感受:一个单音延长到无限,笛子声“小小的尖音,疾疾地一上一下”唱声和伴奏声自顾自地各不相干。同时,这两种声音构成的不和谐中间竟然还各有各的不和谐之处,唱声中,十五六岁的歌者跟不上过高的调门,唱得声嘶力竭,歌者却还不慌不忙;伴奏中,笛声一扭一扭地高低长短不一,“像个小银蛇蜿蜒半路,半晌,才把人引到一个悲伤的心的深处”。
然而,在这多层次的不和谐声音之中,张爱玲却感到“这声音是这样地苍凉与从容”,这与她一向秉持的“参差的对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是相符的,人人都生活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中,而每个人又各有自己的小世界,张爱玲常常慨叹:“这是乱世”,乱世中的人们顾不得别人,只顾得自己的一方凌乱天地,正是这样凌乱的世界与凌乱的人生,构成了一出时代的大戏剧,历史也无非就是这样一代代演进过去。
张爱玲的文章通常没有明显的政治指示,她往往通过某个细节一笔带过。《异乡记》写于1946年,时局不安,张爱玲个人生活也颇不平静,在行旅中“遭遇”了这段古意深浓的社戏,自然会勾起她的古今怀想,戏里搬演的都是些“古来争战”的故事,是“争战”而非“征战”,说明争夺的势力不只单独一方。古来纷乱的时局,用自古传承下来的戏曲强调唱出来,竟是苍凉从容。每场战乱都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瞬,再宏伟的争战目标溶合到时间的长流里都是虚空的,而这亘古流传的戏曲,尽管通俗,却浸渍了千百年来人事的演义,承载了每个历史个体的人生传奇。
张爱玲的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的英文名称是Still alive,宏大的历史需要浓缩到戏曲中,才能在后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再重演一遭,这样一代代流传下去,再恢弘的当年也演化成了古久的日常。所以这社戏在张爱玲听来“简直像一个老妇人微带笑容将她身历的水旱刀兵讲给孩子们听”张爱玲在写作中一向注重探讨历史的宏大和普通人日常的琐碎,而这社戏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纽结,将二者牵连起来,历史都是由普通人的生命汇集而成的,点点滴滴的日常性是历史的基础,嘈杂的细小声音聚合成一个习惯性的唱腔,
对于《社戏》中幼年观戏的“我”来说,月夜里的水乡舞台像“画上的仙境”,远远地观望着充满神秘的吸引力,行到近处,虽然令人稍微失望,一旦离开之后,仍旧令人留恋。纯朴自然的民间文化体验已经渐渐变为一个飘渺的梦境,遥不可及。鲁迅笔下的社戏出自于著名的绍戏《游园吊打》中最精彩的一幕,这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与作者怅惘的心境比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纯真幼年的怀念和乡土民风民俗的珍视,它们与月光下的豆麦的清香一同飘散了,再也难以捕捉,确是“远哉遥遥”。
《异乡记》中的社戏唱得却是古史正剧,这正剧也是一种反衬,作者在未知的行旅途中承受着环境与内心的双重煎熬,这出社戏似乎给了作者以安心的力量和来自远古的安慰,这戏唱得越是从容,就愈加反衬出世事的动荡,社戏给作者以苍凉的人生启示,现实与历史就是一番参差的对照。
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社戏似乎隐涵着一丝相近的意味,张爱玲在卧听绍兴大班的社戏之后目光所及月白色的院落和朵朵淡白的云,悠然恬淡的景色是她内心平静境况的写照,接着她便写下了一句与“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极相似的句子:“晚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浅色的明亮的蓝天”。
纯朴的民间文化渐行渐远,历史是温情的,她记录下每个人的故事,以供后世凭吊;但人有时却是薄情的,因为人们常常不能理解历史温情的暗示,就像《异乡记》里不耐烦社戏的年青人:“这种戏文有什么好看?一懂也不懂的!”鲁迅为民间文化精神如梦一般的消逝发出一声另类的“呐喊”,张爱玲以社戏参悟历史,在历史中找到了现实碰撞的出路,历史是“远哉遥遥”了,更为苍凉的是,历史中的这一份从容无人能懂。
注释: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张爱玲.异乡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