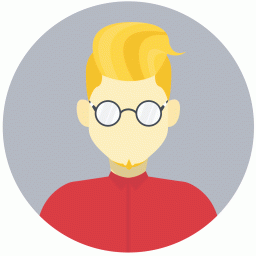江嘉良 我不做老大很多年
时间:2022-09-14 09:53:04
乒乓球之所以是“国球”,是因为她的博大精深――很多很多明星、很多很多经典战例、很多很多精神财富、很多很多奇闻轶事……
因此,对于乒乓球,我有很多不太了解、想了解更多更深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凡遇到乒乓界的人,总是希望能“求解”。
在不久前“纪念容国团首夺世界冠军五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又见到了江嘉良。和江嘉良有多少年没见过面了,我自己也记不清,可能五六年、七八年、或者十几年。他还是那副很干练的劲头儿,那种感觉不太好用今天人们常用的那个“帅”字形容,而适宜于过去常用的形容词:“精神”……
正好借此机会,弄明白关于江嘉良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一个团队里,那个球员能够做领军人物,最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愿不愿意做这个老大。
主将
站得出挺得住
1983年第三十七届世界锦标赛,江嘉良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大赛的主力阵容中,而且在团体赛的所有场次中都为中国队“打头炮”。那届比赛,是许绍发第一次出任中国队总教练,而江嘉良正是许绍发的“嫡系”弟子,但是就打法而言,江嘉良的直板正胶打法并非“秘密武器”,他能担此重任,显然是因为身上所具有的“主将气质”。
江嘉良是1979年进入国家队的,1982年年底,他参加了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这个比赛现在叫瑞典公开赛,因为是每年年底举行的传统赛事,当时中国队把她作为一次重要的练兵,并且会把运动员在这一比赛中的表现,座位确定第二年世界锦标赛团体阵容的重要参数。江嘉良在这次比赛中的出色成绩和精神面貌,使他得以在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时,就成为中国队的主将。
从那以后,江嘉良参加了四届世界锦标赛,获得了两次团体冠军和两次单打冠军,成为继庄则栋、郭跃华之后,第三位蝉联男单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
体育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由于他们曾经取得的杰出成绩和他们身上特有的气质、魅力,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公众视野里,他们都能始终“活”在人们心目中。
这种人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体育明星”。
江嘉良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若即若离,甚至不再在主流媒体“特别关注”的视野里,但是提到他的名字和他曾经的作为,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以至于当他偶尔在媒体和公众中现身的时候,还是会引起一阵骚动。
这都是因为“主将”的缘故。
对于“主将”的角色,江嘉良有自己的理解,他说:
“国梁接手男队的时候问我,‘王励勤和马琳谁能当领军人物?’――他知道当时许指导选我的时候,就是把我当做领军人物的――两个人我就都分析给他听,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愿不愿意做这个老大’!当时我说我觉得王励勤的打法上要有一点更改,而且胆子要稍微大一点、要开阔一点,马琳打法很全面,但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愿望:去做领军人物。
一个队里面必须有个这样的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要能站出来、能够顶,顶得好坏是另外的事情。团体赛的第一场是很难打的,除了压力等等之外还有很多事儿,像抽签你不能离开、入场式你不能离开,等等,两个人一出场就好像打仗一样,就像两个将领骑着马举着大刀……”
有趣的是:江嘉良初出茅庐的时候是“打头炮”,他的最后一次比赛也是“打头炮”:1989年世锦赛,是中国男队最困难的时候,看着手里捉襟见肘的“几张牌”,许绍发去问江嘉良敢不敢第一个出场,江嘉良知道自己也很难打,但还是二话不说站到了先发位置。
作为一个在国际商业比赛中采用直拍横打技术的选手,惹得当时法国乒协很生气,说江嘉良骗钱来了。
打法
输得起脸得厚
就中国传统的直板正胶打法而言,江嘉良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这是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
江嘉良说:“陈龙灿和刘国梁都是直板正胶打法,我们几个各有特点,其中我是最正规的,陈龙灿来回球差一点,但是前三板好,国梁和他有点相似。改规则以后之所以没有这样的人才,不是说这种技术没有出路了,而是因为练正胶花的时间太长。
现在社会上都买不到很好的正胶球拍了,挺让人感慨,其实这种打法是很传统、很中国的,需要很全面的基本技术,胆识、斗志,等等。”
很久以前就听许指导说:江嘉良是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的运动员,所以我特意向他“求证”这件事,他说――
“1989年世锦赛后,有一个东欧的经纪人以我的名义组织商业比赛,那时候中国还比较穷,所以我们去了好几个运动员,都是花我的‘出场费’。那时候我的世界排名还是第一。
“那次我跟盖亭一共打了八局球,我全输了,因为我采用了直拍横打技术――我练这个技术只练了两个星期,还不太熟练――许指导在队里最初是让另外一个队员练这个技术,但是那个小家伙不成气候,没有打出来,我1989年输了球以后,也想把这个技术练出来。但是适应这个技术至少要一年时间,一年当中你要输得起球,脸皮要厚……
“当时法国乒协很生气,说江嘉良骗钱来了,现在看来,是不是很滑稽?”
想来有趣:刘国梁、马琳、王皓三位直拍名将赖以统治世界的“直拍横打”,最初却被认为是一种江湖骗术。
1987年逆转瓦尔德内尔夺冠后,江嘉良失声痛哭,然后又破涕为笑,向观众席上飞吻……
赛点
杀得狠拿得下
江嘉良最令人拍案叫绝的一场球,是1987年世锦赛的男单决赛:第四局,在16∶20落后的情况下,他逆转瓦尔德内尔。
江嘉良很坦诚地说:单打决赛之前,陈龙灿在半决赛时让给了他,这对他保留体力和老瓦决战非常有利――“那时候是21分、五局三胜,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全都要参赛,我从早上九点开始打,打到晚上十一点,有时间吃一块牛排,没时间就吃方便面牛肉干巧克力,所以,为了确保中国队拿男单金牌,队里就安排陈龙灿让了球,就像我混双让给焦志敏他们那样。”
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对于16∶20之后的一些细节,江嘉良记得非常清楚――
“好几个经典球,一个是他放高球我进攻,打了有十几个来回,还有一个就是19∶20的时候,他拉了一个球很接近,只要他提出来这个球了,我当时就认了、我就放弃了,准备打第五局了,当时他对这个球很犹豫……
“打到最后的时候,我和老瓦眼睛盯着眼睛,我盯着他的眼神恶狠狠地,意思是说‘你小子还是得输给我!我要把你拿下!你还不放弃?’――打到最后,就把人性那种东西都打出来了。
“追到20平的时候,我特意跑到瑞典队那边,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同时也在心理上暗示着我自己――我的气势不光是对老瓦,而是要把他全队的整个气势压制住――我握着拳头就在他们那边转了一圈,很有杀气的。”
很多人都记得赛后的情景:那场球结束后,江嘉良失声痛哭,然后又破涕为笑,向观众席上飞吻――
“赢了以后,就感觉有点艰苦,觉得每次在比赛中碰到委屈的事情、难的事情都让我来扛,一直都是这样,包括我还要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上台讲话、要唱歌什么的――那个时候乒乓球队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少,没有人去,到最后说江嘉良你去讲话吧,你不讲谁讲啊?这样的活动参加多了,倒是把跳舞、唱歌这些练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想到这些,想到又是把这种最难的机会给了我,我觉得有点委屈了,又委屈又喜悦,就在那儿哭……
“还有‘飞吻’也是这样,那时候中国运动员很少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大家看了觉得很新鲜。我太太那些演艺界的朋友就说:这个小伙子还可以嘛,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代表!”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你要听教练的,你不听教练的你就完蛋……
噩梦
想不通弄不懂
退役这些年来,江嘉良经常以电视台评论员的身份解说乒乓球比赛――
“雅典奥运会那回,解说完球以后我做了场恶梦!
“那一次,马琳输给了老瓦,老瓦赢球以后向国王招手,做指挥家那样的动作,他很享受,但我心里很难受――我不希望他赢!每次比赛解说的时候都让我预测,只要讲到欧洲的老队员,我就感到一种悲哀,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年轻、体力好,睡一晚上第二天朝气蓬勃,虎虎生威的走出来――老瓦比马琳大十几岁,马琳怎么会输给他呢?”
在江嘉良自己的乒乓生涯里,1989年世锦赛也就像一场噩梦――
“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是我跟阿佩伊伦打,阿佩以前跟我打真是没得打,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器材上首先就吃亏了――他比我年纪大两三岁,怎么会越打越快、越打越猛了呢?就是因为粘胶水,我们那时候自己内部不允许粘胶水。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你要听教练的,你不听教练的你就完蛋,运动员是没有创造能力的,99%的人都是听教练的,都是苦练、死练这种,包括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那时候也尝试过用胶水,五块钱一瓶,粘自行车轮胎的那种,粘完就挨教练骂,不允许!为什么我们越打越慢,他们越打越快?就是器材上的更改我们没有去跟进。
“技术上也有问题,没有去跟国际接轨,反手我们没有进攻能力,更不要谈直拍横打了。”
在那场决赛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江嘉良在比赛中一度“罢赛”,要求换裁判,对于江嘉良来说,这也算是一场噩梦――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外国的报纸、香港的报纸,都说我输球没风度――那个裁判是个邮电工人,很普通的裁判。换裁判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的愿望,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很无奈,因为我必须那样去做,打球又打成那样……我没法形容当时的那种心情。”
据我冷眼旁观,江嘉良对于这个“裁判风波”一直有些耿耿于怀,这应该也是退役后和乒乓球界的关系若即若离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第四十届世乒赛的噩梦之外,1988年奥运会也是江嘉良的一场噩梦――
“1988年是我的本命年,但是坦白讲,那个时候技术已经不够用了,还是老一套的打法。韩国我去了三次都没有取得好成绩:第一次是韩国公开赛,我打第二名;第二次是亚运会,我们团体4∶5输给韩国;第三次就是奥运会了。韩国不是我打球的地方!
“现在想想,我觉得在用人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当时我双打和许增才配对,他胆子还是太小,而且打法上也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滕毅……”
江嘉良乒坛生涯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是1989年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他让给了队友于沈潼……
很难设想如果我和李宁换一下位置会怎样,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情。
退役
闪的念流的泪
1989年,25岁的江嘉良退役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年龄退役,是一件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江嘉良披露了一些有趣的“历史掌故”――
“那时候广东经济发展很快,我们1983年一千五块钱人民币奖金,那个时候已经很高了,但是和社会上比较,还是觉得很失落。我还记得1982年出国,许指导给了我几个超市里面的塑料袋,那个时候已经很高兴了,好像得到什么宝贝似的。”
江嘉良其实有一个转型的良机:“当时,‘健力宝’要找代言人、做体育品牌,想在我和李宁之间选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你不做?’我说:不是我不做,而是许指导不让我想得太多。”
对于恩师,当时的江嘉良言听计从:“许指导的教法也很好,成就我现在这么一个个性,把南方人北方人的精华能够结合起来,南方人的细致和北方人的豪气,他为人真的很好,很善良,他教球这方面,包括他教人,我是很听他的,那时候有什么想法,我都跟他讲,他说你不要想得太多,一心一意打球……
“很难设想如果我和李宁换一下位置会怎样,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情。”
但师徒之间,在看法上,也并非完全一致。
“后期我跟许指导有一些分歧,都是很小的事情,从我自己检讨,也是一时冲动。现在没有去沟通,也没有去问。他是我的恩师是肯定的。
“到最后,我想去国外打球了――我当时已经退役,跟我太太1988年结婚了,我就问许指导我的后路该怎么走,他回答:‘你打球的时候没有去跟国外的人联系过?’一下子我真的懵了,当时就流眼泪了!”
江嘉良没有任何经验和准备,去面对新的生活。
“打球的时候,我就是一心一意打球,因为我做事情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乒乓球不允许有私心杂念,有的人领先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想法呢?在一闪念的时候会输球?――所以每次乒乓球回来总结经验,都要讲‘不要有私心杂念’。乒乓球打起来不好看的原因就是抠得太细了、抠得太紧了,不像网球、羽毛球有一个空间在里面,乒乓球是一点空间都没有。
“所以打球的时候,我真是一心一意地,什么也没有想。”
就这样,江嘉良没有成为李宁,他在退役以后走上了一条另外的生活道路。
我不知道现在的运动员是什么心态,未必是百分之百地快乐,我理解他们,站在那个位子上,有些顾忌很多。
生活
看得开放得下
江嘉良的妻子吴玉芳,曾经以《人生》中的表现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称号,他们的结合被认为“绝配”。
“谈恋爱的事情,我最感谢许指导同意我追求吴玉芳――我永远感谢他两件事:一个拿冠军,一个找一个好家庭――用现在的话讲他许指导是老板,我给他打工,他那时候要是说不行的话,我绝对停,不管我的女朋友有多好!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这一点。他还通过影协帮我去了解吴玉芳。”江嘉良回顾姻缘时,对教练十分感激:“那个时候在北京老有一些文体明星参加的活动,我们是一见钟情,所以许指导这点是非常开明的。”
结婚之后,江嘉良曾经到马来西亚发展――
“这种职业素质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我哪有什么私心杂念去打球,不打球去赚钱这在当时想都没想。那时候真的很茫然,非常非常地茫然,后来跑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钱根本长途电话费都不够我打,钱很少,没有办法,90年的时候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那里是羽毛球的天堂,不是乒乓球的天堂。”
江嘉良感慨地说:“人家从十四五岁开始摆地摊的时候,就去跟人家谈价钱,你江嘉良能拉得下脸来吗?你能有这个技巧吗?你有跟别人打交道这个能力吗?能那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吗?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不行,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当然同时也有我们的劣势。”
而江嘉良也不想再回到北京发展:“因为北京没有给我太多的快乐。其实北京是个好地方,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经常一谈起乒乓球会做恶梦、很痛苦……我不知道现在的运动员是什么心态,但是我想想,包括张怡宁、王皓也好,未必是百分之百地快乐,我理解他们,站在那个位子上,有些顾忌很多。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员有房子有汽车,最顶级的,但是没有去享受,你有好房子,但是你还得住队里,你有好车,但是可能保时捷的跑车已经快养出老鼠来了,因为没人去开……
“生活就是这样,只有享受到它才是真正拥有他,但如果你用不到、享受不到的话,其实是一种痛苦。”
过尽千帆,说这些话的时候,江嘉良有着一种对于人生的明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