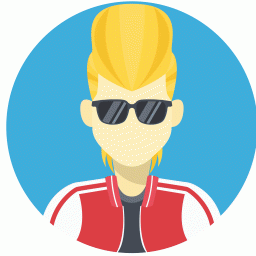从杜十娘看“三言”“二拍”中女性新的婚恋观及其成因
时间:2022-09-14 03:07:35
[摘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样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中还有很多。这些作品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并通过她们折射出明代女性新的婚恋观。这既和明代新的社会思潮有关,也和作者独特的情教观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杜十娘;三言二拍;女性形象;婚恋观;成因
一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订的“三言”中的婚恋名篇,它曾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潘虹饰演了杜十娘。她高贵忧郁的气质把杜十娘的美丽、善良和凄婉的悲剧命运演绎得如真似幻,赢得了观众和影人的好评。这样的婚恋名篇在“三言”和同为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的凌初编辑的“二拍”中还有很多。在目下翻拍重拍古典名著蔚然成风的氛围下,这些作品对启发编剧和导演运用电影这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去反映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地位和生存处境有一定意义,也可引发我们当代人的思考。
(一)尊重自我追求的女性及渐变型婚恋观
“三言”中有不少敢于冲破封建社会传统婚恋观的女性。这类女性在婚恋中,多积极主动大胆追求对自己心仪的男子,她们会主动赠予信物或送一个秋波,并不在乎他们的家世门第,也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顾虑。除了精神爱恋,她们还大胆、主动地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贞节观念的束缚。《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中的李氏、《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的陈玉兰、《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氏是这类女性的典型。她们或想方设法与情人幽会尽男女之欢、或与恋人私奔以期长相厮守、或以死抗争求得婚姻自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揭示明代女性婚恋观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故事框架建构在现代婚姻中常涉及的婚外恋上。女主角王三巧和丈夫蒋兴哥恩爱有加,从没想过要背叛丈夫。但丈夫去广东做生意几年不回,抛下年轻貌美的她独守空房,结果她没能抵挡住的诱惑,和陈商有了男女私情。在面对礼法的两难抉择时,她斗争过、挣扎过,试图用礼法压制,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并坦然承受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从王三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明代女性在选择配偶或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更多地尊从自我,少礼法拘束。不独只女性,男子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中国男人向来在女人的贞节上很难超凡脱俗,而蒋兴哥在面临自家夫妻感情危机时却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宽容态度。“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更多地是从自身找原因。再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王景隆、《单符郎全州佳偶》中的单符郎,在面对沦落到烟花柳巷但致死为他保全贞节的情人玉堂春和已经沦为娼妓的情人邢春娘时,他们始终钟情,锲而不舍地追求,不以良贱为念,不以贵贱易妻。“二拍”中对女性“失节”问题同样表现得很宽容。《酒下酒赵尼媪迷花》、《赵司户千里遗音》、《顾阿秀喜舍檀那物》、《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谅解、同情的笔触写了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越相敬重”。男女主人公以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性融化了理学桎梏,显示出新的人伦道德色彩和尊重妇女的人文主义精神,透发出对于健全人性人欲的充分理解与冷静欣赏,是对传统婚恋观的合理调整与热心疗救,显示出婚恋观的裂变。
(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和超前型婚恋观
“相悦成婚,礼从义起、以爱及爱”(乔太守语)应该是婚恋关系最为合理的存在状态,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缔结婚姻必须权衡门第高低、财产多寡,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卖油郎独占花魁》却为我们诠释了一种全新的婚恋观。莘瑶琴曾把从良的希望寄托在衣冠子弟身上,但衣冠子弟的打碎了她的梦。这时秦重出现了,他没有门第、财产、相貌、气质风度等优势,只是一个走街串巷老实厚道的小贩,但他身上却有至可宝贵的“闺阁良友”气质,他的“昵而敬之”感动了莘瑶琴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最终赢得了莘瑶琴的心。莘瑶琴从开始瞧不起、拒绝秦重,到后来不仅肯定了卖油郎的人品,还肯定了他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自食其力,布衣疏食,淡泊平生。这种选择可谓婚恋观念与人生价值的双重变革,也创造了一种不靠门第财产、不靠相貌功名、不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摆脱一切外在条件、以逐渐生成的至爱为唯一纽带的纯粹情爱。“男子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婚恋观无疑具有现代意味。
与莘瑶琴身世、经历颇为相似的杜十娘却没有如此幸运,她被富家子遗弃,最终选择了投江而死。有人说她本可以不死,李甲不就是贪图一千两银子吗?给他就是了,十娘拥有的何止千万。即便从良的美梦破灭,对李甲不再抱有幻想,她也可以一走了之,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她有百宝箱呀。如果真是这样,杜十娘就不成其为杜十娘了。因为她知道,爱情、婚姻、名分、尊严以及未来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不能凭借“身外之物”去换取,感情的媒介不是金钱,婚姻的纽带不是百宝箱,自尊自重的人无需借助身外之物来增重自己的分量,她要的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爱情。一个身陷青楼却不出卖灵魂的女人,一个懂得爱情与婚姻不同于做买卖的女人,一个渴望作良家妇女、过正常生活的女人,这样一点微不足道的梦想却在转瞬之间被负心郎及周遭诸多习惯势力打得粉碎。带着对孙富的仇恨,对李甲的蔑视,对生活的绝望,以及一种自尊自重自怜自怨的情绪,杜十娘沉江而死了,她死得气贯长虹,死得雍容尊贵。她的死是自身价值和人格力量最辉煌最璀璨的展现。她用自己的死昭示了只有人的自身价值才是婚姻的唯一纽带。这种婚恋观无疑具有超前性,就是在当今也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样“二拍”中《通闺闼坚心灯火》里的罗惜惜与张幼谦、《李将军错认舅》中的刘翠翠和金定,她们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冲动,表现出婚恋自主的精神,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
二
“三言”“二拍”中女性新的婚恋观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明代新的社会思潮
有明一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把理学家所强调的宇宙天理秩序作为封建伦理秩序的根据,把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来为封建政治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说明。为加强统治,明王朝曾组织人力修撰《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实行八股取士制度,考试时从《四书》、《五经》里命题,只允许考生根据朱熹的注解发挥,不允许异端思想的卷入,极大地限制了文人的思想自由。在文学上,统治者甚至以法律、诏令的形式,直接控制文艺创作的题材,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此限”(《大明律.搬做杂剧》)。在现实生活中,贵族显宦可以不必隐蔽他们的生活,却刊刻《闺阁四书集注》和《女儿经》,极力向广大妇女灌输纲常名教,“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这些灭绝人性的理学教条更给明代妇女带来了极大的人格与精神上的束缚。
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以产生关系的萌芽,市民意识的觉醒,思想文化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这其中有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束缚人性,以王艮、颜山农、罗汝芳等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倡导“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对传统道学表示轻蔑。特别是李贽,在继承和发展泰州学派进步思想的基础上,公开以“异端”自居。他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的权利,大胆地把“圣人”与“众人”等同起来,以此来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直接对抗。他尊重人的自然情性,对人欲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好货好色”是人生的最基本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的说教。对妇女,他也持较平等的态度,如他提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限制的结果。在文学上,他倡导“童心说”,强调绝假纯真,抒写真情实感。
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李贽影响,对李贽推崇备至。文艺方面,他也接受了李贽的观点,非常重视通俗文学的作用,他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古今小说序》)把通俗小说的教育作用看得超过儒家经典,这本身就是一种离经叛道。他还指出,“浊乱之世,谓之天醉”,而“天醉”的黑暗局面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天不自醉人醉之”,所以要“天不自醒人醒之”。人要醒天,就必须通过言论作品“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醒世恒言序》)他编订“三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他通过小说揭露社会弊病、批判黑暗现实,特别重视描写“男女之情”,强调情真。这就决定了在一些以妇女、婚姻为题材的的作品中,他能够突破理学桎梏,表现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赞美她们真挚的爱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杰作无疑是他这种思想的反映。
(二)作者冯梦龙独特的情教观
除了文学观念上的离经叛道,冯梦龙还特别重视在小说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发挥“情教”的作用。他编辑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情史》就集中反映了他的情教观。在《情史序》中他说“情始于男女”,“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可使它“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以达到“情教”的目的,产生像《六经》一样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人有“七情”,即《礼记》云:“所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冯梦龙《情史》中所讲的“情”主要指“爱”――人的同情心,休戚与共的关系和“欲”――人对饮食男女的追求及男女之间的爱情。基于此,在人情、爱情、婚姻等方面他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闪烁着反封建礼教反程朱理学的民主思想光辉。
在人情方面,道学家把人的一切看做罪恶的渊薮,“天理”(更见制度与名教)的大敌。程颐说:“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二程粹言》卷二)朱熹说:“若便说做人欲,便属恶了。”(《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教训人们对人欲要“克”,要“扼”,要“灭”,要“窒”。而冯梦龙却和李贽一样竭力论证人欲的合理性。他大胆宣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情外》)人们对各种的追求,完全符合人的天性,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如同草木要发芽,“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情芽》)人有是生机勃勃的表现,窒息人的,就像抑制草木发芽,做人还有什么情趣?在《情芽》卷中,他还列举了大量材料来证明圣贤同凡夫俗子一样有情有欲,那么普通百姓追求饮食男女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需求。
在人的各种情感与欲望中,男女之情、两性之爱是最基本,也是封建礼教防范最严密,致使无数青年男女惨遭迫害,恋爱、婚姻、家庭悲剧层出不穷的,对此冯梦龙也有深刻认识。他对妙龄寡居的卓文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不顾父亲的威胁逼迫,毅然夜奔司马相如并结为夫妇的侠骨柔情和义勇行为予以热烈赞颂:“是妇是夫,千秋为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情侠》)《情史》中还记载了许多聪明机智、有胆有识、忠于爱情、始终不渝的女子。这就不难理解在“三言”中,他为什么会编选为数众多的爱情婚姻故事,并写下一些赞美真挚爱情、反对虚伪礼教的批语。这正像他在《挂枝儿》、《山歌》中收集大量的情歌一样,无疑具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山歌序》)的反封建意义。
冯梦龙对婚姻的看法也包含不少卓识,有别于陈腐的传统观念。他给婚姻下了一个崭新的定义:“男女相悦为婚。”(《情迹》)不讲门第财产,不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仅仅突出“相悦”。他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婚姻制度的弊端,礼教可怕,人言可畏,青年男女只好强食婚姻苦果,而妇女的牺牲往往更加惨重。所以他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给青年男女择配的自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便借乔太守之口表达了这种观点。《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玉堂春落难逢夫》、《单符郎全州佳偶》、《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也都表现了不计财产、不较门第,而以真情相爱、以真心相许的婚恋观。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三言”“二拍”婚恋名篇中的女性能够超越时代表现出新的婚恋观,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冯梦龙编,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上)(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作者简介]程战芝(1968― ),女,河南孟津人,民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