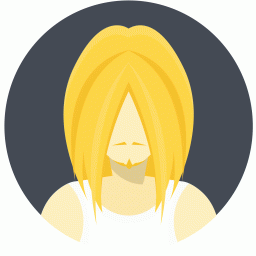今天我们如何回到亚洲?
时间:2022-08-26 12:03:33
既是学术,谈的,恐怕都不是大众意义上的常识,于常识问题,往往要大胆发出新意,提出质疑,然后小心求证,方为学术。
所以,在张承志的学术散文集《常识的求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中,常识,只是个幌子,虚晃一枪的背后,是他想要谈的问题。
作为标题的这篇文章《常识的求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一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从“五四”谈起,话题马上就转入了张承志熟悉而中国普通人比较陌生的领域——阿拉伯伊斯兰的世界。
在情感上,我对张承志热烈拥护的哲合忍耶、革命、赤军、阿拉伯有一种滋味复杂的亲近感,就像在近代历史上,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民一样,他的书、他的煽情的文字总是让青春期时的我激动莫名,而古波斯、阿拉伯的典籍所带来的西域神秘世界,又在勾引着我对异域风情世界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张承志为《热什哈尔》的翻译出版工作所作的努力,我们可能对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波斯带来的礼物,在穆斯林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叙事——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在蒙古史上,我们读到了《元朝秘史》……这些或被忽略或尘封的书籍,诉说着和西方史观不太相同的故事。
张承志提出了新的视角,在西方历史观的背后,存在着东方的历史观、阿拉伯的历史观,从前完全被遮蔽和忽略,这显然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关心“第三世界”的“小三”文化,它们,当然也需要扶正。但是问题在于,张承志得出的结论“沿着地中海的那条陌生防线,乃是中华民族的的万里长城”,是值得讨论的。
只是地理意义上成为远东与西方之间缓冲地带的奥斯曼帝国是否有兴趣为遥远的充当炮灰?张文《地中海边界》持此论。但一八四年,当船坚炮利的英国人敲开大门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仍旧是亚欧大陆之间的巨无霸,尽管已垂垂老矣,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惊闻天朝噩耗,缘何不兴起义师围魏救赵?反而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而且,基尔帕特里克在《异域盛放——倾靡欧洲的中国植物》一书中认为,恰恰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打断了丝绸之路的陆路交易路线。
熟读世界史的读者都知道,奥斯曼帝国版图最辽阔的时候,也没有打过黑海占领俄罗斯和波斯。即使没有奥斯曼帝国,欧洲殖民者要想象蒙古骑兵那样横扫千里,在陆路连续征服击败阿拉伯、俄罗斯、波斯、蒙古和中亚剽悍的游牧民族以及西伯利亚的恶劣天气,最后和刚刚建国的清朝八旗子弟碰上并且让他们俯首称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德国的机械化闪电师当时所向披靡,在莫斯科的满天风雪中也只好缴械投降。不管苏俄算不算亚洲国家,从极地呼啸而来的冷空气始终是横亘在欧洲与远东之间的最大障碍。倘若把俄罗斯算作欧洲列强之一,在清朝末年帝国大厦将倾之时 “同志加兄弟”的奥斯曼帝国又在什么时候对抗过俄罗斯以解慈禧老佛爷和中堂大人李鸿章的燃眉之急?所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或阿拉伯防线保护了东方不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这样的结论,也许只是张承志先生的常识吧。
在北大的演讲中,张承志认为,巴黎和会“首先是西方阵营庆祝对奥斯曼帝国五百年征战攻防的胜利的庆功会”。奥斯曼帝国作为德、意、保加利亚、奥匈帝国协约国一方的战败国,接受战胜国协约国的协商解决或者说瓜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难说不妥。奥斯曼帝国有点像盛极而衰的蒙古帝国,它的领土靠马背上民族的战功获得,多少攻杀战取的背后,是平民的死亡和城市的屠戮。一六九至一六九一年,奥地利帝国军队撤出科索沃后,奥斯曼帝国军队对当地居民采取残暴的报复措施,迫使三四万户斯拉夫人在佩奇大主教阿尔塞尼耶三世的率领下离开科索沃和马其顿北部,逃亡到匈牙利南部、今日的伏伊伏丁那和克罗地亚境内,才形成塞尔维亚人聚居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塞尔维亚人大迁移”。如果奥斯曼军队爱民如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塞尔维亚人何必舍近求远?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国民,当然有过四海清平的全盛时期。但是苏丹哈里发制度和清朝的皇帝等级制度有一个共同点: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制度下,有何民主可言?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恐怕更严苛。甚至,至一九八年,奥斯曼帝国仍有奴隶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失利和巴黎和谈诸强欺弱的结果,也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国民运动最后一世苏丹六世的结果。自此之后,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像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从今天来看,那段往事当然有其残酷和荒谬的一面,但是至少,它在形式上了帝制,使共和思想如星星之火播散于民间,尽管帝国的阴影仍如影随形。
殖民主义是西方历史上永远的耻辱标记,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不以意识形态的眼光说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换汤不换药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中国循环历史中,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力量的进入,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真不知道何时有人民当家做主的一天。而澳门的存在,表明这种形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虽然以殖民为始,却未必以殖民为终。澳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唯一没有为战火波及的城市,诚如基尔帕特里克所指出的,澳门,根本不是葡萄牙殖民者武力强占的结果,而是当时的明朝政府划给葡萄牙商人的暂时驻足地。鸦片战争之前,在贸易季节之外,西方商人必须离开广州,到澳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暂住。而且根据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葡人为了维持居留澳门的权利,必须向中国皇帝交纳地租和赋税,必须像朝鲜、越南、暹罗等亚洲藩属国一样向中国皇帝呈献贡品,从里斯本或果阿派往北京宫廷的使节,也被看作维持朝贡关系的贡使。此外,葡人还必须不断向管辖澳门的各级地方官吏送礼行贿。”直到一八四九年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才停止向中国交纳澳门地租及占领关闸,但也从未奴役乡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相反令其在二战中成为一个平静的避难所。
对此,我的看法是,在不忘历史、清算西方殖民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苦难的同时,要认真看待西方民主的传统,并虚心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张承志先生对西方中心论的反驳,在我,总有一种阿拉伯中心论的感觉。
在批评苏珊·桑塔格的《他者的尊严》一文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在我们看来,在阿布格莱布的小小揭露提醒人们留意的,冰山潜在水下的部分,是更大也更卑鄙的十字军原教旨主义阴谋。”“使他们撕开了一切面具酷刑拷打,使他们气急败坏地急于摧毁的——是使他们在心理上深感自卑的穆斯林尊严。”
用“十字军原教旨主义”和“深感自卑”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对方,和张承志不能接受的苏珊·桑塔格所使用的“恶魔独裁者”(指萨达姆)和“合理性”(指美军入侵伊拉克)在逻辑上我不认为有太大的区别。
张承志没有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虐囚照片公开的背后是极权世界被压制的黑暗,我们没有看到萨达姆虐囚,不等于萨达姆没有迫害政治犯,也许,受刑者连被拍照的权利都没有,正如我们在许多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另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问题和独裁者极权统治的非法性,需要同样的批判力度。为侵略者唱赞歌当然不对,但如果像张承志先生那样,择其一点,大加抨击,是否矫枉过正?这是需要警惕的。
在这本书中,他一再表露出他的核心立场——归亚的方向。亚洲,本是一个地理术语,当张承志将其身份认同化,将西方和亚洲树立为对立的概念时,我们就必须面临一种抉择:是回到亚洲,还是越来越西化?
正如格非有一次所说的:“我也是人民的一份子!”亚洲,在亚洲,从来没有在地理上搬到欧美去。但是张承志们的焦虑我们当然能够理解,那种西方制度、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亚洲传统的冲击,在最近百年里,实在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以出国为荣,以好莱坞大片、薯片和可口可乐打发时光,儒家的坚持、士的精神,似已被消磨殆尽。这是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想要在身份认同中获得心理慰藉,又希望能尽快融入到世界大洪流中淹没自己。张承志所持的回归立场也许只是一种乌托邦。但是正是他的存在,提醒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差异性,要消弭这种差异性,使得我们的制度、文化中阴暗的一面能够逐渐走向光明,而璀璨的一面又能得到保持得以薪火相传,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摸索。
西方中心论在今天,是左右两派争论的焦点,对待西方的态度,似乎总是划分两个阵营的唯一标尺。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西方,应该怎么看待传统,如何回到亚洲?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墨索里尼想要恢复古罗马的荣光,却走向扩张和独裁,最终,古罗马的梦幻终于在帝国的崩溃中轰然倒塌。日本,曾经犯下法西斯罪行的日本,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堪称中国的老师,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日本,只是保留了一些文化标志,在民主形式上、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都已走向西化。
在《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中,张承志对赤军的辩护让人震惊,在本书《“归亚”的方向》一文中,赤军更成为归亚方向的实践者。日本导演若松孝二和赤军领导人之一足立正生是好朋友,还曾跟随足立以及赤军女首领重信房子去了中东拍摄纪录片《日本赤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世界战争宣言》,可谓革命意气风发,但是时过境迁之后,二八年,他拍摄的《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更多的却是反思与悲鸣。浅间山庄事件,被认为是日本赤军运动转向消亡的标志性事件,在山林的秘密集结地中,赤军内部“狠斗私字一闪念”,在“进步”和“改造”的口号下,一个个同志被活活折磨至死,其残酷性较之中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张承志在《敬重与惜别》中,对这段往事却只字不提。张承志只以“当日本国内发生了残杀战友事件”简笔略过,他有没有因为要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而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
重信房子、冈本公三等阿拉伯赤军,不顾个人安危,放弃安逸的生活,为素不相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解放战争所作出的努力,其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确实一度让我非常感动。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和英国、阿根廷的马岛之争,同为领土问题引发的宿仇。即使还有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即使巴勒斯坦还有立国的问题,这种仇恨,在二十一世纪,也更需要和平外交手段的努力,以暴制暴(特别是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从来不是当下解决的好方法。而且阿拉伯赤军在巴勒斯坦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还是热衷暴力本身,本身就非常可疑。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阿拉伯赤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本·古里安空港)向旅客发动突然攻击,造成约九十八人死伤,其中二十六人死亡。在《敬重与惜别》中,关于此事张承志有专文辩护,用冈本公三的证词、桧森孝雄的回忆录和重信房子女儿所著的《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为证据,证明三名阿拉伯赤军当时不是对乘客乱射一气,而是想“袭击机场的管制塔”,而且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卷入,赤军成员安田安之扑在手榴弹上,被炸身亡。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丸冈修等人劫持从巴黎经阿姆斯特丹往羽田空港的日本航空的波音七四七飞机,后经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利比亚。在释放乘务人员和乘客以后,炸毁了飞机。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及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一九八六年六七月间,“赤军”暗杀小组企图暗杀日本天皇。……如果这一切都那么正义,为什么重信房子二一年在狱中要宣布解散赤军,并向所有受过赤军伤害的人谢罪?她说:“谢罪并不是后悔,而是期待在要求一个更好的日本的时候能够吸收这些教训。”
回不回到亚洲,是否以西方为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帝国的武功霸业、文明的辉煌和人权的独立尊严之间,哪一个更重要?这是需要张承志先生思考的一个问题。追溯这段历史,我想说的是,帝国的胜利和国民的安居乐业是两码事。在现代意义上,对公民个体的尊重,国家和政府真正意义上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才是重中之重。
历史:思辨与实践——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差别
姜佑福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本书致力于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观念”上的基本差别,但首先强调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和理解黑格尔哲学,才可能透过二者在方法与主题上的相似之处,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社会本身的批判;“历史观念”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对同一个事实的不同解释,毋宁说恰恰是“事情本身”的差别,是人类生存原则的历史性差别;这种生存原则之差别的现实过渡,或者说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克服,须得依靠从“世界历史”去向“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