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平血案看转型期“社会焦虑”
时间:2022-08-16 11:2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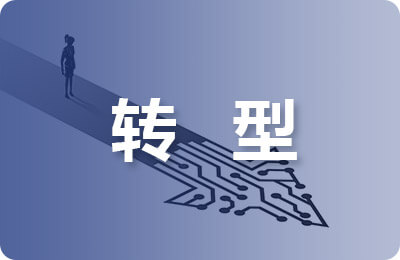
“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
极端事件折射社会焦虑
2010年3月23日早上8点,福建小山城南平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案件:一位辞职的社区医生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手持利刃55秒内刺向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小学生死亡,5名重伤。
人们在愤怒、惊诧之余不由地想到:郑民生是个精神病患者吗?答案很快得到了否定,在面对审讯时,郑民生明确交代作案动机是针对两个人:一个是他认为排挤他、给他设置升职障碍、想逼走他的单位老领导;一个是最终抛弃他的第二任女友。
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固然难逃法律的严惩,但是其从一个平凡的人,一个还算称职的医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演变成一个残忍的、的杀人狂的人生轨迹,或许更需要人们警醒。
可以说,“失败”是郑民生的人生标签:蜗居、恋爱受挫、人际关系紧张、工作失落……当然,大多数人遭遇这类事情也不会犯罪,是郑民生在压力和窘迫之下自己出了问题,他将个人生活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在满怀对社会怨恨情绪的驱动下,最终完全变态。
透过郑民生案,笔者想到了现在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社会焦虑。
社会非理性冲动潜伏危机
当前,为数不少的城市市民似乎或多或少地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社会焦虑”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困扰着人们,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烦躁、压抑、紧张、非理性冲动等气氛。
一些中低收入者在为眼前的生计、为以后的出路焦虑:较高的生活费用如何解决?就业或再就业问题何时解决?家庭成员的医疗费问题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就是一些算不上是弱势群体的城市市民也往往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足,而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利处境心怀忧虑。
社会焦虑出现的背后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冲突。在城市中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在较短的时间内会出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社会焦虑潜伏着社会危机。现在常见的现象是在同一城市、同一社区,彼此缺乏信任,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更谈不上合作和关爱;城市市民普遍缺乏一种应对社会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人们会轻视一个社会所应当具有的规则意识和规则体系,进而在行为取向方面更容易选择成本小、见效快的短期行为;处在焦虑中的人,当焦虑增强到一定程度时,一旦遇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容易把不满堆积,放大困难和挫折感,并迁怒于身边的事物。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社会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
换句话说,城市社会市民群体性焦虑到了一个临界点,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转型阵痛下社会矛盾的纠结心理
市民群体焦虑心态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阵痛,也是社会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期,社会矛盾多发的高风险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意味着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速地变动。在这个变动时期,城市必定会出现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同与适应需要经过一个时期。
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城市市民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或认可、认同的复杂心理状态。不少人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不会有十分的把握,也就难免出现一种比较焦虑的心理状态。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既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而且相对于过去而言,集体意志削弱,个人意识膨胀,人们变得越来越独立和自我,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和自私。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现在也并不成熟,很多必要的规范制度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网尚未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从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的发展和信仰的缺失也造成了城市市民群体生存焦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状况是乌托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崛起;知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化,这就造成了信仰缺失,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尤其到了今天,社会资源的格局开始处于定型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基本分化完成,大型资本的社会控制基本趋于固定。
于是,在现代的中国城市出现了畸形的一幕:一方面,城市市民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空壳化,人们失去了有着强大意志力的社会信念基础;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的不公所造成的国强民弱的状况,又使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成为被剥夺的一“族”,有着强烈的失落感。该有的信念没有了,该得到权利的没有得到,未来的前景也不太清楚,群体性的焦虑也就不可避免了。城市市民的焦虑,深深来源于社会转型后的中国社会整个矛盾和纠结的心理。
政府构筑消除隐患安全机制
在个体充满焦虑和人生缺乏热情的状态之下,政府不能成为旁观者,而应主动消解公众的社会焦虑。
事实上,社会问题的发生并不是由个人或少数人引起的,也不是由少数人负责的,它造成的后果是社会性的,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对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力量的交汇合作才能改善和解决,因此,政府必须主动解决这种社会焦虑,而不能被动地防御。
政府要做的就是构筑消除社会焦虑的安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障机制,扩大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上下沟通机制,建立群众利益表达、意见反映的正常渠道;第三方调停机制,实现政企分开,减少政府成为冲突对象的可能性;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预防、化解矛盾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平安建设。
无论是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制不健全的焦虑,还是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快速变迁的焦虑,这些焦虑都有明确的指向,也都具备一定的普遍性。社会焦虑作为市民内心的不安全感,虽然未付诸行动,可是,普遍的、长期的社会焦虑如同大量微不足道的小白蚁,会渐渐破坏社会和民族的凝聚力,损害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甚至吞噬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