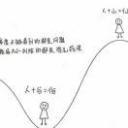疯癫的诗意
时间:2022-08-14 08:20:55
当白兰芝在一翻挣扎后收起行李,恢复优雅的姿态,走向她的归属地——精神病院后,她终于被“规训”并永远地“流放”了,随之,舞台上的最后一束追光照在史黛拉身上,在她的一句“我们到底对她作了什么?”后,全剧嘎然而止……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了,此次台北李清照私人剧团的新作《白兰芝》在上海话剧中心的D6空间上演。音乐剧《白兰芝》改编自《欲望号街车》,并以女主角白兰芝为名。
以白兰芝为名,在舞台上只启用扮演姐姐白兰芝和妹妹史黛拉的两位女演员,将原剧中的男性角色全部去除,不在性、暴力、权力上逗留,只留下姐妹之间细微的情感变化和彼此追求幸福途中的无奈和残忍。这样的改编,削弱了两性之间的冲突,放大了姐妹俩精神世界的异化,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去展现现代文明下人类的“疯癫”。
疯癫,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疯癫,是人类的弱点、错觉和幻想的表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不同定义、不同体验及处理方法的变化。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态度还很暧昧,只是把其当作嘲讽和揶揄的对象,并且出现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到了古典主义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态度开始鲜明,疯癫被理性对立,受道德谴责,在禁闭中沉寂;从18世纪末起,随着医学的发展,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病,它被理性彻底抛弃,甚至不能与其构成一种关系,精神病患者的语言则成了疯癫的独白。
白兰芝疯癫的独白,从最初的欲望便已经开始,经过死亡,至最终的精神崩溃。正如她刚到新奥尔良,询问街车时对自己命运的隐喻——他们叫我搭乘“欲望号”街车,再换乘“公墓号”,经过六个街口,在“乐土街”下车。
白兰芝的欲望既是与生俱来,也是命运造就。她痴迷声色、贪恋虚荣,为了获得心灵的慰籍,在执教的学校勾引十七岁的男学生,在下榻的旅店与陌生人频繁交往,在妹夫史坦利面前不忘展现女性魅力,在带给她最后希望的米奇面前粉饰操守,即使在希望破灭之后,她也竟不死心地去引诱送报纸的男孩儿。导演为白兰芝在“教导”史黛拉时设计的一句台词——“幸福仰赖引诱”,是对其欲望一针见血的诠释与总结。
白兰芝的死亡早已谱写在生命的序曲中。从她的祖先放望、肆意挥霍、变卖家产并相继离世起,死亡的阴影就一直伴随着她。她年轻的同性恋丈夫因为遭到她的羞辱而自杀,更是成为了她一生的负罪。而当她向周围的人一点一点地“坦白过去”后,死亡也就渐渐向她逼近,卖花老太太的出现象征着她灵魂的死亡。白兰芝说,死亡的反面是欲望,她正是用欲望避免自己接近死亡,然而事与愿违,亦如导演为她谱写的歌词——一出悲剧仅仅这样,没有风波没有挣扎,老妇没有希望。
终于,疯癫的独白化成了白兰芝对自己吟唱的挽歌。妹妹史黛拉呢?如果,疯癫对姐姐而言是一种诱惑,那么,对妹妹而言就是一种堕落。史黛拉的疯癫,来自对丈夫史坦利盲目的爱,也来自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史黛拉羞涩地告诉姐姐——他离开一个晚上我几乎就受不了,要是他离开一个星期,我几乎就要发疯。在姐妹俩对唱的《愁云花蜜不离不弃》中,姐姐用相同的一句话反复质问妹妹是否究竟幸福,而妹妹的回答总是这么铿锵有力。即使她遭到丈夫粗暴的对待,即使姐姐被丈夫无情的蹂躏,她依旧相信,如果把姐姐送走,她就会回到往日的幸福甜蜜。姐姐的幸福仰赖引诱,妹妹的幸福仰赖牺牲自我,何等的殊途同归。姐妹俩就这样沉醉在爱的迷乱中,竞争男人,攀比幸福,互相祝福。
疯癫的诗意,始于剧作的内涵,终于舞台的呈现。导演认为,爱的迷乱是现实主义难以舒展的花瓣,却可能成为展开诗歌的前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爵士乐和传统戏曲的结合成为了《白兰芝》的载体,塑料和金属构成了舞台的质感,舞蹈肢体和戏曲身段组成了演员的形体,奇装异服和浓妆艳抹塑造出角色的形象。如此,音乐剧《白兰芝》带着调侃的语调,以“折磨人”的姿态出现在充满着理性和秩序的今天,做着不自然的疯癫的表达。
白兰芝的亮相令人“无法忍受”,她从观众席中走来,路过之处留下行李,等走到舞台,再矫揉造作地烦请观众一件一件把行李送上舞台去。白兰芝的“坦白”令她无处遁逃,每次都会遭到“天降白粉”的难堪,好似猛然掉落了妆容,又不得不在惊慌中胡乱擦抹。白兰芝的蜕变让她深入绝境,从白色的塑料纸大衣到鲜红的日本和服再到白色的内衣,好似刚到新奥尔良时无法卸下的伪装、回忆贝尔立夫时无法回避的坦白、最后希望破灭时无法遮掩的,所有的形象都印证了整剧为她谱写第一支乐曲——我是白色我是飞蛾我是粉。
与白兰芝的鲜艳相比,史黛拉的色调素淡,尤其是少了浓妆艳抹。厚厚的塑料气泡纸让她怀孕的身材更显臃肿,透明的薄膜纸让她露出主妇本色,俏皮的黄色连衣裙传达出她自欺欺人的快乐,如她向姐姐形容自己的幸福——她和史坦利只是草芥夫妻。然而,正是这样的幸福让妹妹无奈地照看姐姐,让妹妹急切地把姐姐推向另一个男人,又让妹妹在万般无奈下把姐姐送向不归之路。名正言顺的残忍,这又是何样的一种疯癫?
巨大的反光金属片作为舞台的地面,塑料保险膜包裹了舞台的后幕和两侧,舞台的一边堆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另一边架着衣架、置着沙发、放着白兰芝的行李,舞台的正空悬着两副中国传统水墨画,正中摆着大红色的一桌一椅——疯癫的诗意就被这样从人物的内心投射到整个剧场空间,又在人物的角色转换中迸发出更多,白兰芝时而是史坦利,史坦利时而是史黛拉,史黛拉又时而是米奇,两人分饰四角,迅速得顾不得给观众留出时间,然而,当男人缺席,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模仿只会不经意间成为一面镜子,让另一个女人审视自己。两个女人就这样迈着舞步,做着造型,在语言之外交换着真实的内心。
音乐剧《白兰芝》,是一场姐妹俩关于疯癫的游戏,是创作者对于疯癫的诗意表达,是观众对于疯癫的体验与欣赏,更是一次直面内心的拷问——作为一种被边缘化的非理性的存在,在看似冷静而忙碌的现代生活中,疯癫究竟距离我们有多远,却又有多近?亦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认为,人类必然会疯癫到一种程度,即使不疯癫,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所以,我们不禁可以这样理解,导演最终以妹妹史黛拉的台词“我们到底对她作了什么?”作为剧终,是疯癫过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