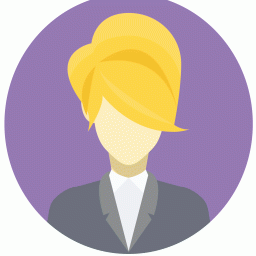伽达默尔解释学视域下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解释的尝试
时间:2022-08-08 11:52:48
摘 要:在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揭示了经典文本和解读者两者之间存在的阐释空间和张力,并提供了一种文本和解读者两者关系的独特视角,本文正是基于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以《论语·雍也》中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为例,试图验证该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阐释的可能性。
关键词:解释学 上知 下愚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5-0122-02
一、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文本与解读者两者之间的张力)
1.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
伽达默尔对“前见”的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第一步采用了胡塞尔的洞见,即我们对任何对象的理解,都包含一种意义的筹划,而这种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背景、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例如,胡塞尔较为常用的苹果树的例子,我们观看一棵苹果树,从来不可能全面地(包括前面、后面、下面和里面那样)和整体性地、直观性地被给予,它总是只给出一个侧面,即观察者总是只能从一个侧面去观察,然而,观察者所意向和经验的是整个显现的对象,而不是那个通过直观给予的某个侧面。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我不是首先具有经验或感觉印象,然后以某种方式理解它,而是恰恰相反,在知觉某对象时,已经存在在前的心理预期或意义规定的结构。心灵在知觉行为中,并非白板一块,而是一个主动意义的规定者。那么,在对文本进行阐释时,在先已经存在着意义的筹划或解释,是存在着“前见的”;而第二步,伽达默尔采用了海德格尔对理解前结构的揭示所表达的要点,即:即使在我开始自觉地解释文本或把握对象的意义之前,就已经把它放入某种脉络中,从某种视角去观看,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设想它。故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立”的优越观点可以用来探讨文本的真实意义,在解释文本和把握对象意义时,我们总是讲它与我们自身的实践结构相关联,任何对象的意义是由我们自身的情况或者生命关系和在先的预期所一起规定的。例如,海德格尔在《早期弗莱堡文选》中采用的一个例子,当我们(现代城市居住者)走进一间教室,可以明白那些讲台、课桌椅等意味着什么,而当一个居住在非洲层林里的土著(从未见过教室的人)进入一间现代意义上的教室时,他会以自己的前结构对教室进行理解。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被抛”状态。
伽达默尔这两个为“前见”恢复名誉的步骤难以避免主观主义的指责,如果我们总是以某种有前见的方式去理解文本,那么这种理解与纯粹主观的解释将很难讲存在任何差别。进而可以推断:每个处于其特殊生存的处境的个体在其独一无二的处境中形成了自己的偏见,这种偏见(或者说前结构)是此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和理解一样,是此在的基本生存结构(所以才将其成为本体论解释学),而不是后天形成的某种认识意义上的方法论。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地,世上也没有两个完全处境的个人。面对同一个文本,任何两个阅读者之间、每个阅读者和原作者之间,甚至是原作者和已经写就的文本之间,都不存在绝对正确理解的可能性。故产生所有理解都是正当的、没有一种理解是优越的这种主观主义倾向的理解,为了避免这种主观任意性的指责,伽达默尔引入了两个措施对任意解读的可能性进行限制。即:
2.传统和完全性预期观念的制约作用
伽达默尔除了跟随海德格尔将理解固定在实践关联中,还进一步地将这种实践关联置于历史中,即,我们对文本对象所具有的问题或者理解并不是任意产生和随意进行的,而是根源于历史的和解释的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例如在对某个文学作品的理解中,首先我们会用我们先驱曾经理解过的方式去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抛境遇本身不是一个无条件或者任意的境遇,在理解某作品或解释某对象意义之前,我们自身所特定的文化传统已经赋予我们某些特定的假定。这种假定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得以理解的基础。这里引入伽达默尔的另一个概念,即“效果历史”:意指传统对那些属于它的东西的作用力量,以至即使拒绝或反抗传统,它们也仍被传统所制约。如抽象画给予观看者所产生的效果,就在于这种对心理预期的阻碍作用。那么,理解行为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主观任意的行为,通过效果历史的作用,限制了我们理解的可能任意性。
此外,伽达默尔又引入了“完全性预期”或完美性观念来限制主观任意的解释。所谓的完全性预期概念,意指为了避免文本的任意的或个别的解释问题,必须假定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解释学循环,部分的意义要依赖整体来解释),它有某些真理要告诉我们并且在相关主题上它比我们更是权威。相对于某个文本,其读者被要求对所阅读文本的真理进行开放,我们要承认该文本具有某种权威规范性,这样,读者才有可能检验自身对文本所体现的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因此可见,伽达默尔为了避免主观主义,最终采取的策略是以经典的文本作为某种意义上判定的标准。换句话说,在这里,伽达默尔似乎以对过去的依附,取代了批评者归之于他的对于前见的依附。但这种策略又被批评为保守主义的。
3.总结
从上面可以看出,任何一种解读行为都必然包含两方面的因素:文本和解读者。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理论建立在这两者所构成的张力之间:一方面,经典文本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中真理的源泉,本身具有规范权威性,强调这一维度可以避免可能的任意性解释(相对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不同解读者对同一经典文本的具体解读,又必然和该解读者自身的具体实践关联相联系,受前见制约,强调这一点又可以避免其中的保守主义。
既然任何解读行为都包含这样的两方面的因素,那么,从理论上看,伽达默尔对这两方面因素之间关系的揭示,同样可以应用在中国儒家注释活动中。
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阐释学梳理
由于中国传统儒学的要求是“尊经服古”,如何正确地理解经典中蕴含的真意,成了后学者终其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紧紧围绕着经典文本,形成的一系列注疏性的文本,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主要特点(有的学者干脆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注疏”两字)。因此,经典著作(如儒家的四书五经)对后来学者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规范意义。不难推断,中国传统学术中较少涉及解释者在前见的作用下、对经典的创造性阐发,而更多的是,强调对经典的依附和遵循,尽可能地在经典文本内部寻求最贴合文本原意的解释。因此,不大恰当地说,如果要给中国儒学传统简单地定性的话,它是保守主义的。下面以《论语?阳货》中的“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为例,来看经典文本对解释者的限制,以及这种保守主义的具体体现。
早期对于这类话的解释以王充为代表:
“夫中人之性,在所习染。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一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习。故孔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可推移者,谓中人也。” 东汉王充(《论衡·本性篇》)
之后,董仲舒提出所谓“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性三品说。唐韩愈也有说法不同但意思相近的“上品之性”、“中品之性”和“下品之性”的性三品说。又有北宋的经学家邢昺曰:“唯上知圣人不可移之使为恶,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强贤。此则非如中人性习相近远也。”以上诸儒者都是站在“性三品说”的立场上来解读“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句话的。这在《论语?雍也》篇中可以找到佐证:“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论语·雍也》),人类按其天赋的本性是有差等的,上知与下愚是与中人不同的两类人,他们的本性不能够改变,只有中人是可以改变的。
在此,可以看出“完全性预期”的作用,解释者自觉地将《论语》看做一个意义完整的整体,并是其必须从中学习的真理承载者,故在对其解释的过程中依照上下文,使其贯通一致,不至于产生矛盾。但这种解释存在着理论上的缺憾,如果某些人(下愚)天生的无法成善,那么,其行为的不道德性就不应该由自身负责,道德礼义对其也无强制性的作用,人之能否成善全然是上天所赋予的禀赋决定的,这易于陷入“宿命论”,而忽视了自身的道德自觉性,随着理论的发展,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对这句话的解释有了新的不同:
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程子说“人性本善,有不可以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与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朱熹《四书集注》)
这里从程子的观点可以看出,其对人本然之善性和气质之性进行了区分,人之天性都是善的,故无论上智、中人、下愚都分有这一本然的善性,都可以成善。而之所以有上智下愚之分,不是在于本然善性的缺失与否,而是下禀的气质之性有美恶的差别,故而,一方面,这种解释途径可以解释为何现实生活中会有上智下愚的差别,另一方面,又解释了下愚有可以移之理,但由于其自身自暴自弃,才造成了不移的后果。所以程子认为愚是可移的,并非绝对不可以移,虽是“昏愚之至”,然经“渐磨”便可以“移”而不为“愚”了。程尹川的弟子曾向他请教“愚可变否?”他回答说:“可。孔子谓上知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也。……自暴自弃,不肯去学,故移不得。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程氏遗书·卷十八》)愚人本身是具有“移”为不愚之人的可能性的,但如果他不可为学,那么他就是真正的下愚了。这一点也可以在《论语》中找到依据,如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此外,这时候的解释向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即将孟子的性善论引入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此时,解释者将具有强制性解释的经典文本的范围扩大了,即将《孟子》和《论语》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解释,按照这个整体来看,王充等人的“性三品说”就与孟子的性善论相违背,就产生了矛盾。之后,清代学者戴震延续了此种解释向度而略有不同:
“生而下愚,其人难与言礼义,由自绝于学,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怀惠,一旦触其所畏所怀之人,启其心而憬然觉悟,往往有之。苟悔而从善,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同进入知。以不移定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为,知不善而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这里,他首先肯定“愚”具有不可移的一面,又认为“愚”还有可以移的一面, “愚”具有“可移”,“不可移”的二重性。他所张调的是,生而下愚之人,若经过后天的教化和自身的修养,是可以由愚进智的。这里可见中国传统儒学保守主义的一个特征,较为容易产生一些能够持续的观念。
三、总结
虽然中国儒学传统较少关注解释过程中的“前见”方面而更注重对经典的依附和传承,但这种前见依然可以通过不同经典文本的加入而造成解释向度的改变,如上面所体现的《孟子》性善论的补充,以及宋明理学中体现的对佛道的扬弃,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等影响,都造成对经典的解释向度的不同改变。而这种改变本身,恰恰体现了人文学科本身的历史性。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造成自身的改变。进一步地,这些解释本身并不能依据年代的远近,以及其面对的文本范围的大小,而判定其自身的真理性。这也是解释学给我们遗留的问题:我们无法寻找一个合理的标准去判定某一解释的真理性。同样地,在中国儒学解释中,也面临同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逻辑研究(第一卷)(修订本)》作 者: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编 者: 埃尔玛·霍伦斯坦,译 者: 倪梁康 ,出 版 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6-3-1.
[2]《存在与时间》,作者:[德]马丁·海德格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
[3]《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
[4]《论语集释》,程树德著,中华书局,2006.
[5]《孟子字义疏证》,清,戴震著,何文光 整理,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