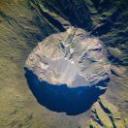浅议余华小说先锋性的体现
时间:2022-08-05 12:02:11

摘要:文类颠覆的目的依然是价值观的颠覆。亚文化小说中价值体系是传统中国道德的全盘接受照章搬用,因为中国的亚文化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而其文类之过于程式化又把这些价值观僵化了,因此对亚文化文类程式的戏仿成为颠覆这些价值观的途径。在中国今日的先锋派作家中,余华是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构筑最敏感的作家,也是表现出最强的颠覆精神的作家。
关键词:余华 先锋性
一、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在对传统小说的主题性颠覆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大量作品中,用“冷漠叙述”的手法热衷于对暴力、灾难、尤其是死亡的叙述。无论是《一九八六年》中疯子对自己的慢条斯理的自戕,还是《古典爱情》中对于“人肉市场”的描写以及《往事与刑罚》、《死亡叙述》、《现实一种》中的死亡叙述,语言都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余华的冷漠叙述极好的实现了对历史(《一九八六年》)、时间(《往事与刑罚》)、理性(《河边的错误》)、爱情(《爱情故事》)、伦理(《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的彻底颠覆。文学评论家李陀曾指出:“我以为余华小说具有一种颠覆性――阅读余华小说犹如身不由己的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余华对鲜血的钟情也由来已久。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写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与死亡”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也是余华颠覆传统的利器。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余华何以在内心积淀如此深厚的暴力情结呢?对于这样的疑问,余华曾经声称“这是作家的难言之隐”,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尽管如此,我们从余华的《现实一种》(1997年意大利版)的前言里仍然不难发现,余华对鲜血和死亡的迷恋,其实与他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他在这篇序言里写道:“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余华在序言里还提到,童年时他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常常在炎热的夏天独自一人跑进里面乘凉。那时的余华几乎听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哭声,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时间长了,面对亡者亲属的哭声,他渐渐失去了常人所有的恐惧与震撼,以至于竟然“觉得那已经不是哭泣了,它们是那么的漫长持久,那么的感动人心,哭声里充满了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
当然,童年经历和儿时记忆绝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的全部原因。余华的创作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他作家,还与他的阅读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余华在谈到写作过程中对材料处理的感觉时曾经坦言:这样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阅读的体验。余华还说,他主要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海明威、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作家的创作技巧和风格对余华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余华谈到“三岛由纪夫一再声称他对死、对恶、对鲜血淋淋的迷恋,在他的作品中,人们也经常读到这些,谁都能知道这是事实。……对于三岛由纪夫来说,这一切都是极为美好的,他的叙述其实就是他的颂歌,他歌颂死亡,歌颂丑恶,歌颂鲜血。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叙述是如此美丽。同时他的美又使人战栗。”余华在赞叹三岛由纪夫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尽管余华在90年代的创作中已经没有了早期作品中的那种血腥和暴力,尽管他把他归结为最初创作的偏激,但那样的创作其实并没有错,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小说的文本,他给予读者的是叙述之后内心的震撼。不是不负责任的宣泄,而是让阅者合书后的反思。原来写“恶”一样能达到审美!
在这些外国作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的细部描写对余华触动很大,在1982年到1986年,余华一直沉陷在对川端康成的崇拜和热爱中,所以那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到处是川端的影子,他感到了川端目光的广阔和悠长。“‘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写一个母亲凝视死去的女儿时的感受。正是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后来,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
如果不是在1986年他读到了卡夫卡,他认为他可能就断送了自己文学前行之路。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让他的小说观念为之一新:他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情是否愉快来决定形式。这就成了开启余华最初小说观念的闸门,在他的《虚伪的作品》中,他几乎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迫不及待地阐述了自己在创作上的新感受:建立一种自由自在的虚构的世界的重要性,并自觉地在小说的形式上开始了探索。我们可以发现,是川端康成教会了余华如何写作,卡夫卡则给了他想象和勇气,使他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扭曲的变形的原始的罪恶)有了特殊的敏感。
对于自幼便胆小怕事且一直循规蹈矩的余华来说,现实秩序与内心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他渴望展示自我内心中的强悍,也渴望分享权力意志所带来的自由冲动,同时它又看到了人性中许多非理性的隐蔽成分,看到了欲望、暴力、死亡组成的权力话语中所包裹的种种悲剧性命运――人性的悲剧。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余华的小说展示了他自己的想象,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颠覆,艺术地呈现了不可逾越的生命悲歌。
二、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在对小说文类性的颠覆
除了主题性颠覆之外,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还明显地表现于他所惯常使用的文类性颠覆,即对旧有的文类实行颠覆性戏仿。
历史在余华的小说中成为首要需要被颠覆的对象。当历史崇高光圈显出原形,只是盲目残杀的刀刃之反光,当以“历史的利益”为名而实行的酷刑被剥去言辞妆饰,历史就失去了意义的权力。不仅历史,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其他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在余华的作品中都受到了颠覆性挑战。如《现实一种》是对中国的家族伦理的无情颠覆,在那个大家庭里,兄弟的“核心家庭”互相残杀,以消灭对方的子嗣为目的。在余华稍后一些的作品中,以上主题性颠覆“逐渐被一种”更为深刻的颠覆性活动-文类性的颠覆所代替。余华采用一种属于“颠覆性戏仿”的反讽手法低调陈述,它通过对中国俗文学中各种写作类别和阅读习惯的戏拟,从而不仅暴露、凸显、而且还否定和颠覆俗文学中承载传统伦理价值的僵化“程式”。《河边的错误》可以被读成是反公案-侦探小说;《古典爱情》是反才子佳人小说;《鲜血梅花》可视为武侠小说的颠覆。这三种都是中国俗文学中有悠久历史的文类,有对大众吸引力历久不衰的种种程式。这些程式被自然化,创造出强有力的现实效果,使俗文学读者完全认同,毫无保留地信以为真,如痴如醉地投入其情景并接受其伦理价值。在余华的作品中,这些程式似乎被遵守了,但被剥夺了其最主要的因果性,他的小说成为亚文类的颠覆性戏仿,程式受到尊重,受到礼遇,没有被恶意扭曲,只是按程式行动的人物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这样程式就成了无根据的空壳,成了为程式而程式,转向自己的否定。先锋派的从形式到技巧实验本身具有对既定政治价值的强烈解构效果,在中国今日的先锋派作家中,余华是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构筑最敏感的作家,也是表现出最强的颠覆精神的作家。
参考文献
[1]李陀.阅读的颠覆[N].文艺报,1988-09-24(5).
[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3]余华.灵魂饭[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
[5]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6]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J].当代作家评论,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