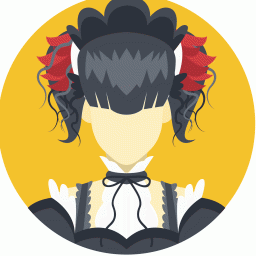《真诰》与“启示录”及“启示文学”
时间:2022-08-01 06:42:32

摘要: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真诰》与“启示录”及“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比较视野,不仅对进一步探讨神仙道教的特质,而且对理解与阐发中西宗教文学的内涵与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真诰》确实具有“启示”(revelation)的意蕴,但在《真诰》中“启示”所依赖的思想基础“末世论”(Eschatology)和“千年王国主义”(Millennialism)都并不充分;《真诰》的“启示”属于一种宇宙论式的启示,从而具有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性质。《真诰》同样具有“启示文学”的文体(literary genres)禀性,但由于在宗教思想和历史渊源上与《启示录》存在显著差异,《真诰》“启示文学”呈出中国宗教文学的鲜明特性。
关键词:启示;真诰;启示录;启示文学;宗教文学
自道教的代化研究开始以来,西方学者就一直较为关注《真诰》,并尝试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真诰》之与“启示”(revelation)即是其中之一。较早可能是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将《真诰》称之为“茅山启示录”(The Mao Shan revelations)。此后,明确认为《真诰》具有“启示”意蕴的,是以法国学者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的论断为代表:“这一象可以拿来和我们所知的世界范围内宗教中伴随着口授文本的启悟描述相比较,最著名的例子是《圣约翰启示录》、《古兰经》以及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在幻觉中对神灵的所见所闻。”虽然“启示”广泛存在于世界各种宗教之中,具有某种普遍性,但像贺碧来这样直接将《真诰》与《新约?启示录》等相联系,可以证明西方学者笔下所谓“茅山启示录”云云并不仅仅是语词的借用或单纯的类比,而是一种比较视野的体。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比较的出发点肇始于《真诰》与《启示录》的文学性上。“启示”与“启示文学”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启示”的本质属性规定了它必然具备一种高华的文学性,表在“启示”文体本身、丰富而奇特的象征和隐喻、戏剧场景及叙事描写,以及冷峻的感情等各个方面,以《但以理书》、《启示录》为代表的启示文学是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的典型事例。《真诰》作为中国东晋时期南方神仙道教上清系的经典,以“仙真降诰”的独特体式、多样化的表方法、灵动的想像和神秘的意境,同样体出较高的文学性而深刻地抒发了宗教体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真诰》与《启示录》在“启示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无疑是一个极富启发并具有重要价值的反思视角。
显然,本土学者对这种来自于西方的比较视野进行正确的解读并进一步思考,对理解与阐发中西宗教文学的内涵与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真诰》与《启示录》的宗教思想核心
《真诰》与《启示录》的比较,首要重心当然还是宗教思想的比较,这是问题赖以成立的基础。
在基督教的义理上,《启示录》是上帝的启示,由耶稣通过天使传给他的仆人――正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的约翰。约翰作为基督耶稣委托的预言者和先知者,写下他所看见的、所发生的以及所要到来的事情――上帝的启示,从而使上帝的教谕宣付到各个教会。《启示录》是以“启示”的方式对正在受到迫害的、面临着行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教会的回答,它以“罪恶世――理想未来”的二元对立,揭示上帝的旨意:在末日灾难以后,神圣在与罪恶的最后战争中终将取得胜利。《启示录》目的是鼓励因信奉耶稣而惨遭迫害的教众们恪守他们的信仰,保持坚强与忍耐,以等待上帝在胜利之日奖赏他忠心子民的“新天新地”的到来。
《启示录》的宗教思想核心是末世论(Eschatology)。“末世论”是一切神学之母,普遍发生于世界各种宗教之中,是文明以后创生型宗教关注根本问题的必然表。“末世论”主要是以“预言”的内容体在“启示”的宗教文本中。以“末世论”为基础而生发了多种思想倾向,如“救世主义”或“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千年王国主义”或“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如果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发展来看,《启示录》集中体的是“千年王国主义”:一切魔鬼被捆绑扔到封闭的无底坑中,而上帝之道的殉教者重新复活,与基督共同掌权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人类所期望的和平与公义通过上帝的权柄得以实。在一千年以后,上帝实行末日的审判,魔鬼遭受第二次死亡,新天新地彻底到来,从此“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千年王国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久远,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各种各样的“千年王国主义”具有以下一些根本特征:第一是当世的腐败与黑暗已经无可救药,末日审判必将来临;第二是人类必须变革,并且就要在世,借助超自然的存在实这种变革;第三是明白此理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变革。
这种末世论包括其重要表弥赛亚思想、千年王国思想都见于古代中国,这是因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实的还是终极的――都有相似之处。比《启示录》稍早一些时候,中国西汉成帝、哀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声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下教我此道”,其说假德运而兼及终世之论,已经具备初级的末世论意蕴。此后又出《太平清领书》亦即《太平经》,尽管是书真伪参半、思想混杂,但已经具有明显的期望太平、逃脱苦难,乃至于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思想观念,显然含有以末世论为基础的“救世主义”和“千年王国主义”因素。后汉之末,天灾频仍,政治黑暗,“太平理想”应乎需要,成为庶民之信仰,并造就宗教之革命。“东汉史籍中,凡称‘妖贼’的,多半是指与太平道思想体系有关并以此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后汉书》卷三十八传论:“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话验神道,或矫妄冕服。”“验神道”之中,民众之“太平理想”是其主干,而精英阶层之图谶神学、德运理论及术数之说,则提供了一种技术性支持。黄巾之起,是这些农民运动的集中爆发。奉事“太平道”并“颇有其书(《太平经》)”的张角,尽管其思想基础同样十分复杂,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说,已经属于较为典型的以末世论为核心的宗教拯救理论,黄巾起义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千年王国”救世运动,开辟了公元一至五世纪风起云涌的民间宗教起义的先河。
在民间宗教运动的基础上,伴随着佛教传播流化的刺激,融汇种种传统信仰因素而形成的道教,无论是较早的北方五斗米道一天师道还是东晋以后的南方神仙道教,都综合地吸收民间宗教的末世观念,同时又糅合佛教教旨,产生出自己的末世主义思想,并相应涌出众多的救世运动。根据小林正美的研究,较为系统的道教末世论,正由上清系所首创,并影响到其它教派,到东晋末期广泛地流行在道教徒之间。《真诰》当然也记录了相关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大灾咎的发生,“五行杀害,四节交掷,金土相
亲,水火结隙,林卉停偃,百川开塞,洪电纵横而啕沸,雷震东西而折裂。天屯见矣,化为阳九之灾;地否阂矣,乃为百六之会。亢悔载穷于乾极,睹群龙示(攫爪?),流血乎坤野,尔乃吉凶互冲,众示灾咎。”二是“壬辰”太平之说和“金阙后圣李君”降世预言。所谓“壬辰”,即终结此世的太平之世来到之年(壬辰之年),同时也是救世英雄的降临之际。“壬辰”太平之说历史较久,至少与谶纬学说大兴密切相关,因此它的具体所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所谓“后圣李君”,就是壬辰之时降临的救世者。此一预言本身也是自东汉太平道至魏晋五斗米道一天师道的一脉相承。“金阙后圣李君”预言未来的谶言在道经中的具体内容不尽一致,前后也屡经变化。它也可能是当时流行更广的李弘图谶传说中的另一系列,以“后世圣君李弘降世”为中心思想,主要在南朝上清系中流传。
在东晋南朝时期的道经如《太上洞渊神咒经》、《上清后圣帝君列纪》中,“天地大终”、“壬辰之年”“真君降世”的学说更为细致具体。总体来说,这种末世论认为一种周期性的天地大灾必将发生,只有经过考验被证明信仰坚定、道德高尚的“种民”,并通过自身的种种努力,才能在救世主――金阙后圣真君――的引领下,“过度壬辰”,进入下一个全新的太平之世。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真诰》中无论是“末世论”还是其重要表“千年王国主义”都是极不充分的。一方面《真诰》并不以当时道教的末世理论为中心内容和宏观背景,不过只是零散的提及,缺乏像《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以上清系为代表的东晋义理化道教的末世论,“是认为此世的终末,是基于天地运行的法则必然会发生的”,因此是一种宇宙末世论。《上清后圣道君列纪》曰:“夫唯二气离合,理物有期,三道亏盈,出处因运,期之至也,因而适之,运有来也,就而抚之”,清楚地表明了“期运”之至实因宇宙规律,而非人事实造就的思想观念。相比之下,犹太一基督教的“末世论”则是一种历史末世论,认为灭亡的灾难、末日审判和最终回归正义、新时代的到来并非自然的规律而是历史与实的必然。这就导致了它对实和人性的彻底悲观和坚决否定,从而主张只有顺从上帝的意旨,并依靠上帝派来的救世主的力量,世界众民才能得救。
宇宙末世论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它奠定了神仙道教通过与宇宙的合一而达到摆脱灾难目的的根本教条。宇宙论的取向与历史的、实的取向存在根本的不同,缺乏真正的末世意蕴。《真诰》是“长生不死”信仰到神仙道教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它的核心思想仍然还是“成仙”。成仙就是以信仰与技术的双重力量达到一种解脱,亦即追求灵肉俱得不死,而不像大多数高等宗教那样追求超越生命,摆脱肉体的束缚而达至精神的永恒。因此,早期各种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诸多道教因素,往往过多地注重于“技术”手段,带有浓厚的“巫术”倾向而缺乏宗教精神,这一点在《真诰》中仍有大量的遗留。
当然,上清道教对此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提升,《真诰》集中体出两方面的突破:第一是开始树立了以坚定信仰而不是药物、禳祓、禁咒等手段实解脱的实践取向,至少强调精神解脱与肉体长生并重,“上论九玄之逸度,下纪万椿之大生”,主张“不为秽欲所惑,不为众邪所诳”,以排除尘世束缚而保全至素,只有“握玄筌以藏领,匿颖镜于纷务,凝神乎山岩之庭,颐真于逸谷之津”、“游蹑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绝空,人事无营”,才能“回日薄之年,反为童婴”,并以肉体不死进至精神的永恒,“仰掷云轮,总辔太空”。甚至融合佛教思想,主张迈出形骸,拔越生死,所谓“欲殖灭度根,当拔生死栽;沉吟堕九泉,但坐惜形骸”,进一步尊显出对精神解脱的重视。第二是解决了与世俗特别是一般价值观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继承吸收了民间中的天堂地狱、首过忏悔观念,以及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建立起“三官按核”、“墓注冢讼”的功过德罪体系,以地狱、天堂的不同归宿强调前世今生积累功德的重要性,从而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脉相承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价值核心,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宗教道德与信条。所有这一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末世论”的观念,同时又实际反映出它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义理化发展,特别是与传统的世界观与伦理价值观的融合趋势。
所以,它不彻底否定实,不进行绝对的道德谴责;不主张末日的审判和救世主的拯救,而强调个人的实践努力,同时不排除技术的力量,比如服食与炼气等。上清道教甚至主张选择某一自然环境以作度灾之府,“辟兵火之灾,见太平圣君”。这种度灾之府并非是上帝的赐予,而是天地自然的形成,“句曲山,其间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顷,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见太平。”因此,它的“拯救”主要是对自我的拯救,一如早期道家那样,主张以保全并发扬“真性”而达至在宇宙间的从容与逍遥。《真诰》全部启示的核心,就是实这种自我解脱。为此,《真诰》中的娓娓教谕,都在强调信仰坚诚、向道勤至的重要性,告诫修道者时时保持警惕,以“水火不能惧、荣华不能惑”之不懈心志,通过仙真的种种考验,同时辅以具体的修炼,层层进阶。可以认为,上清神仙道教更接近于宇宙论式的宗教,“宗教的宇宙论关怀所强调的是力图理解宇宙的基本特征以及在神话和仪式中为人所牢记的层面。各种表象和符号被用来构成一种‘万物存在方式’的宇宙图景。这些表象和符号反映了‘人是什么’以及‘他如何了解他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的不同观点。它们表了一种生活的倾向性,一系列人对其宇宙中自我理解的假设和诠释方式。”一言蔽之,即以人与宇宙的和谐化合为解脱,“口挹香风,眼接三云,俯仰四运,日得成真,视所涯,皆已合神矣。”由此,上清神仙道教当然也就和将人从末世罪恶中解放出来才能达到最后幸福的纯粹的救世宗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二、《真诰》的“启示”内涵
作为宗教概念的“启示”或“天启”,简单地说,就是神向人显示真理或旨意。希腊文apocalypsis的喻指意义是指“暴露”或者“揭去”,意味着移去封闭真理的阻碍。但实际上,所有的启示都是人而不是神对其所处当下的一切内在意义的发,“人创造了他所说的历史,并以此为屏障来掩盖启示的运行。”
《真诰》不是简单的“扶乩”产物,确实具有“启示”的意蕴。但这种“启示”更多地来自于萨满教人神沟通仪式以及“神灵附体”行为。南方地区直至南朝时期仍然“巫风”较盛,留有大量的萨满遗存,上清创教者正是借助于此从而创造了仙真降诰的“启示”形式,同时并进行了义理化的提升。
表面看来,杨羲并不像是真正的萨满――一中国世界中的古巫,他并不是天神之子,也不是献祭者;他不能治病,更不能上天入地或进入阴间召唤灵魂,不具备法力和冒险经历;甚至不能像古代的“巫”那样以舞娱神,他只是被动地接受仙真们的降临。杨羲唯一的禀质,就是能够“通灵”,亦即只有他才能“接真”,并能转达仙真们的旨意。但这恰恰是萨满最核心的质性所在,萨满们的其它一切能力,都是这种通灵能力(交通天地、人神)的准备、铺垫和发挥。萨满交通人神,其核心意义在于揭示了另一个世界,在上
清系的宗教意义上,就是使仙真世界的“奇迹”成为可能。“萨满的‘奇迹’不仅确立了和巩固了传统宗教的结构,而且还刺激和丰富了人们的想像力,消除了梦境与当下实之间的障碍,开启了通往诸神、死者与精灵世界的窗口。”在这一点上,《真诰》所构造出的杨羲并不逊色。尤其重要的,上清创教者对萨满古巫进行了扬弃,在另一个方面构建了理论,亦即通过存思与冥想并辅以其它修炼使得“仙真来游”。依靠个人的修行努力,而不完全通过萨满,这正是上清系义理化的核心。总而言之,上清系的人神交通一方面继承古代萨满教的遗存而强调“通灵”异禀,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修炼,天启的接受者与记录者始终不是上帝所委托的先知和预言人,而是一位对“万物存在方式”的体悟者。
因此,这种“启示”更接近于“宇宙启示”。“宇宙启示”是以宇宙神论作为宗教内部视角的必然结果。如上一节已经论述到的,宇宙论或日宇宙的视角,根本点在于强调与神的内在统一,它在从道家到神仙道教的整体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与以历史和民族的视角而形成“先知启示”的犹太一基督传统迥乎有别。
“宇宙启示”往往导致神秘主义的体验。宗教神秘主义(mysticism)“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元经验的(meta-empirical)、直觉的、对某种非时间、非空间、不朽和永恒之物的统一性体验,无论该物是一个人格神,或者是一个超人格的绝对者,或者仅仅是一种意识状态。它是一种超越了自我的、与某物或者在某物之中的‘一体性’的实,无论这种一体性是在完全的同一性中或者在密切的结合中被体验到。”它的本质是使自身融合到万物的一体性亦即宇宙之中,消除任何的主客体隔阖,而达到一种宁静的愉悦。所以,南方上清系道教尽管具有义理化的提升,并对前此种种实践方式与技术手段进行了较大程度的革新,但因其“宇宙论宗教”以及“宇宙启示”的本质,使之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因素。
《真诰》排斥低级的方术如黄赤合气等,其所尊尚的“并景双修”,倾向于人神的精神和合。《真诰》虽然也重视金丹、服食、导引、炼气等等“技术”方法,但更强调它们与精神活动的融合:“研玄妙之秘诀,诵太上之隐篇,于是高栖于峰岫,并金石而论年耶!”在真人诰语中,真人们所强调的前所未有的修行方式是“存思”,这种修行手段虽然渊源有自,并从《黄庭经》开始就有所发展,但却是在《真诰》中达到了一个极致。《真诰》的“存思”不再仅仅是对身体内神的观照以修炼肉体本身,而是扩大至对一切永恒高尚的超验体的存注与冥想,服日餐霞、奔辰步星,以祛除邪恶、荡涤污秽,使人“聪明朗彻,五藏生华,魂魄制炼,六府安和”,最终仙真来迎,上登太霄。在根本上,它更倾向于一种精神活动而不是肉身修炼。同时,存思的冥想既不完全是内敛与返观,更不是寂灭的入定,它的想象生动灵活,不拘一格,它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这样的精神活动,最终达至与存思对象融合为一,使心灵进入到神圣而永恒的境界。“道成,则同与天地共寓在太无中矣。若洞虚体无,则与太无共寄寓在寂寂中矣。”毫无疑问,上清经法属于一种“自然的”神秘主义,而并非是对神或神性发生深邃体验的“有神的”神秘主义。
三、《真诰》与《启示录》的“启示文学”
《真诰》是一种汇编性的手稿,在某种意义上和《圣经》一样是一部多样化的文体集成。《真诰》和《启示录》在文学意义上的比较,当然是就其某种共同的文学质性而言的。从根本上说,《真诰》与《启示录》得以在文学比较意义上联系起来的是“启示文学”。
在圣经文学的意义上,“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是指以特殊文体(literary genres)以及特殊的文学表方式来承载独特的宗教内容的一种文类作品,它源于古希伯来“先知文学”,公元前165年以后出了一大批作品,并在崛起的基督教中继续发扬光大,《新约》中的约翰《启示录》成为杰出代表。思想上,“首先,启示文学具有将世界截然地分为善与恶的双重性特征。其次,‘启示文学’是关于世界及人类最终命运的文学,主要关心未来事件,特别是那些关于终极历史的事件。”文学性上,“启示”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形式,“启示文学”在语言、故事叙事、戏剧化描写、体裁、风格、结构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特征,但最根本的是象征主义的表方法。按照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理论,所有的“启示”必然都是象征性的,因为神话和象征符号是发并描述神圣事物的表达方式。
尽管犹太基督教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宗教”,但《启示录》的种种象征也并非与具体历史事件一一对应,在这一点上《真诰》同样如此。“启示”作为一种文体,其核心在于它的隐喻意义大于表面的意义。虽然《真诰》的象征可能不像《启示录》那样扑朔难明,但其所具有的隐喻的本质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上,无论从神谕还是从预言、占卜的角度说,天机总是不可用明显的文字泄露而只能以象征和寓言来传达,它需要信仰者用智慧来体悟,获得自己的答案。因此,《真诰》作为一部“仙真降诰”,无愧于“启示文学”的文体禀性。换言之,《真诰》既然具有“启示”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它具有“启示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特征:丰富的象征性与隐喻意义。
但由于在宗教思想和历史渊源上与《启示录》存在显著差异,《真诰》的象征意义当然也就有明显的个性。
文学主体的主观倾向是第一个关键要素。就圣经文学而言,整体《新约》的文学性本身有一些特殊之处。《新约》大体上是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的下层人士的创作,语言简单质朴,并且多有错误,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而接近于民间文学。这个特点是由早期基督教历史状况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真诰》则显出一种复杂的相对性:一方面,《真诰》文本无疑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至少是处于社会中层的士人的撰作,其诗歌和大部分叙事都属于严格的书面文学范畴。它作为一部手稿,书法水平尤高,属于当时的顶尖层面。另一方面,《真诰》同时存在很多口语化或者是“俗语”的对答,与《新约》相同,也有很多流行的和杜撰的词汇。其诗歌虽然词藻华丽、形制俨然,但水平并不很高,许多篇什因此而晦涩不明。总体上,《真诰》的文字水平与当时的杰出的理论著作相距甚远。不过,这种相对性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矛盾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精英性本质,这同样也是上清道教义理化努力的结果。总体而言,《真诰》文学的主体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与《新约》作者――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下层庶民,显乎不同。
作为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宗教寄托,《启示录》重在“更加具体地描绘末日审判的恐怖景象,更明确地用近距离的镜头显大决战的恐怖情景,以及在大决战之后,旧天地毁灭,新天地诞生,弥赛亚的降临,和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实”,因此它以奇异甚至是恐怖的象征为主:龙、异兽、血、鼓号、蝗虫、无底坑、硫磺火湖……。总之,《启示录》种种象征符号所要表的,是“撒旦与天使的天上争战与敌基督者在地上的横行霸道构成一幅立体的整个宇宙大变动的恐怖图画。……即天地间充满不祥的预兆――天灾人祸,战争、动乱与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甚至可以说启示文学所揭示的中心内容就是末世这突如其来的最后的日子,它以全地普遍的、巨大的灾难为先兆,所以启示文学无不极力渲染末世
的黑暗、恐怖、惨烈。”
而《真诰》则以华丽的象征展示仙境的美妙,如琼台、紫宫、绿景、朱房、天池、绛云、灵轸、琅轩、金庭、玉圃、香风、玄峰等等。这些都不是世间之物,而是某种想像的创造。即使是一些具体物件,也被加以种种新的美化和陌生化,如“白羽紫盖”、“佩玉金铛”、“流金之玲”、“金真玉光”、“八景之舆”、“白羽黑翮”等,不仅成为仙道的象征,而且成为法力之器。《真诰》虽然同样注重仙、尘的二元对立,但重在强调仙界之美,而不在揭示尘世之恶,所以它描绘俗世的文字不过是“尘滓”、“浊波”、“泥渎”、“尘波”、“沉疴”等泛泛之语,与《启示录》中详细的恐怖图画,相差极大。
《启示录》也有上帝之城的描写,但并不是它的主要目标。同时,《启示录》中的上帝之城“金碧辉煌、珠光宝气,连每块石头也仿佛冒着蓝宝石般的火焰”,则是一个燃烧的火焰、炽热的天体的神谕原型,它象征着通过水深火热的磨难而达至天国。这种象征在中国宗教中只能属于地狱世界,而绝不会出在天堂图景中,因为“天”作为宇宙论宗教中人的最后归宿,它必然就只能是和谐的与平静的。
与前述基本主体倾向相关联的,尽管《真诰》的比喻象征繁杂丰富,但却不仅没有《启示录》那样的“异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象征并不与实和预言相关。《启示录》中的魔鬼巨龙、巴比伦、兽,以及七印、七号、七碗,显然都是以象征手法指向某种实状况,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奇异的象征一定会被约翰最初的听众或读者一眼认出。《真诰》的数字、色彩、物件、谜语或隐语并不具备《启示录》的指向实的隐喻意义,而是以丰富的技术性和秘密性内容指向人体、宇宙的本质规律,这是它神秘主义的特质所决定的。中国古代信仰以宇宙论视角为基石,力求通过技术性的分析发宇宙、人类社会的终极规律。由于认识水平所限,他们往往从朴素直观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技术分析,因此首先建立起“互渗”的观念,将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系统,然后将它化为某种运算方式,又运用到各种物质的与社会的规律的探讨中,其直接的成果就是以“阴阳五行观念”为代表的一种思维方法、符号与关联模式。表在道教特别是上清神仙道教中,就是关于金丹、服食、导引、炼气以及存思冥想方法的神秘隐语系统,《真诰》中如“交梨火枣”、“山源天马”、“泥丸玄华”等,比比皆是。显然,尽管它们充满奇特,但并不是《启示录》那样惊心动目的“异象”,更不是关于实的隐喻。
由此,《真诰》与《启示录》所共同拥有的多样化体裁,如叙事、戏剧化场景、诗歌、书信形式等,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真诰》的叙事主要是神仙事迹或修炼故事,以寓言文体实劝讽向道的功能。《真诰》也可以视为一场演出持续数年的宏大戏剧,每一次降诰都是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但它极为细致的戏剧化叙事却不像《启示录》那样重在强调末日的背景,而是旨在开启一个传达教义的喻指空间,并诱导接受者发挥他们的想像力以填补其中的意义空白。如安妃与杨羲的相会,乃是以男女因缘际会的戏剧效果,喻指一种“并景双修”新的人神化合之道,使向道者由事兴感,妙达真旨。因此,《真诰》戏剧化场景本身仍不过是一种宇宙论式谕示。而《真诰》的诗歌更与《启示录》乃至《圣经》中的所有诗篇都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它是一种玄思化的诗歌,如同东晋玄言诗用诗歌来表达玄学思考一样,《真诰》用大量的诗歌传达其宗教旨趣,而这些诗歌尽管在感情上和内容上因讽喻教旨而缺乏文学价值,但仍然能以丰富的想像营造出瑰丽的图景,以传达那种与道合一的神秘性体验,体出以象寄意、委婉含蓄的典雅文学特征。
最后,所有关于《真诰》与《启示录》在“启示文学”意义上的诸多文学性的比较,都可以总结到文学风格这一关键的美学要素上去。毫无疑问,《启示录》具有史诗的风格特征:规模宏大、情感丰富、气氛激昂。利兰?肯顿总结认为,《启示录》不仅采用了史诗的表手法,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具有彻底的史诗性质,表了末日来临与拯救的剧烈的矛盾与冲突,叙述了基督征服撒旦与魔鬼并建立永恒天国的故事。而《真诰》则以其秘密神谕睁性质,呈出一种属于修道者个人的乌托邦式风格:华丽、浪漫、飘逸、宁静和愉悦,与《庄》、《骚》及魏晋游仙诗以来的神仙美学一脉相承。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在《真诰》与“启示”、《启示录》的比较视野下,神仙道教的宇宙论视角和神秘主义的特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当进一步从“启示文学”的观照角度切人时,《真诰》及后世神仙道教文学的整体特征亦有了清楚的展。并且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文学特征与其宇宙论宗教的思想基础存在逻辑的关联。如果从这一反思视角出发并继续深入研究,关于中国古代宗教文学的根本特质及其内在基础,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合理而圆满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