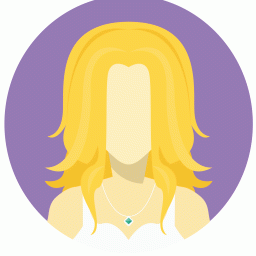打工诗歌与和谐文化建设
时间:2022-08-01 01:54:50

近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南中国沿海的展开,成千上万的民工涌进广东“珠三角”进厂“打工”。在这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和人员流动的浪潮中,中国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发生着激烈变化。伴随着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转型与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层与新的文化。“底层”和“打工诗歌”就是这一转型与分化的产物。“打工诗歌”随着打工底层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中国当代“打工诗歌”正是当代底层社会的“心声”和“镜子”。 “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诗人的精神升华以及打工群体的精神快餐,在表达底层诉求、维系底层和谐上发挥着相当的文化功能。
中国当代打工诗歌正是当代打工诗人内心情志的表现,它反映了当代打工诗人这一特殊群体独有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诉求。第一批打工诗人大都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和农村,随着南下淘金的民工潮,走进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珠三角的工厂。从内陆落后的乡村到沿海发达的城市,从散漫自在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到高度封闭的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从充满田园牧歌气息的乡村文化到繁华而冰冷的都市商业文化,这一系列的境遇变迁与碰撞,在敏感的打工群体中造就了这一时代的打工诗人。“打工”,这一沧桑的词语,它链接着沧桑的“打工诗人”和沧桑的“打工诗歌”,它使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底层身份”与“底层写作”第一次对接。“打工诗人”出生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在现代化的城市生产环境中又处于都市社会的底层。这种双重底层的身份使打工诗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往往处于碰撞和裂变之中。由于社会转型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作为打工者的打工诗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困惑。他们出行难,找工难,做工难,维权难,回家难,感情难,子女难……然而,亲身遭遇的不平与困境并没有使这批有文化有梦想的打工诗人自暴自弃或者以暴制暴;相反,他们将苦难的遭际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在紧张的劳作的间隙,打工诗人通过“打工诗歌”的“书写”活动,舒缓、稀释和转移了打工的痛苦、紧张和愤懑。“打工诗歌”,不仅是一代打工者生存性的证明(柳东妩《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而且,还将这种形而下的生存性转化为形而上的精神性(张未民《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关于打工诗歌的思考》)。正是这种源自内心的不自觉的打工诗歌的“书写”活动,让打工诗人暂时忘却了身受的苦难与不平,进入了一个精神上的寻求与探索。“打工诗歌”由初期“愤青”式的痛感抒发升华到成熟期的“为漂泊的青春作证”(《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打工族》2002年12月下半月)。打工诗人在业余的打工诗歌书写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与出路,他们在“经济淘金”失败困境中意外地走上了“精神淘金”之途。改革开放30年来,在广东这片热土上,一批背井离乡的有文化的打工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的“打工诗歌”创作,到90年代“显山露水”,进入新世纪“树旗组团”,打工诗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打工诗歌越来越红火。2001年夏天,打工诗人自发结合在一起,在广东惠州自费创办了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标志着多年来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分散的打工诗人开始团体的呐喊,显示了打工诗人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的“打工者”身份决定了他们与体制之内的职业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即使是所谓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肌质”和功能的不同。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诗人的精神“肌质”,不仅抚慰了打工诗人的痛苦,引领其精神追求,而且,作为真正打工群体的代言人,在建构社会和谐文化功能上,满足和引领了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市场经济语境中,“打工诗歌”破土而出,逐渐显山露水,是与它背后庞大的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分不开的。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切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形象、昂扬的情感,给予与打工诗人同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2007年一部命名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诗集出版不到25天,1000册即销售一空。“打工诗歌”以其满足了庞大的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而获得了存在的依据,同时对打工群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打工诗歌”以其特有的文化建构功能逐渐赢得了主流文学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和肯定。2002年1月,《北京文学》辟出两个专版刊发“打工者之歌”。同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报告文学《为千百万打工者立碑》,报道“打工诗歌”作者生存状态和办刊历程。2005年1月,面向打工族的“全国鲲鹏文学奖”设立并评奖。2006年11月上半月,《诗刊》首次以“打工诗选”的名义,推出20位作者的“打工诗歌”。
在20余年的打工诗歌历史演进中,打工诗歌抒情主体经历了由“小我”到“大我”,由个体自发到群体自觉的转变,打工诗歌逐渐成为打工群体的一面精神旗帜。正如一首打工诗表白的: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罗德远《我们是打工者》)。
“打工诗歌”作为社会底层的镜子和心声,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转型色彩和平等和谐的社会心理诉求。打工诗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它记录着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打工诗歌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如农民工进城问题、打工者身份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这些底层问题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问题。打工诗歌所体现的问题意识超越了打工者一己的身心诉求,而成为底层弱势社会群体的集体诉求。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法制正在完善的今天,在社会底层声音表达渠道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打工诗歌为表达底层弱势声音,抒发底层内心的积郁,提供了一个渠道,打开了一个窗口。打工诗歌,不仅调节了底层个体与群体的苦闷,而且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的不和谐的关系。从打工诗歌对社会结构不和谐的诉求中,我们日益感到重建社会正义与平等的重要与迫不及待,我们日益感到建构和谐社会的必要。值得庆幸的是,打工诗歌,从自发到自觉,从民间身份到为主流社会认可,从底层的自我救赎到全社会的关注支持,这些变化足以表明打工诗歌所承担的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所在。
打工诗歌以关注打工者为中心的社会问题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调节功用。这种文化调节功用在渠道和方式上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社会结构各阶层之间。打工诗歌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和阐释,可以调节社会文化生态的平衡,从而调节社会关系的和谐平衡。中国诗歌自古就有“兴观群怨”的功用。我们相信, 在资讯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打工诗歌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底层弱势声音将得到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打工诗歌所拯救的,将不仅是打工诗人一己的个人命运,还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良心和人性的回归。打工诗歌所肩负的文化价值,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怎么强调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