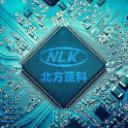她爱上诗 第9期
时间:2022-08-01 10:54:47
小女孩的时候,曾经也痴迷过新诗。为了买一本诗集,步行很远很远,穿过村庄和田野,去另一个小镇上的书店买书,为此,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那个书店的店名“夜雨”以及那个瘦高清白的店主人。在他的书店里,我买过余光中、泰戈尔、席慕容等的诗集。那个时候,我还读顾城,读北岛,读戴望舒,读舒婷,读徐志摩。每当电台里乔榛朗诵《雨巷》,丁建华朗诵《致橡树》时,我都激动不已。学校举行朗诵比赛,我读余光中的《民歌》,获奖。在班级的新春联欢上,我读余光中的《乡愁》,读到自己哽咽。“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等等。那些或朦胧或忧伤或激昂或哲理的诗句,给一个乡村女孩平淡苍白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绮丽的色彩。读到一首深深震撼心灵的诗句后,女孩儿会凝入沉思中,眼神也迷离起来,思绪不知飘忽到何方,也会拿起笔,写下稚嫩的诗句,在班级和学校的墙报上涂鸦上随性写下的断行。或许,青春就是一首诗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诗歌从我的生活中逐渐远离,工作、结婚、生女,每天睁开眼就是开门七件事,生活不再像是一首诗,而是一篇平淡朴实的纪实散文了,直到她,我的女儿,重新让我回忆起那段青春朦胧的岁月,重新让我回到诗歌的世界。
在女儿的阅读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去让她读某一样类型的文学作品,除了适合她的年龄特点之外,基本上和我自己的阅读一样,都是随兴所至。我清晰记得她第一次和我兴奋谈起的第一个诗人是西班牙的洛尔迦。那是她在读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中,邂逅了洛尔迦,她一见就喜,和我大谈洛尔迦的生平、洛尔迦的诗句。“吉他/开始哭泣,黎明的酒杯/破碎。”这恐怕是她最爱的一句了,就连没有读过洛尔迦的我也被她感染得耳熟能详。另一个让她痴迷的诗人是聂鲁达,不知她在哪儿读到了聂鲁达的诗,之后央求我给她借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聂鲁达的《诗歌总集》。这本书几乎被她放在桌边床头,随时翻读。她被聂鲁达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繁复的意象以及南美大地的壮阔丰美所深深震撼。对聂鲁达的长诗《大地上的灯》,她写有这样的评论:
亚美利加州的爱 ——读《大地上的灯》
《大地上的灯》是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中的第一首长诗。
茂密的雨林,缠绕着巨蟒的参天巨树,潜伏着鳄鱼的危机四伏的大河,突兀的山岭,飞鹰与邦巴斯草原,地底下暗黑岩石的矿藏,古印第安民族建造的金字塔与神秘的鲜血淋漓的祭祀仪式……那个与我们隔着整片太平洋的南半球的大洲在诗歌中展现出了奇丽而又壮观的景色,但那不仅仅是景色,而是生命,仿佛远古时期施下的神秘巫术,给予那里一切万物涌动的生命与灵魂。名为亚美利加的大地,诗人的父亲,与母亲。
我同样惊异于一系列事物叠加产生的令人震撼的效果:
红木制成的
羽箭的箭杆,
聚集在花的阁楼的铁器,
我大地上兀鹰指挥者
高翔的利爪,
陌生的流水,邪恶的太阳,
凶暴的泡沫浪潮,
潜伏的鲨鱼,
极地崇岭的尖齿,
披着羽毛的蛇神,
带着稀罕的蓝色毒汁,
飞鸟和蚁群
迁徙时带来的古老热病,
连片的沼泽,
酸刺的蝴蝶,
近似金属的木头,
……
我知道诗歌经过翻译总会产生某些偏差,但尽管如此,这一段依然精彩得使我浑身发抖。如此波澜壮阔的音韵与形象之美!如此迷人,如此瑰丽!
这也是一片在最近的数百年里长期受到杀戮、侵略与掠夺的土地,充满了压迫与反抗,耻辱与光荣,卑鄙的与高贵的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但我们记住的总是它独特的带着苦难与顽强的美,是诗人与亚美利加洲的爱,是亚美利加洲对子女的爱,即便在战争之中,在幻灭之中。
忘掉那些植物、野兽、大河、矿藏,飞鸟与人类吧!终究这只是生命,生命是大地上的灯,少有这样被书写与歌唱的生命。
被她喜爱过的诗人还有里尔克、波德莱尔,中国的海子。关于海子,有意思的是,她最喜爱的倒并不是那首人人都能背得出来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而是《打钟》,“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打钟的黄脸汉子/吐了一口鲜血”。后来她听到周云蓬的歌,对周云蓬谱曲演唱的海子的《九月》也很有感觉——“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几乎是不读诗了,但是因为曾经热爱过,所以并没有忘怀。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这样一本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我买了一本回家,搁在书架上都没去看,却被女儿看到了,她读了,非常喜欢。和我大谈北岛、郭路生。尤其是郭路生,我是在读了徐晓的《半生为人》时才知道他的,而他的另一个名字食指,我是在极为偶然的机会读到的一期《今天》上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的诗人,但并不知道两者就是同一个人。直到有一次,女儿向我提起郭路生,提起他的《相信未来》,提起他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才知道原来郭路生就是食指。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对她的冲击力也不小,为此她写过一篇读后感想。
哀悼与祝福——读《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作者笔名“食指”,原名郭路生,这首诗作于1968年,正是此时,中大批北京知青下放到农村,作者也不例外。
我想象过作者离开北京时的情景,到底是怎样的场面触动了他怎样的情绪使他写下了这样动人的诗句呢?“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我几乎没经历过分离,更没有“哭喊着抓住一只手”的经历。不过从许多文学作品中我大致也可以理解作者的一部分情感。当时的故事片记录过,红脸的青年们将头伸出窗外,大喊万岁。这和书里写得不一样,书中似乎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随着汽笛的拉响,尖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想抓住一只手,因为那的确是他们“最后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