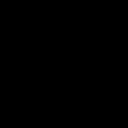从“得意忘言”到“文学自觉”
时间:2022-08-01 03:19:15

作者简介:胡小曼,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2012级研究生
摘要:“言意之辩”是魏晋南北朝玄学中一个经常涉及的重要论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这个哲学中的唯心命题,在文学的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却具有正确和深刻的内涵”。尤其是当文学艺术走向自觉和独立的时候,“言意之辩”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规律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言意之辨” 文学的自觉 精神本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从魏晋著名思想家王弼重“意”而不重“象”的思想观点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哲学范畴中的“言意”也早已不是处在一个向度上的概念。他把得意看作是目的,把言看作是得意的一种手段,得了意,言、象均可忘掉。“得意忘言说”注重的是对精神本体的体悟和把握。王弼承认象只有通过言才能了解,所以对意的把握最后还要归结到言。然而意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更玄妙、更幽微的意,便非言、象所能表述的。
王弼等人所讨论的,终究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就人的认识和表现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或特点而说的。但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影响一切精神文明的思想背景。哲学上的“言不尽意”是诗学上的“言不尽意”的衍化源。这场哲学上的“言意之辩”,广泛地渗透到美学、文学领域,对美学理论和美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文学思维理论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文学史家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进程中是很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所谓“自觉”,就是说人们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批评水平的提高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都是自觉时代的标志。
这一时期,关于文学思维理论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奠基的时代,也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期。其一是关于思维特征的,这主要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运动规律、基本特征,以及灵感思维、文学体验、创作冲动等问题的研究。其二是关于思维方式的,主要涉及在审美心态下,物、意、言三者的矛盾和统一,尤其是文学意象的特征及其语符化的问题。
言意关系,是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讨论得最热烈的重要问题之一。那一时期, 关于言意关系的看法有三种:“言不尽意”说;“言尽意”说;“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后者最为重要,王弼依此原则建立了魏晋玄学,它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一个美学命题。它是魏晋玄学的基础,并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启示,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走向思辨性、系统性的内在动力。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文学自觉除了从文学审美外在形态以及审美向度的进步之外,文学理论系统系的建立也是其标志之一。而这一时期以言意关系理论探讨为代表的王弼等人的观点的阐释无疑也是文学真正走向成熟与自觉的标志。
二.文学审美和创作的自觉
“言意之辩”由来已久,早在《庄子》天道篇中就有:“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就是说,语言难以传达出深奥的事理来。《周易》也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到了魏晋时代。随着哲学上的言意之辩的流行,言能不能尽意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从而成为玄学名理的重要内容。玄学家们曾对言、意、象(物)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从总体上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规律,并试图通过“忘言”、“忘象”的具体办法,希望由有限的“言”、“象”去领悟无限的“意”。正是在这点上,玄学和文学贯通了起来。玄学上的“忘言”、“忘象”,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引导人们形而上学的看问题,不要囿于文字而忘了意理。玄学上的这场争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恰恰启示文学家对“言”的重视。从文学的审美规律来讲,固然可以“得意忘言”,而在审美创作方面,却无法忘却言的存在。在王弼的逻辑框架中,在“言―象―意”的认识链条中,“意”固然是目的,而迈向目的的第一步却是“言”。美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其表现总是具体可感的,又脱离不了有限。成功的作品即在于通过有限表现无限。正因为“言不尽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创造的特殊规律,这才使得它对当时及后世的文艺创作及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人们在审美活动中产生了种种感受、联想等,要将这些感受传达给他人,必须要借助语言等物质手段。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类的思维可以不凭借语言。艺术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或形象思维,不一定依赖语言手段。这是指创作思维阶段的特点,要将思维传达出来,则必须借助语言等。无论哲学和文学,讲超越语言,讲“去言”、“忘言”,从原生意义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思想感情的交流,都需通过语言文字。何况,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其创作思维的运行中不可能没有语言因素的介入。诗人之所以被人称为语言大师,正是由于他们对语言的艺术加工。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不论多么深邃、奇妙,没有语言这一载体,文学本体就无从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显现伴随着语言,语言的通塞关乎文思的利钝,关乎审美意象的传达。对文学创作而言,就要把审美意象化为语言文字。所以作家们总是致力于传达技巧的磨练,总是追求语言能够充分达意,将审美意象通过语言文字纤毫必露地显现出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另一方面,变动不居而又错综复杂的审美感受,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在玄学“言意之辩”中,“意”指精神本体。所谓“言不尽意”是指人们在理性思维时不能用语言文字把头脑中的概念,完全准确地表搭出来。对于文学创作来讲,这个“意”,不仅仅是理性思维,抽象概念,同时也包含情感、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这种以情感为枢纽的审美感受,具有比概念更复杂的特性,更难于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之五),就说明作者捕捉、感受到了审美对象的意蕴,形成了一种主体情思,但这种情思又苦于用语言来表达。在创作实践中,“言不达意”的苦恼,时时折磨着每一个作者。西晋卢湛《答刘琨诗书》提出:“是以仰惟先情,俯揽今遇,感念存亡,触物眷恋。《易》 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懑,谨贡诗一首。”卢湛在这里指出,自己“感存念亡,触物眷恋”的复杂感情,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
以上似乎都是在讨论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美学上的体现,但这种迹象也告诉我们,文学创作不仅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书写记录”,而是从“意象”等等层面上探求其审美意义,让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加“专业”,在“得意”后不忘言说藏在这一文学美学理论背后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蓉:《论“言意之辩”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第19卷,第4期。
[2]戴林:《试论魏晋言意之辩》,《贵州教有学院学报(社抖版)》,1992年第2期。
[3]季水河:《“ 言意之辨” 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系统性》,《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2、3期合刊。
[4]刘琦、徐潜:《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维理论的发展》,《文艺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