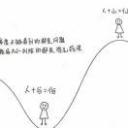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 世界性的联合
时间:2022-07-31 06:15:57

在德国卡塞尔(Kassel)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由于得到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保持着相对独立而严肃的学术立场,卡塞尔文献展一直被视为当代国际艺术界的重要坐标,在挑选策展人与艺术家时,更注重其在学术上的造诣与艺术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深度。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在6月9日拉开帷幕后,将在截止9月16日之前的这100天时间里,展出来自55个国家的115位艺术家带来的670件作品,包括雕塑、表演、装置、研究、档案资料与策展项目、绘画、摄影、影片与视频、文本与音频作品,以及艺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对象和实验。
担任本届艺术总监的是来自美国的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在此之前,她曾以策展人的身份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旗下的PS1工作,时任都灵Castello di Rivoli当代艺术馆馆长。2008年,这位专门研究“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艺术史学者曾负责主持悉尼双年展。
据卡洛琳表示,本届文献展侧重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将质疑“经济增长中人们所坚持的信念”,并由整体主义与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所推动。她将卡塞尔文献展理解为一个公开的实验场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探究对当代生活的理解和观点。
有趣的是,关于本届文献展参展人员,官网上列出的并不是“参展艺术家”名单,而统称为“参与者”,艺术家只是几十种参与者里的一个类别,其他还有活动家、动物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等等。对此,卡洛琳解释道,现阶段急需全球脑力劳动者联盟,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专业人士,都需要站到一起发声,一起工作,共同提出命题,而从历史角度看,“艺术家”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她希望将文献展关注的范围从单一的视觉艺术扩展到整个文化范畴以及科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因而指出“本届文献展旨在探索不同知识形式如何参与到重新塑造世界艺术的实践中。可能有些参与者的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均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其行为、姿态、观念与知识,艺术应该是海纳百川的”。
此外本届文献展在展区分布上也打破了常规,除了分布于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文化火车站(Kulturbahnhof)、文献展厅(Kulturbahnhof)、橘园宫(Orangerie)、宾丁啤酒厂(Binding-Brauerei)等常设展区,文献展还延伸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设有一个单独的展览场地,并进行一系列的研讨会。
Q:此次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是“舞蹈,曾经是狂野不羁的,声嘶力竭的,摇曳有声的,铿锵有力的,神魂颠倒的,摸爬滚打的,经久不歇的”(The dance was very frenetic, lively, rattling, clanging, rolling, contorted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 有何特殊用意吗?
A:这更像是一个口号。我试图创造出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们能构想出意象图景, 让我们能对其形式与形状有感官上的认识,一读便能感知其准确的意蕴;而且当我们读到它的结尾的时候, 却又已忘记了它的开头。因此你可以说它是为了避免概念化, 避免陈旧话题而进行一次语言构建。这个句子实际上是来源于对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一种名为“班波拉舞”(Bamboula)的奴隶舞蹈的描述性文字。班波拉舞具有十分性感的特质, 在1830年左右被立法禁止了, 因为奴隶主认为该舞蹈过于狂野, 有煽动奴隶自我解放的革命性倾向。当时正值海地革命胜利后不久, 整个美国社会对革命可谓谈虎色变, 因此该舞蹈的非法化也就在所难免。“班波拉”这个名字在当时还被用来指作。它同时也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德国女子工读学校中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我这里说的工读学校是指那些调教问题女孩的学校, 而非那些改造女罪犯的看守所。在加入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之前乌莉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曾是一名记者,她曾在卡塞尔郊外一个叫Ursachen的小城为德国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关于女子工读学校的纪录片。她将该片冠以“班波拉”的名字, 因为它代表了解放或混乱的一瞬,同时它也在那所工读学校女生中颇为流行。该片最终没能在德国电视上放映,因为当局认为向公众播放一个恐怖主义者的作品不合时宜。最终存世的只有一个广播剧与一部电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皮埃尔·雨格(Pirre Huygue)曾于里昂在他的“移动电视”项目中放映), 在当时也属地下流通的东西。这就是该词的大致故事背景, 同时它还与卡塞尔附近的某个地点有关联,此次文献展的部分灵感就来源于该地。那是一座被称作Breitenau的班尼帝克汀修道院, 始建于 12世纪。我曾带参加此次文献展的所有艺术家拜访过。那里最早是一所修道院,然后变成了感化院, 再后来又成了贫民收容所,在19世纪70年代又被改造成了俾斯麦时期的一所监狱。俾斯麦下令在这座神奇绮丽的宗教厅堂里遍竖高墙, 分隔出一间间的牢房。魏玛共和国曾在20世纪早期将其作为关押罪犯、 与乞丐的地方。纳粹也曾将其作为集中营使用,专门关押那些在卡塞尔的军工厂里生产武器与坦克的苦力囚犯。当时甚至还曾盛传一句话, 那就是“老实点,当心被送去Breitenau”。它不是一个死囚集中营,只是一个实施惩戒的地方。每个犯人在这里关押的时间不会超过50天。它的主要目的是训诫苦力。战后该集中营被关闭,被改造成一所女子工读学校后再次开放,今天那里已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Q:那么你如何定义此次文献展呢? 也定义成一个 “集中营”吗? 或者说你都定义了何种类型的项目?你在那里都建立了什么类型的“医院”?
A:一座疯人院!舞蹈指导杰罗姆·贝尔(Jér?me Bel)就正在与瑞士的一个由精神病患者组成的剧团合作,计划上演一场关于傻子之形态的精彩剧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傻子之形态,但谁才是真正的傻子呢? 这一剧目正在被精心筹备,将在一个叫Kaska的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废弃电影院里演出。这出剧就是此次文献展口号内容的一个范例。你知道,这一口号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对某种能量与过程的表述。用更连贯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一个概念。我不想让它只传达一种关于肤浅或浮躁态度的意味,而是能够给予片刻的宽慰。我常常思考这个世界以及它的金融化趋势,思考那些制造出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劳动条件,思考那些持续不断的崩溃与复苏,思考与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未来走向。从科技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以一个特定的事实为特征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是由知识产品所驱动的。软件设计者等人是内容的制造者。信息的流通,信息的获取以及信息的控制是权力集中的领域。因此,艺术家是一类身处奇怪位置的工人,因为一方面他们是21世纪前卫的被大众疏离的非物质劳动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与软件设计师不同,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催生解放的空间。在这样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悖论下,在认知资本主义的领域里,我们通常都想避免或抗拒或找到一个新出路。在那场讨论里,我决定不要概念。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诱导。它只是我为此次文献展的艺术作品与其它艺术过程创造空间的一个途径。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信奉某种怀疑哲学。我觉得怀疑论根本就不是一个消极的观点,它其实是相当积极的,倡导继续探求。一届回避特定话题的文献展是有其密度与强度的。你可以说它很抽象。这就如同你问一位抽象派画家“这幅画是关于什么的?”,在内容驱动艺术些许年后, 你可以说从那个角度看它是一种抽象的内容。我所做的就是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考量并回答了那个问题。我将其视作一个结构性的原则,而非一个题材、一个主题, 甚至一种风格或对当下艺术圈所发生的事件的解读。我已经对艺术家或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四个位置进行了考量。
Q:分别是哪四个位置呢?
A:这四个形态和态度决定了展览的形式。
当你被围困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当马奈在巴黎公社期间被军队包围的时候他做了什么? 在围困的情境之下你会怎么做? 或者说如果你是当今喀布尔的一名艺术家, 或诗人, 或作家, 或一个普通人,而你在过去的30年里都处于被围困或包围的情境下, 这时你会怎么做? 内战、时期、外国占领,一直上溯到英国阿富汗战争时期……这已是当今世界司空见惯的一类情形。
另一类情形是处于退却或隐退的状态下。当你从一个地方或状态中退却或退出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 高更去了塔希提岛,他从此与艺术世界隔绝了。隐退就如同莫兰迪所说,“我被法西斯者包围, 但我还是画我的瓶子”。政治哲学中的一大争论焦点就是逃离, 以及关于罢工可归溯至意大利自由派的观点。我有一半意大利血统,而且我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意大利, 所以很明显我受这些意大利思想家的影响。我对这种从知识生产中抽身而退的问题很感兴趣。我总在想,从这种状态中会诞生出什么样的艺术呢?
第三种位置是希望的状态。当你处于希望的状态中时你会做些什么?艺术家在希望的状态下往往什么艺术作品都做不出来。埃及爆发解放广场革命后我打电话竟找不到一个艺术家, 因为他们都忙着革命呢。或者再比如马列维奇, 他在十月革命时完全停止了绘画, 积极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了。
第四种是“在舞台中心”的状态。当你处于表演或位于舞台中心的状态下时你会做些什么? 这是一种类似youtube以及facebook时代的被关注状态。大众关注的是他们眼里的大师。如果你知道提诺·赛格尔(Tino Seghal)有过一个作品《这个变奏》, 那是一个尤为复杂同时也拥有众多参与者的一个作品, 你就能明白这一状态。
上述这些情形同时也是与地点有关联的。只有大约80%的展览是在卡塞尔举行,其它地方的展览平台则是与卡塞尔同时进行的。
Q:比如哪些, 你能举些例子么?
A:比如, 我们现在正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做一个叫“开罗研讨会”的艺术项目。这个项目由莎拉·瑞夫奇(Sarah Rifky)与丘斯·马丁内兹(Chus Martinez)合作开展。我不喜欢“策展人”这个称谓, 因为不太喜欢这个词所透出来的权威感。我喜欢“人”这个称呼。7月, “开罗研讨会”将探索希望以及与睡眠有关的希望状态。届时将会有众多艺术家参加,包括朱莉·马赫瑞图(Julie Mehretu), 她除了参加“开罗研讨会”外还将在卡塞尔展出她的作品。在亚历山大不可能举办展览, 因为那里到处洋溢着希望的氛围。在那样的氛围里, 艺术家都忙着做其他事情去了。
8月,在加拿大的班夫还将有一个以“隐退”为主题的项目。这个项目将在一个度假区里举行, 由文献展的另一位人凯蒂·斯科特(Kitty Scott)与我合作推出。我们将把班夫郊外森林里的那些小屋利用起来,作为这个项目的活动场所。届时将会有一些哲学家、艺术家等来参加, 比如皮埃尔·雨格(Pierre Huygue)。他来参加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觉得他在法国民族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个人艺术作品很好地反映了隐退或退却的主题。参加者还将包括来自布达佩斯的哲学家加斯帕·米克罗斯·塔玛斯(Gáspár Miklós Tamás)。这个项目将包含一个展览,因为当艺术家处于隐退状态下时他们会有独立作品创作出来。
上面我提到的第四个位置则对应着我们在阿富汗喀布尔策划的一系列研讨会、艺术工坊以及一个群展。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多次前往阿富汗,与另一个人安德里亚·韦里阿尼(Andrea Viliani)开展紧密合作。安德里亚对阿里杰罗·波提(Alighiero Boetti)的“一个旅馆”很着迷。于是我就随我的顾问迈克· 陶席格(Michael Taussig)与弗朗西斯(Francis Al?s)以及阿富汗艺术家马里阿姆·迦尼(Mariam Ghani)等人前往喀布尔, 共同探寻“一个旅馆”。马里奥·加西亚·托雷斯(Mario Garcia Torres)正在围绕波提的这个项目开展抗议活动。我们还去探访了巴米扬大佛, 很遗憾它们在2001年3月6日被炸毁, 比纽约双子塔的倒塌还早6个月。这东西两座大佛的被毁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对我来说, 这反映了数码时代的冲突。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存在使得展示它们的图片成为可能, 它们也许就不会被毁。它们历经2000年沧桑岁月屹立未倒, 最终却在这样一个数码时代被毁灭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图片很容易就可以被传遍全球, 也很容易就被删除。
我常常思考物体与物质的脆弱性, 以及物质与物体为何重要的问题。这也是阿富汗之旅终于成行的原因之一。原本只打算作为研究性考察活动,后来却成为了一个决定,因为我对阿富汗存在的被围困的状况很感兴趣, 而且我还想到了卡塞尔, 想到了卡塞尔文献展如何于二战后在一座几近被毁灭的废墟之城中初创的经历。他们当时展出的20世纪早期艺术家的作品,在纳粹政权时期是被禁的。这些作品还不算是当代艺术品,更像是20世纪早期的风格。在那个时代, 非官方艺术家就是非法艺术家。在喀布尔, 我曾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之感, 很多记忆都重叠了。这里的一些宫殿让我想起了卡塞尔的某些地方。这让我开始思考我能为创建公民社会有何贡献。我还一反“艺术是在冲突发生后产生的”这一传统艺术观念, 开始思考我能在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战争制造了事实, 我同样也制造了事实。
就我在前面谈到的四个条件方面,喀布尔可谓是万事俱备。在喀布尔, 你正处在舞台中心,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一瞬间就能传遍全球。同时你也是处于隐退的状态下的,因为波提的旅馆地处静谧偏僻之隅, 而且在这里你也能感到一种与外界的纷杂构成鲜明对比的内心的宁静。你也处于围困之中, 同时却又充满希望。所以我们决定在这里与来自CAA美术系的学生们共同组织一系列研讨会与艺术工坊活动。CAA美术系规模不大,却拥有众多艺术家与学习艺术与艺术史的学生。这些艺术家并不是你我所熟知的艺术系统里的艺术家, 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项目非常感兴趣。这是草根层面的一次大合作。他们不是来自文献展的内部。在喀布尔将有一个卡塞尔文献展的单元,这让人倍感振奋。
Q:你的29名人(agents)的作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策划平行艺术活动、调研活动以及研讨会, 你如何确保这些活动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得到体现呢? 对于此次文献展展品的设置,你又是如何构想的呢?
A:总共大约有115位艺术家参加此次文献展, 实际上参展者并不仅仅只有艺术家,这一点很有趣。虽说此次文献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构建更宽泛的氛围,但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其打造成一个供艺术家展出作品的平台。所以,虽然绝大部分参展者为艺术家,但同时也会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参展者, 比如安东·塞林格(Anton Zellinger), 他会将他的整个量子物理实验室从维也纳搬过来。还有一个项目将在一家中国餐馆里进行。在这个项目中,将始终有一个作家坐在那里,如安立奎·维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此外还会有更多的内容。这些项目都是为了避免让文献展仅仅成为一个艺术展 ,而是力图将其打造成一个感官与思想的联盟。
我对跨学科合作不感兴趣。我从不要求一位艺术家与一位科学家合作, 我觉得那很没意思。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是将马克·隆巴蒂(Mark Lombardi)置于一个量子物理实验之侧时我们所能获得的艺术体验。这不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展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里科学研究正在发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世界性的联合”。我不想把一个人从他的领域里抽离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今时代的问题之一。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带来一些伟大的作品,比如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就做了一个叫“拒绝时间”的作品。阿洛拉与卡扎迪勒(Allora & Calzadilla)则就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创作了一件相当精彩的作品—— 一种能模仿鸟叫的笛子。我与艺术家交流, 他们则向我做出各种提议,阿洛拉与卡扎迪勒的项目就是这么诞生的。这一项目实际上是关于我的两个问题的。一个是多物种共同进化,共享世界, 并通过共享再造世界;另一个则是古老知识与当代知识融合。这两个问题,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到了。
所以我与艺术家谈到的是一系列的兴趣,并不是单单的某一个兴趣。我经常谈到的是多物种进化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危机四伏的情境之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再造世界。对此不少人是赞同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传统的思考方式, 仅仅只考量人类。这已是很陈旧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整合各种类型世界生产者的大联盟, 同时也需要非人类的参与者,植物与其它动物,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一些人看了我在文献展之前出版的“100个思想笔记本”, 指出尽管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点,但也并不存在冲突。就好像有一个不冲突的原则存在。此次文献展有不少项目是参与性的, 但同时也会有很多可以被称作雕塑或装置的艺术品展出。你将发现该展就是一团彻头彻尾的混乱,因为没有一个统领性的主题, 它更像是一个放任思想恣肆生长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