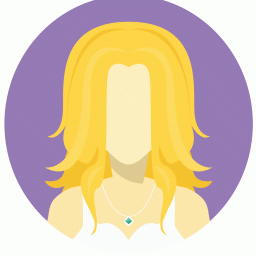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
时间:2022-07-28 03:08:26

摘要:于会见的艺术就是“后现代崇高”哲学①:它以批判的姿态介入“现代性”,因而是“后现代”的,而“后现代”如果依据后结构主义的理解,不是杰姆逊美国版的大众文化、波普艺术,而是不可表述的“大地”和人的生命存在,是康德和利奥塔意义上的“崇高”。因其所处理的是现代性及其后果这样一般性的“世界史”问题,且不再局促于什么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差异”,于会见的艺术获得了“世界主义”的视野和胸怀。
关键词:于会见;艺术创作;绘画作品;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学;审美;后现代崇高;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于会见绘画给我们传递的一个最强劲的信息是其与“现代性”的纠结,这纠结的结果究竟是画家成为“现代主义”的代言人抑或反现代主义的英雄而汇入“后现代主义”阵营,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否问题。或许可以说,正是超越了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于会见才成为一个不“简单”的画家,而“不简单”则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真髓。我们可以把于会见读作哲学家,首先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哲学家:让我们就在此处开始吧!
一、现代性就是“出现”
“现代性”作为一个颇有年代而又持续不断的思想学术话题存在着越描越厚、越说越玄的不清晰的趋向,然而在视觉上极为清晰的是,现代性就是“改天换地”,在地表上一系列堪称地标的“杰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天际线。纽约的摩天大楼,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东京的银座商厦,宜昌的三峡大坝,正蜿蜒前行于中国大地的高速铁路大桥,等等。在这方面,于会见提供给我们的是工业时期的烟囱,横跨沟沟壑壑的桥梁,桥梁上奔驰着的列车,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给大地开膛破肚的水利工程,等等。要而言之,让于会见陶醉的是现代性的物质符号或借用波德利亚的术语——“物体符号”。确乎如此,现代性就是“形象”工程,具有外在性与可见性。我们都熟悉《共产党宣言》在言及现代化之摧枯拉朽的破坏力时的一个描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也不陌生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界定,“过渡、短暂、偶然”③,但我们似乎不太在意的另一方面则是,一切烟云飘渺的东西都凝固了,都要经由物质化方才取得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转化为可见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其核心意思是“物化”(Verdinglichung)、“具体化”和“看得见”。
于会见将现代性揭示为“出现”,出现于大地上的种种人工制品。面对自然,不是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于会见赋予现代性事物的“出现”以一种奔突力,一种陡然,一种“突然”,一种波德利亚所谓的“外爆”。于会见的画作充满了运动感,力量感,甚至是不由分说的感,这是现代性能量的喷发,是现代性的狼“奔”豕“突”。了解于此,我们就知道在他的画作中何以有那么多的仿佛被刀劈斧砍的大地,那么多直刺苍穹的电杆、佛塔、山峰,尤其是那反复出现的似乎一怒冲天的鸟群,而向下则是令人目眩的沟壑、深渊。
二、“出现”就是“崇高”
必须辨别清楚,“出现”(presentation)不是“再现”(representation)。“出现”归属于事物本身,是事物的自行呈现;而“再现”则是现代性主体将事物作为客体的认识活动或表象活动。如果依据康德,“再现”不过就是主体性的自体循环,过去曾经美其名曰“人的自我确证”,而这确切地说则是黑格尔的理论。康德没有像后来的黑格尔陷入理智主义的泥潭不可自拔,因为他还葆有一个“自在之物”。受黑格尔影响,青年马克思将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主体哲学命题,康德以来西方美学以此为正宗,为主流,但它无法回答一个最基本的美学问题:古希腊艺术何以具有永久的魅力?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就是人的理性,是说得清道得明的,因而是“知识”。难道艺术欣赏者需要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对于某对象的知识吗?诚然,与对象的心心相印,高山流水的境界,乃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但更是一种对话活动,而能够刺激对话进行下去的则是参与对话者自身的不可对话性的生命存在,它是理性和话语的生命活水。
结构主义的对话,如托多罗夫、克里斯泰瓦所阐释的巴赫金的“对话”,只是一种“互文性”,是文本间在文本层面上的理性主义对话。而深邃的对话主义尽管不会抛弃这一点,但更愿意补充以本体论的意义。在本体对话主义者看来,优美与崇高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在实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优美以其对主体的逢迎而使我们忘记了对象的真实存在,对象呈现于主体的乃是可以言语者也,是表象,是浅层;由此而言,崇高就非常可贵了,它对主体想象力的摧折,唤醒了主体对自身之局限于话语层面的认识,从而了解到对象还有其不属于“我”的独立的神秘与存在。
于会见深谙于此,他说“大地是一层皮”,而皮下的则是“历史”。他向我们暗示,历史并不只是“叙述”,不只是可付诸叙述的“经历”(Erfahrung),因而“故事”,它更是生命的体验(Erlebnis),更是日常生活的“惯习”(habitus),换言之,是哲学解释学的“传统”:我们无法随意躲避“传统”,选择“传统”,因为“传统”是我们生命体的先在构成,是“基因”。
于会见描画大地上人类的所作所为,这是他所谓的“大地是一层皮”,但他企图带领我们穿透这层表皮而深入“历史”,深入对于地表上的人类而言知其或有而不得其详的未知领域,那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于是于会见的现代性“出现”就是康德“自在之物”的“显现”(Erscheinung)。面对这样的“出现”或“显现”,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整合,因而感到震惊、恐怖、晕眩,找不到方位。坚持于此的于会见将注定与“优美”无缘,他看透了美的幻象,美对他不过就是幻象,是话语性的皮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穿过话语的表象,于会见看到了“无名”,看到了“玄之又玄”的真理。
三、“崇高”本质上属于“后现代”
根据康德,“崇高”来自于“理性的理念”(dieIdeenderVernunft),更准确地说,是“理性”接通了“理念”,这个“理念”相当于老子的“道”,是世界的“绝对整体性”和“无限性”,无形式、无尺度,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它不接受任何对它的“再现”和“庸常”的领会。对崇高(以及自由)的研究使康德不再把“理性”局限为“知性”,那是理性的第一重含义,而是将“理性”还作为对“知性”的突破:“理性”同时是非理性的。然而,理性也好,非理性也好,在康德统统内在于人的主体性。康德是科学理性的康德,也是人文理性的康德——我们知道,人文理性与自由相关,与心中的道德相关。质言之,德性是人之整体不可缺少的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