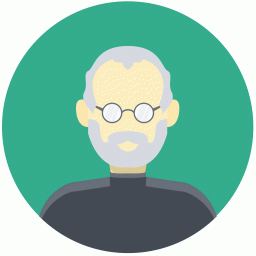那年我们还小
时间:2022-07-08 10:53:45
逃学
小河水一浪一浪地翻腾着向下流。
我们泥鳅般赤条条地躺在河边的沙滩上,用沙子把自个埋起来,只留个脑袋出来。
来顺扭过头对铁蛋说:“哥,你不去上课啦?爹知道了,打你的屁股呢。”
“爹不知道,再说,爹抓不住我,谁也抓不住我。”
“那,老师呢?”
“老师也抓不住。”
“我不信,三进就让老师抓住了。”
“三进是三进,我是我。”铁蛋自豪地说。
得生说:“来顺,你娘的胆小鬼,以后别跟咱们了。”
“偏跟,我跟我哥,又不跟你。”
“你哥也不准跟,谁也不准跟。你一人在家玩吧。”
“就跟。”
“你再说?”
“就跟。”
“好,你个跟屁虫,我给你撒个屁,你跟吧。”得生站起来,准备撒屁。
“我告诉我爹去。”来顺撅着嘴,泪汪汪地看着铁蛋。希望他哥铁蛋来帮他。
铁蛋果然跑过来,抱住得生要摔跤。得生摆脱铁蛋的手,沿着河岸跑,铁蛋紧追不放。得生一边跑,一边说:“我投降,我投降!”
铁蛋还是追,得生就扑通跳到河里,铁蛋也跳到河里,两人在河里嬉闹。闹够了,两人从河里湿漉漉的出来,又爬在沙滩上用沙子覆盖了身子。
来顺说:“我要回去了,要不,我爹知道了打我。”
铁蛋说:“回去弄啥?爹准备了一个鞭竿,打折你的腿呢!”
来顺是铁蛋的弟弟,比我们小两岁。那时,我们刚上一年级,他就跟到一年级的教室门前,爬在窗台上,垂着长长的鼻涕往里看。我们逃了学,他转身跟紧我们,寸步不离。他知道我们的全部秘密,我们拿他没办法。我们只能既吓唬他,又哄着他。
我说:“来顺,青蛙爱玩吗?”
“爱玩,要呱――呱――叫的。”
“好,那咱们回头给你捉一只。要是你爹问咱们,你就说咱们上学去了,要是老师问,你就说咱们帮大人干活去了,记住没?”
“记住了。”
“那好,你说一遍。咱们就去给你捉青蛙。”
来顺鹦鹉学舌地说了一遍。
我们轰一下笑了,抖落身上的沙子,扑通扑通的跳到河里,像蝌蚪一样在水里挤成一堆。来来回回地寻找青蛙。
“来顺,来,过来,给你一只青蛙。”
铁蛋从河里摸到一只青蛙,双手捧着,屁颠屁颠地从河水中蹦出来,送到来顺面前。
青蛙瞪着眼无声地抗议,样子像是在骂铁蛋,铁蛋不管,将青蛙扔在来顺面前的沙滩上。
来顺伸出食指在青蛙身上点一下,青蛙就啪地跳一跳,来顺吓得往后退一退,最后来顺扑哧一下笑了,鼻涕吹成两个大大的泡泡。
铁蛋返身跳到河水里,冲着来顺喊:“来顺,看,哥给你玩个鸭子凫水。”铁蛋扎个猛子,身子和头潜在水里,撅出屁股在水面上。
我和得生水性差一点,就在河边蹬狗刨。
正玩得起劲,只听来顺在岸上叫:“不好了,老师来啦,快出来。”
我们抬头一瞧,来顺藏了起来,白玉老师立在河岸上。
白玉老师指着我们说:“出来,都给我乖乖地滚出来。”
我们傻了眼了,泅在水里哪敢出来,再说,都没穿衣服呢,让女老师看了,害臊不害臊。
白玉老师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脸一红,背过身去命令说:“穿上衣服,回学校。看我咋收拾你们。”
我们蹑手蹑脚的从河里出来,像丧家犬似的找衣服穿,慌乱中,我把裤衩当衫子套在了头上,得生把铁蛋的裤子穿在了身上,铁蛋急地骂:“得生,你娘腿,你穿了我的裤子。”
好不容易穿了衣服,背了书包,我们就像吓破了胆的兔子,撒开脚丫就跑,白玉老师一边追,一边喊:“站住,都给我站住。”
我们不敢停下来,一顿饭工夫,跑得没个影了。
充饥
正是晌午,太阳毒辣辣地照在头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我们不敢回家去吃饭,更不敢回学校,我们躲在一片槐树林里,来回游荡。
来顺哭叫着说:“我说回去,你们就是不回,呜呜呜。”
得生说:“叫,叫,就知道驴叫,再叫,把你的嘴给缝上。”
来顺哭叫得更凶了。铁蛋推一把得生说:“走开,别欺负我弟。”
铁蛋转过头对来顺说:“来顺,不哭,哥给你叠个飞机。”
铁蛋翻开书包,想要找张纸,翻来翻去,没有找着,他就嗤啦撕下书皮,叠了个飞机,塞到来顺手里。来顺接了纸飞机,止住了哭叫。
不知谁家的饭香飘到我们的鼻子里,铁蛋狗一样嗅了嗅,说:“嗯,辣椒炒豆腐,真香。”说着连打了三个喷嚏。我和得生跟着也连打了几个喷嚏。我们嘴里的馋虫被那香味勾引出来了,肚子像公鸡打鸣似的叫。
来顺扔了纸飞机对铁蛋说:“哥,我要吃饭。”
“来顺,听话!玩飞机,日――”铁蛋捡起纸飞机,抛到空中,学着飞机的叫声说,“飞机接咱们来顺来了。”
来顺不看飞机,他摇着头,甩着胳膊说:“不要,不要,我要吃饭。”说着又哭上了。
铁蛋没有法子,用脚踢着槐树说:“弄点吃的吧,我弟弟饿坏了。”
我们就到附近的庄稼地里挖了几个山药蛋,用衣襟兜了,跑到一个树窝窝里,想用火烤了吃,一摸口袋,才知道没带火柴。
我们将山药蛋丢在地上,愁眉苦脸地相互埋怨。
几头鹰在天空盘旋,我们对着鹰喊:“鹰,鹰,叼盒火柴来。”鹰听不懂我们的话,它一圈又一圈地飞着。
忽然,一头鹰俯冲到槐树林里,叼起一只麻雀,拍打着翅膀飞走了。这个动作启发了得生,他站起来说:“有吃的啦,有吃的啦。”说着就跑到一棵槐树下,飞快地脱了鞋,噌噌噌的往槐树上爬。
得生爬到树丫,揪下一朵槐花往嘴里塞。我们这才发现槐树吐出米粒大的白花,还没完全开放。
得生鼓着腮帮子说:“好吃,哼,香死人。”得生扔下几朵槐花给我们,我们尝了尝,香,确实香,芳香。
我和铁蛋猴一般先后爬到树上,放开肚皮嚼,牛一样嚼。
来顺胆小,在树下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给他扔槐花。
吃了一气,肚子胀得鼓溜溜的,才从树上笨笨地下来。
得生说他口有点渴,要到河边去喝水,我们就来到河边喝了一通水,这才满意地打着嗝,往家里走,路上,得生撅起屁股吱儿撒了个屁,铁蛋也吱儿撒了个屁,我憋足了劲也想撒一个,结果是个哑屁――没有声音。
得生和铁蛋就嘿嘿地笑我。
我有点生肚子的气,暗自抱怨它没给我制造个响屁,觉得脸上很没面子。
走着走着,得生捂住肚子往麦地里跑,铁蛋跟着往麦地里跑。
我正在纳闷,感觉肚子一阵阵的疼,赶忙也往麦地里跑,我们都拉稀了,蹲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叫。
那晚上我跑了三趟茅厕,得生上了五趟茅厕,铁蛋上了四趟茅厕,惟有来顺喝的水少,他竟然没上茅厕。
受罚
第二天,我们一个个脸色枯黄,蔫蔫地去上学。白玉老师她可不管我们昨晚上几趟茅厕,她拎起我们的耳朵,像拎猪崽似的,一个个把我们拎到教室外。
然后,她掐着我们的胳膊问:“说,为啥逃学?”
我们你推推我,我推推你,就是不说。我们已发过誓的,就是打死,也不能说的。
白玉老师说:“好啊!你们这些碎蛋蛋,嘴还挺紧的。看我能不能撬开你的嘴。”白玉老师说着,把我们关在她的办公室里。
晌午的时候,她锁了门,哼着小曲吃饭去了。
我们饿得不行,就在她的办公室找吃的,找了半天在她的床底下翻出一篮苹果,可谁也不敢第一个动口,还是铁蛋胆子大些,他率先咬了一口,我和得生也顾不得什么了,抓起来就咬,狠咬。
一袋烟工夫,一篮苹果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吃完苹果,尿憋得慌,又不敢往地上撒,急得团团转,我们盼白玉老师快点回来,可她就是不回来,她一点也不着急。
得生蹲在地上,看样子是憋不住了,铁蛋眼珠一转,笑一笑,对得生说:“别撒在地上,找个盆盛着。”
“好,快给我找个盆。哎哟,憋不住了。”
“给你个盆,你有胆撒吗?”
“咋没有,再憋,就憋破肚子了。”
铁蛋没找到盆,他在桌上提来老师的暖瓶给得生,得生拔开暖瓶塞子,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冒,得生就骂铁蛋:“你娘的铁蛋,那是老师的暖瓶。”
“说你没胆,你还嘴犟。”
“你娘的,你有胆,你咋不来撒。”
“来就来,去,蹲一边去。”
铁蛋果然掏出小往暖壶里撒尿了。铁蛋撒完尿牛气哄哄地说:“这叫童子尿,补人,大补,我爹说的。我娘生我家来顺时,我爹就让我撒一碗尿,端给我娘喝。”
“骗人!”
“谁骗人?不信问我爹去。”
得生听铁蛋这么说,也就有了胆了。“那我也给老师补一补,要挨揍,咱们一起挨。”
铁蛋和得生撒完尿,鬼鬼地看着我,我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就提着裤子,对着暖壶口也撒了一泡尿。撒完尿,心里慌得厉害,怕老师发现了揍我们。
左等右等,白玉老师总算回来了,她开口就问:“说,干啥坏事了。”我们的头嗡一下大了。她咋知道呢?莫非她看见我们往她的暖壶撒尿了?
幸亏铁蛋反应快,他厚着脸皮接上老师的话说:“嘿嘿,老师,你是问昨天的事吧?”
“甭管昨天、今天,都给我说。”
铁蛋就把昨天我们逃跑后摘槐花吃拉稀的事说了一遍。白玉老师捂住鼻子,摆着手说:“脏死人了,滚,都给我滚。”
我们一溜烟跑出来。回家吃饭去了。
报仇
说实话,我们挺喜欢白玉老师的,那喜欢是埋在心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白玉老师从不用鞭竿敲我们的脑壳。她对付我们的办法是用指甲掐,她不掐别处,就掐我们的胳膊,掐过来,掐过去,我们咧着嘴叫,她才慢腾腾地问这问那。过后撸起袖子一看,那掐过的地方,如同是蚊子咬过留下的包,红通通的,却从来没有掐破过。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她就这样把我们给掐服了。
我们喜欢白玉老师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年轻漂亮,白玉老师的脸,粉嘟嘟的,真耐看呀,比城里人的脸还耐看。她的衣服也是全村最鲜亮的,那种白底碎花的汗衫,风一吹,轻轻地摆动,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扇一扇地吸引我们的眼球。
可是她不该和丁子那个混蛋老师眉来眼去,丁子算什么东西,他教我们体育,就让我们在地上爬,衣服都磨破了,还让我们爬。
丁子是部队复员的大兵,教给我们的都是匍匐前进,我们不喜欢匍匐前进,我们爱玩篮球,他就是不让我们玩。
不让玩就不玩呗,我们也不稀罕,可他居然把我哥捆起来了。
我哥是个好学生,不爱体育课上像甲虫那样爬来爬去,他在教室的黑板前默写生字。丁子老师瞧见了,找来女学生跳绳用的皮筋,捆住我哥的手,把我哥拴在黑板前的一颗铁钉上。
这事是来顺悄悄告诉我的,我听完肺就气炸了,跑回家向我爹作了汇报,我极力鼓动我爹去找丁子那个混蛋算账。
我爹正蹲在我家的碌碡上吸烟,听了我的汇报说:“三字经上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师替我教育娃子,那还有啥说的,我得感激人家呢。”
这是啥话?我一直认为我爹是个识文断字的爹,是个英雄的爹,我爹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把我爹看扁了。
我爹不但不去找丁子算账,他还教训了我哥一顿,我哥勾着头,眼里含着两泡泪,样子像个绵羊。
我看着我哥的那个熊样,就转而恨上我哥了,丁子敢把你吊起来,你咋不敢咬他呢?那时侯我认定人的嘴除了说话吃饭之外,还应该是咬人的。我家的大黑狗,见人就咬,一咬一个准,人见人怕,我哥不敢咬人,我就认为我哥是连狗不如的,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但是我心里的气老是出不来,既然我爹不管我哥的事,那我出马管管。我先是在丁子的体育课上捣蛋,他命令我们匍匐前进,我偏就地打滚,他让我们立正,我偏稍息。我早就想好了,他要是打我,我就咬他。丁子很狡猾,他竟然装作没看见。
于是我只好想别的办法,我偷偷地在学校的墙上用粉笔写字骂丁子。“丁子是头毛虫!”
我本想写“丁子是头毛驴”来着,想了半天,驴这个字不会写,也许语文老师没教我这个字的写法,也许老师教了,我记不起来了。
我猜测丁子见了这些字会气个半死,那我们就扯平了,谁也不欠谁什么了。遗憾的是丁子他没生气,他骑着自行车嗖地过去了。
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不能善罢甘休,我决不能就这样饶了他,他欺负我哥不说,他还勾引我们的白玉老师呢?那就更不能饶他。
我拉了死党铁蛋、得生,逃了学来到丁子家的玉米地里捉麻雀。丁子家的玉米才半尺高,里面有无数的麻雀叽叽喳喳地找食吃,我们瞅准刚出窝的小麻雀追,小麻雀翅膀嫩,飞不高的。
想不到的是,丁子家玉米地里的麻雀和丁子一样狡猾,老是往玉米丛里钻。我们沿着田垄追了好几个来回,没捉到一只麻雀。我们就用脚踩,麻雀没踩到,踩倒了不少玉米。
我觉得我不是在捉麻雀,我感觉我在捉丁子那个混蛋,我非要捉到一个不可,就脱了衣服扑麻雀。我双手兜起衣服,看准了小麻雀猛的扑上去,想用衣服压住麻雀,结果,麻雀没压住,压倒了无数的玉米。
我正扑得起劲,冷不丁,一只大脚踏在我的后背上,我还以为是丁子呢,回头一看,吓了一大跳,不是丁子,是我爹,我刚要说:“爹,我是为我哥报仇哪。”我爹蒲扇大的巴掌已结结实实地落在我屁股上,我疼得嗷嗷叫,脚在地上蹬出一个坑,我爹还不住手。
我爹打够了我,就把我夹在胳膊弯里往家走。我爹的力气真是大,他夹着我就跟夹个萝卜没啥两样。回到家,我爹将我扔在我家的院子里,我骨碌碌打了两个滚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爹又去找笤帚疙瘩,他还要打我,好在我娘从厨房出来,拉开了我爹,要不,我是活不到今天的。我爹气冲冲地吼:“看老子打不死你!拳头大点东西,你把我的肠子气出来了。‘天地君师亲’,排起来老师比你爹还要大呀,你在老师家的地里野,你不是在扇你爹的脸吗?我叫你野。”
我爹想扑过来揍我,我娘拽住了我爹,冲我嚷:“挨刀贼,你看看你闯的祸。还不快去上学,小心打断你的腿!”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上学去了。
打狗
是谁给我爹告密了呢?是白玉老师吗?是丁子那个混蛋吗?还是其他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盯着每个人的脸看,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些破绽,我发现有几个女生对着我嗤嗤地笑。我就怀疑是她们出卖了我。
放学后,我约上铁蛋和得生,尾随着那几个女生。她们并不急着回家。她们在校园里跳皮筋。
她们一边跳,一边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我向铁蛋和得生使个眼色,佯装着捡石子,慢慢地踱过去。她们没有发现,她们颤动着羊角辫,跳得正欢。我们发一声喊,冲上去扯女生们的皮筋。
“坏蛋,坏蛋!”
“你娘的坏蛋!”
“抓住坏蛋,交给老师。”
女生们尖着嗓子惊叫。
我们嘿嘿笑着,得胜地跑了。
跑到园墙边,噌噌噌地爬上去,翻身骑在矮墙上,十分得意,仿佛骑在马背上,冲女生们喊:“在这儿哪,来抓呀!驾,驾,看咱们骑快马。”
“驾驾。”
“得儿,得儿,驾。”
我们扬着手拍着墙头不停地喊,感觉墙头真成了千里马,驮着我们腾云驾雾。
一条瘦狗,翘起腿对着墙角撒尿,被我们的吆喝声一吓,回头望了望,夹着尾巴跑了,我们更得意了。
“哎哟――哎哟――狗,狗。”女生们又一次惊叫。
“哎哟――娘呀。”一个女生哭了。
我们回头一看,那条瘦狗咬住一个女生的裤腿。
“嘻嘻,好玩好玩。”得生说。
“啊啊,是条疯狗。”我说。
“快,去打疯狗。”铁蛋说。
我们从矮墙上跳下来,手里捏了块砖头去打瘦狗。
瘦狗龇着牙,呼哧呼哧地威胁我们。
铁蛋说:“打,快打。”
三块砖头划出三条弧线,飞了过去,两块砖头落空了,一块砸在狗腿上。瘦狗呜儿呜儿叫着逃跑了。
女生们早吓掉了魂儿,呆呆地立在那里。
我们扮了个鬼脸,去追瘦狗。
认错
早上起来,我们去上学,白玉老师点了我们的名。我们站起来,勾着头,等待白玉老师来掐,意外的是,白玉老师竟然没有掐我们,她不住地表扬我们,她说:“别看咱们班这三个蛋儿,平时挺坏,关键时候主意正着呢。以前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
我们的脸腾得红成一只柿子,心里却痒酥酥的舒服。
白玉老师走下来,摸着我们的头说:“想不到,你们还有点出息。”
我们乐坏了,从来没有一位老师表扬过我们呀,谁能不乐?
回家后,我和铁蛋、得生商量了好一阵,我们决定向白玉老师承认我们在她的暖瓶里撒尿的事。当我们说到一半的时候,白玉老师咯咯咯的笑了。
白玉老师说:“我早就料到了,你们这三个蛋儿呀,说坏挺坏,说老实还挺老实的嘛。”
我们羞红了小脸,转身跑了。
从此,我、铁蛋、得生再没逃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