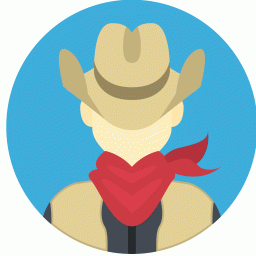杨慈湖之“毋意”道德修养论鱼议
时间:2022-07-02 01:57:47

〔论文关键词〕杨慈湖 道德修养 意 毋意
〔论文摘要〕杨慈湖反对从主观之外寻找道德恶产生的根源,认为“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由“毋意”而展开的“毋必”、“毋固”、“毋我”,他在认同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成人成圣的理论前提下,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道德境界说,认为“意虑不作,澄然虚明”的“永”之境乃是一切道德践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杨慈湖伦理思想在陆王心学伦理思想史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杨慈湖(1141一1226),名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乃陆象山的高足。杨慈湖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特别是在心学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是通过深化陆学启发王学而体现出来的。其以“毋意”为核心的道德修养论,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一、“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的修养论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只有合理地回答了人性善恶问题,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和必须性才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自先秦以来,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韩愈的性情三品说到宋明理学家们通过区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而做出的解释等,都从人性善恶的角度回答了道德修养何以可能,现实中何以有恶,道德修养何以必须的问题。但杨慈湖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裂之”,而非“一之”,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人为恶的必然性。他指出,如果荀子的性恶、韩愈的下品性情、朱熹的气质之性本然具有的话,不仅“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也为现实中有些人为恶不善的不道德行为找到了先天的借口。因此,杨慈湖一方面相信“人心自明,人心自灵…夫人皆有至灵至明广大圣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他说:“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昭明如鉴,不假致察,美恶自明,洪纤自辨。世间未尝有美恶亦未尝无美恶,未尝有洪纤而亦未尝无洪纤;吾心未尝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尝无是非利害。”这就是说,人心本是虚明无体的,善恶之间亦没有绝对的对立可言。另一方面,杨慈湖提出与“心”相一致的“意”来解释恶的产生,他说: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闭固碍塞,始丧其明,始丧其灵。……如太虚未始不清明,有云气焉,故蔽之。去其云气,则清明矣。夫清明之气,人之所自有,不求而获,不取而得,故《中庸》日:“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固有之也”。
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杨慈湖把人先天固有的心性,比做如“太虚”、“明镜”般清明,认为凡对于此清明之性有所增减、损益的即是“意”。“意”好比“云气”,遮蔽了“太虚”,使人丧失本性,进而产生道德上的“恶”。他是这样描述“意”的:
何谓意?微起焉,皆谓之意,微止焉,皆谓之意。意之为状,不可胜穷,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进有退,有虚有实,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达,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有体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动有静,有今有古,若此之类,虽穷日之力,穷年之力,纵说横说,广说备说,不可得而尽。对于寂然不动的“心”而言,一切“动”、“起”都是对这种全然纯善的“心”的偏离,故都是“意”。这样,“意”不仅仅是指私欲,即从个体之“小我”出发的意念,还应包括一切不合乎道德本能的意识活动或意向状态。它的形态是无法用言语概括的,凡是一切有形象、有差别、有是非的具体知识,一切与人的感觉、思维活动相关的观念,一切有主、客分别的认识内容,都是“意”,都会妨碍、阻隔人对本体之善心的直觉。因此,杨慈湖认为烦琐的言辞辨说,也是“意”:“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绝学者之意,而犹日:‘予欲无言’,则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故曰毋意。圣人尚不欲言,恐学者又起无意之意也。虽意求心,未脱乎意。……愈辩愈支,愈说愈离,不说犹离,况于费辞。”澄明纯善的“本心”没有必要用言辞来表述,亦不能用言辞来描述,虚伪的言辞只会掩盖人的真心,使人不尚实德,言行不一。
至于“心”与“意”的关系,杨慈湖的主张是“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故“合”与“意”未始不一,不可分作两截,“心”不在“意”外,“离意求心,未脱乎意”,“心”与“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意”乃“心”之“意”,“意”之于“心”,如波之于水,“心”之动即为“意”,“意”之不起即是“心”,看不到这一点,执著于“意”,便是与心为二、支而不直、阻而不通。
杨慈湖反对从“意”之外寻找心昏恶生的原因,他说:“《乐记》亦非知道者作,其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此语固然庸众者不知其非,而知道者不肯为是。盖知道则信百姓日用斯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无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乱也。故曰‘物使之然’则全以为非裂物我,析动静,害道多矣。”这样,他就排除了主观之外产生道德恶的根源。对于这一观点的提出,杨慈湖颇为自豪,他说:“杨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日用平常实直之心无非大道,此固不可得而书。
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
既然恶的产生在于起意,那么通过“毋意”的修养方法便可维护本心之善,使“心”恢复到寂然不动无尘无垢的本善状态。“毋意”之说,最早见于《论语·子罕》①,朱熹在《四书集注》里也说:“绝,无之尽者。毋,《史记》作无,是也。”杨慈湖继承和发挥了这些思想,“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则此心明矣!”并认为孔子所言“毋”乃禁止意,“绝”乃止绝意:“毋者,止绝之辞。
如何才能做到“毋意”呢?杨慈湖认为应该“匪学匪索、匪粗匪精”、“不假致察”,使纯善之“心”不被支离,不受阻隔。这一过程不涉及任何心理变化和知识的积累;由于他认为烦琐的言辞辩说也是意,因此这一过程也不借助任何如言辞一类的中介物,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成分。只要顺着人心所固有的道德本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心”、“意”自然契合。只要纯善之,’,自”自然静定契合,为恶之“意”即不起。这样,本体与方法在此得到了统一,心学的本体论和修养论在内在理路上得以一以贯之。
杨慈湖之“毋意”意味着反对任何活动吗?非也。他虽然认为人们在思索问题、解决事情、决断外物时,会因物而动“心”生“意”,由“意”而违反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外物隔绝,而是以自然静定之“心”规范万事万物,即物而不滞于物。这就是他在“鉴中象”之喻中所谓的:万物虽然纷杂万千,但“心”如明镜本身不动,故‘旧用酬应,未能无碍”。这种自然静定的“不起意”之“心”,实际上就是他在居丧时所体验到的“哀坳时乃亦寂然不动”之“心”;也是他所谓的“意虑不作,澄然清明,如日如月,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之“心”,以及在面奏宁宗皇帝时的“不起意”之“心”: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宁宗日:“然。”问:“日用如何?”宁宗曰:“止学定耳。”先生谓:“定无用学,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是非贤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觉如太虚乎?”宁宗日:“是如此。”问:“贤否是非历历照明否?”宁宗曰:“肤已照破。”
(见《宋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因此,杨慈湖一再强调所谓的“不起意”,即是,’,合”自然静定,顺应伦理道德规范自然地而思而为,是本心自然流行所形成的对是非曲直的直接明觉,而非绝对的不思不为。他说:
不起意,非谓都不理事;凡做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则不可。[7]孔子莞尔而笑,喜也,非动乎意也;日:“野哉,由也。”怒也,非动乎意也;哭颜渊至于勃,哀也,非动乎意也。阁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非意也。孔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非意也。
在杨慈湖看来,人如果不执著于“意”,人之“本心”就会如人之生理本能一样,自然地生发出来。这样,一切行为也都是出于道德本能的合乎“心”的行为。因此,作为圣人的周公、孔子的“仰而思之”、“临事而惧”、“莞尔而笑”、“哭至于坳”都不是“意”,而是顺乎伦理规范的发乎本能的行为,是合乎道德“本心”的。
杨慈湖指出,由“意”而伴生的“必”、“固”、“我”,同样会使“心”昏蔽而致恶,因此也必须“毋”。(杨慈湖在说“毋意”时,一般是从总体的意义上指“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于“必”,他说:“何谓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小‘必”也是一种“意”,是人执著于一己之私,坚守一端、刚惶自用、固执己见所致。事实上,“大道无方,奚可指定!以为道在此则不在彼乎?以为道在彼则不在此乎?必信必果,无乃不可,断断必必,自离自失。”而“大道”无形无象,既无所不由,无所不在,又莫不共由,莫不共在,哪有一定的方向路径。人们固执地以为“道”在此,故一定如此去做,或“道”在彼,故一定如彼去做,都是没有体悟到“道”“天下莫不共由”的特性,都不合乎“本心”自然静定而又自然发用的特性,都是悖道、起“必”。因此,要“断”“必”。“固”也是一种“意”,“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穷,固守而不化,其道必下。”若拘泥于某种规则制度而不知损益变化,穷顽不化,不知变通,必然会使“道”僵化而走向穷途。圣人却不同:“孔子尝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川,他深悟“无可无不可”的内蕴,明白知与无知的变化无驻。因此能以自然静定之“心”,即物而不滞于物,以一种以不偏不倚、至中至正之道应世接物。相反,如固执己“意”,死守规则信条,必会使“心”蒙蔽而致恶。
什么是“我”呢?“我亦意之我,意生固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小‘我”就是个体之人执著于一己之私而产生的私意。人们总是以自我的立场去认知和生活,所以直接感受到的是我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或失去了什么,一切都以个体“小我”的价值判断、立场观点为依准:“自幼而乳,日我乳;长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读书我读书,仕宦我仕宦,名声我名声,行艺我行艺。”杨慈湖明确指出,若执著于自我的血气形骸、主观意识,就会把自己限于一个狭小的天地,不能变通超脱,从而在心中树起一个“小我”,追求无穷私利,而背离物我一体、寂然纯然的境界。他说:盖有学者,以为意必固我咸无,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则何以能范围天地发育万物?非圣人独能范围而学者不能也。圣人独得我心同然尔,圣人先觉,学者后觉尔。一日觉之,此心无体,清明无际,本与天地同范围,无内外,发育无疆界。
这种对“小我”的破除,就是他所说的“道心无我,中虚无体,自然于物,无柞自然”(《杨氏易传》卷十五),而所谓“无我”即为无“小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慈湖之心学并不是唯我论①,唯我论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个体“小我”即可决定宇宙间发生的一切。而慈湖不重视宇宙间的源流发生关系问题,并在根本上反对固执己见,存“小我”以致坐井观天。慈湖通过对先师陆象山教诲的追忆,指出“毋意”之法,实乃先师对自孔子以来的儒家一脉相传的“正救”之法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只有以“毋意”之法“随处正救”,才能防止“后学意态滋蔓,荆棘滋植”,才能使万世人道之门畅通无阻,使学者自明己心、自信己心,体悟“本心”之妙。黄宗羲在《慈湖学案》中也说:“象山说颜子克己之学,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盖欲于意念所起处将来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标宗,是师门之的传也。”但是,象山之修养论中虽亦有“毋意”之内涵,但真正以“意”来解释恶之起,并提出“毋意”修养论的确是慈湖。不仅于此,在象山的修养论中,在以“欲”来解释“恶”之产生的原因的同时,又认为“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习有所移”,(见《陆象山集》卷十九《武陵县学记》)亦是导致“本心”昏恶的原因,并提出了“剥落”的方法。这就没有根据“善体自现”的思路去解决现世何以有恶以及如何去恶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虽然解决了道德修养可能性和必须性的问题,但却没有在内在理路上将其贯通起来,因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造成了本体与方法的不一致。杨慈湖与陆象山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提出了与“心”相一致的“意”来解释道德恶的产生,而且根据“善体自现”的思路,以“毋意”的道德修养论,将本体与方法贯通起来,达到本体与方法的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慈湖对象山之伦理思想的深化之处。
三、“永”—道德修养的境界
对整个宋明理学来说,道德修养首先关联着成圣的过程,道德践履具体展开为人圣工夫,其最终的目的和期望是圣人之境;杨慈湖亦然。通过“毋意”的道德修养方法,以及“持循笃”的道德践履工夫,杨慈湖旨在达到本心清明纯善,自然静定,天地万物万化万理归一的物我一体、寂然纯然的圣人之境。而这一道德境界,就是他所谓的“永”之境。
杨慈湖认为,“永”之境是一切道德践履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何谓“永”?他说: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永也。困也就是说,“永”不能通过对外物的认知获得,相反,它必须摒弃一切外在的努力,摒弃一切思虑和对知识的追求,摒弃一切不合乎伦理本能的意念和行为,即“毋意”,使本心如日月之光普照大地一样自然流露,对万事万物从容自然、不偏不倚,不掺加任何人为的成分。杨慈湖认为,这一境界就是孔子所说的“何思何虑”之境,也是他所谓的“无知之知”之境。这种境界很难达到,只有始终如此、昼夜如此、动静如此、今日他日永远如此,才可谓达到了“永”之境:
陶日:谨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终不如此,非永也;静如此动不如此,非永也;昼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日思之,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觉,觉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日:天下何思何虑,谓此也;日毋意,谓此也;曰无有知乎哉?无知也,谓此也。
但在同一篇文章中,杨慈湖又说:
一日意虑不做,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一日之永,是谓日至;一月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一月之永,是谓月至;三月意虑不作,澄然虚明如日月之光,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此三月之永。
在这里,杨慈湖没有强调达到此境界后的一贯性,而是从个体修养的角度强调“永”之境并不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而是人人通过修养每时每刻都能达到的;因此,才有“一日之永”、“一月之永”、“三月之永”等等。就此意义而言,杨慈湖的“永”之境界实有层次之分,而这一层次也为贩夫走卒,庸常小人的修养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只有这样,“本心”的自善自明才能具有可行性,“人人皆可成尧舜”才不致是虚言一句。也正因为如此,杨慈湖之“纯永”,可谓“永”之最高境界:
文王之德之纯永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朴天清地浊未分时如此,朴万世之后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范围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发育万物者,此永也。
可见,作为“永”之最高层次的“纯永”乃是超越了时空、生死、古今限制的“永”。只有达此“永”之层次,才能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在杨慈湖看来,这一层次实为一般人所难以企及,只有像文王这样的圣人才能达到,但这恰恰为儒士提供了修养的最高目标。故这种对“永”之境界的推崇,与杨慈湖对“本心”自然静定特性的规定相合,从内在精神气质而言,亦契合于其内向善于冥思的性格特征。
“永”之境就是“本心”澄然清明、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境界,也就是杨慈湖深慕的《易大传》中所谓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9〕的天人本一的圣人境界。由于其所谓的“永”之境具有一定的层次,因而使其具有现实的可企及性。同时,又通过“纯永”之境的确立,使儒士修养有了最高目标。这样,杨慈湖的道德修养境界论就使最高目标和一般目标结合了起来,一方面避免了使儒家的道德修养境界成为遥不可及的高峰,另一方面亦避免了把最高道德境界当成一般目标。因此,后人多从持循、践履上对杨慈湖大加赞扬,亦有一定的道理。
四、余论
正如前文所言,在杨慈湖的“毋意”道德修养论中,本体与方法达到了一致。“意”不但是沟通本体之善与现世之恶的中介,而且“毋意”本质上是由善心把握的。而“意”范畴的提出,为建构与“性本善”相一致的伦理方法论奠定了基础。这种以“意”为预设的伦理方法论,对王阳明颇有影响。对此,后世学者亦有辨证:“吾明王文成公良知一派,固毋起意鼓吹也,称慈湖见解已晤无声无臭之妙。磋磋,读是书者,能潜撤边见,默默证心,其禅耶,非禅耶,亦当有会于声嗅外。”(潘汝祯刻《慈湖先生遗书序》)在王阳明看来,事物作为人的意向结构的一极,是不能脱离主体的,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一切活动都是意识参与下的活动,在此意义上,离开主体的事物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意之所在便是物”,实际上是王阳明“心外无物”说的主要论点和论证。这样,“心外无物”的意义就是要人在心上作格物的工夫,“格物”就成了“格心”。“意”便具有了与“心”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意”又具有“善”与“恶”两种可能性,发自心体而动的,即为善念;过与不及而动的,即为恶念。因此,“正心”的工夫实际上就是“正意”。这样,王阳明之“意”在继承慈湖思想的基础上又深化了一步,使其具有了和“良知”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杨慈湖在陆王心学伦理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可见一斑。
但是不可否认,在整个陆王心学伦理思想史上,杨慈湖之学不得彰显亦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究其原因,约略有二:
其一,许多学者认为杨慈湖之“意”乃直接得自禅宗。刘宗周就曾言:“慈湖言意,分明是禅宗机轴。”〔’”]其实就“意”范畴而言,如前文所述,孔子亦有此范畴,非佛家独有。当然,就对意的具体论证上,杨慈湖确是借鉴了佛家的方式,如佛家所言“无念者无邪念,非无正念”(《顿悟人道要门论》);杨慈湖谓“不起意非谓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则不可。”同时,杨慈湖认为“毋意”不涉及任何心理变化和知识的积累,不借助于任何如言辞一类的中介物,只能是顺着人心所固有的道德本能回复本心之善的观点,亦与禅家的“佛性说”相类。但禅家回复的是佛性,杨慈湖回复的则是儒家的道德本性、善性。另外,杨慈湖所谓的人心本善,恶的根源在于“意之起”,主张以“不起意”为宗旨,认为只要不起意,无思无为,心境则自然静定,是非贤否也就历历照明的观点,也是在借鉴佛教无我、无心、无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就“毋意”的具体内容而言,杨慈湖之“毋意”不同于佛家之“无念”。杨慈湖之“毋意”主要指的是克制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意念的萌发,而佛家之“无念”要求的是无善恶皆不思念的思维寂灭。因此,杨慈湖虽然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佛家的思路,但在“意”及“毋意”的具体内容上却是儒家的,因此将其等同于佛家之“念”、“佛性”以及“无念”说是勉强的。
其二,从总体上看,杨慈湖之伦理思想过于简截,这就使其学说缺乏了理论伸缩度,再向前向深发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故连其弟子对其“毋意”及“合”论等亦缺乏足够的把握,这就很难想像其他学者能知其精蕴。而杨慈湖之学的这一特点,亦或多或少是陆王心学的总体特点。钱穆先生在总结陆王心学的特征时就说:“陆王之学为理学中之别出……因别出之儒,多喜凭一本或两本书,或凭一句或两句话作为宗主,或学的。……象山则专据孟子,又特提先得乎其大者一悟;而阳明则专拈孟子良知二字,后来又会通之于《大学》而提出致良知三字,作为学者之人门,同时亦是学者之止境,彻始彻终只此二字,后来王门大致全如此,只拈一字或一句来教人。”钱穆先生虽然没有列举杨慈湖,但如黄宗羲所言“慈湖以不起意”标宗,即是明证。钱穆先生接着说:“总之是如此,所谓终究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简再易,故可谓是登峰造极。然既已登峰造极,同时也即是无路可走。”慈湖之学不得彰显,即是这一“无路可走”的说明。
[参考文献]
[1]杨慈湖.绝四记〔A〕.慈湖先生遗书(卷二)[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2]杨慈湖.诗解序〔A〕.慈湖先生遗书(卷一)[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3]杨慈湖.家记三·论礼乐[A].慈湖先生遗书(卷九)〔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4]杨慈湖.乡记序仁(A).慈湖先生遗书(卷一)[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5]杨慈湖.宝漠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近[A].慈湖先生遗书(卷十八)[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6]杨慈湖.永嘉郡学永堂记[A].慈湖先生遗书(卷二)[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7]杨慈湖.家记七·论《中庸》汇(A).慈湖先生遗书(卷十三)[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8]杨慈湖.临安府学记〔A〕.慈湖先生遗书(卷二)[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9]杨慈湖家记一·己易〔A〕.慈湖先生遗书(卷七)[C].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
[10]薇山学案[A〕.明儒学案(卷六十二)[C].北京:中国书店,1990.
[11]钱穆.中国学术通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崔大华.南宋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