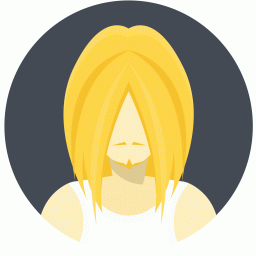今天,他们这样上大学
时间:2022-06-29 09:12:43

对于大学,还没迈进大学校门的同学一定有许多憧憬,已经在大学校园生活的同学一定有许多感触。也许,你有困惑,有迷惘,有抉择的艰难,有徘徊的痛苦,然而应该如何上大学这个问题,一定是值得你深思的。这几个同龄人的经历也许特殊,但对你可能有启发……
我为何放弃北大
6年后,翟翔还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橱最显眼处。那年9月,他没有拿着这张通知书去北大报到,而是报名参加了新东方的托福班。7个月后他收到格林奈尔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转学康奈尔。
翟翔说,放弃北大,带着无奈。他当时被分到医学专业,可这位理科生一心想学文,而那时北大的政策是医学部学生不能转系。
翟翔在安徽长大,5岁那年,他像同龄孩子一样迷上《戏说乾隆》,学历史的愿望,也就这样开场。
收到北大通知书的第二天,他去了欧洲旅行。通知书上的“北大”字样,帮他免去了剑桥国王学院的门票。剑桥的古老校舍和长袍教授,却让他下了放弃那张通知书的决心。
翟翔此前从未想过留学。但实在不想学医,复读风险又太大,才开始申请留美。在寄往康奈尔的申请中,翟翔以一篇对于台湾和大陆问题的看法的文章,打动了康奈尔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如愿做了历史系学生,虽然不是在曾经向往的北大。
问翟翔对康奈尔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说:“大。”一个大学有森林、溪谷、果园和农场,怎一个“大”字了得。
问他在康奈尔读书的感觉是什么,他说:“苦。”没有一门课是必修的,但每门课都不轻松。课上可以边听边享用教授带来的茶点,课下,则每周要读一本两百多页的书,每月写一篇论文。好几次,他在图书馆工作到清晨。发现身边不少美国同学也一样通宵奋战,靠着沙发、趴在桌上、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他的刻苦可以用回报证明。在康奈尔,翟翔历史专业的平均成绩基点是3.9,辅修的东亚研究是4(标准满分为4)。康奈尔素以给分严格出名,一个在这里流传已久的笑话说,康奈尔人“在华氏20度里,爬30度的坡,考40多的分”。康奈尔的创始人相信,压低分数可以鼓励学生更努力地学习。
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学历史,特别是学美国历史,不是件容易的事。曾在康奈尔留下多年无人打破的高分神话的赵元任,感慨自己学生时代最大的失败,就是美国历史那门课只得了68分。
翟翔觉得学习美国人的历史观很有意义,许多教授的包容精神也令他获益匪浅。高中班上,十几个同学去了北大清华,大家后来聊起两地教育的差别,翟翔概括为“美国的课上没有正确答案”。“当代美国外交史”那门课的期中考试,教授要学生假想自己是20世纪下半叶的国务院官员,针对任一外交事件,向总统提出建议。翟翔说,这门课的教授,以批评美国外交“双重标准”而出名,对“异见”只会鼓励。
作为稀有的历史系中国学生,他帮助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的中国文献。在大洋彼岸梳理久远的中国记忆:嘉靖本永乐大典残卷、康熙给罗马教廷的信函、给美国友人的签名照片……翟翔说那种心情很复杂,最遗憾的是,这些文物虽然受到很好的保护,却因缺乏研究而被埋没。
去年夏天,翟翔在北京的一家银行总部从事涉外工作。他还想再回到美国,完成斯坦福的硕士学业。谈及未来,翟翔想起当年申请康奈尔时那篇关于两岸的文章,为两岸交流做点事,这仍是他的理想之一。
告别清华的现实主义者
做了一年的清华学生,马驰(化名)选择退学,到大洋彼岸的宾夕法尼亚报到。
“出国留学的想法很早便有了。”小时候在重庆合川的县城长大,初中他就自学了4册《新概念》,还把第二第三册的课文全背下来了。
同时,他痴迷数学。高二,他已拿到全国数学竞赛银牌。被保送清华。“高三那年原本计划申请美国,可拿了银牌。又想拿金牌。”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去了清华数理基科班,一切重头来过。回忆清华的一年,马驰想到4个字,“刷题考试”。后来在宾大的沃顿商学院,遇到北大清华的交换生,印象是“他们比我们更刻苦,我们也考不过他们”。
“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数学家。”马驰在沃顿学金融,问他学习的乐趣和目的何在,他说:“应用数学。”
马驰说,普林斯顿、哈佛,特别是耶鲁的学生。在他们眼里“有点文艺”。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商学院,沃顿给他的最大感受是“现实”。以一门课为例,曾经是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的教授,要求学生们用一个虚拟账户。依市场的实际情况去运作资本,最后按赚钱多少来给分,最后亏本的只好拿C。马驰说,你也可以选择保守,把钱存进银行收利息,那还可以拿个B。
沃顿商学院的现实主义也影响着宾大的其他学院。马驰记得一个机械工程学院的同学,一门课整个学期的内容就是造一个发动机,“每一个齿轮都是自己磨出来的”。
马驰不愿多提自己的成绩,只是在讲到学院体制的灵活时,不经意透露,本科时有能力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可以豁免掉相应的本科课程,直接拿到研究生学位,他就是这样。
马驰承认中学时代对数学的钻研让他占有优势,比起大多数美国同学,他也更刻苦。但这些也许不那么重要了,“进到公司,最重要的是怎样让别人喜欢你,教你东西。”和人混的技巧,正是白人同学的优势所在。
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马驰的就业目标是美国和中国香港。不过,当年他是带着“应用数学”的愿望去沃顿的,现在,想法有些变了。“理想又回到了做个数学家,”他笑说,“因为我还是喜欢平静一点的生活。”
从复旦“游学”到北大
如果说翟翔和马驰代表的是大学生中的精英,那么樊羽的经历也许更能代表普通大学生的迷惘与追寻。
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从哲学系张汝伦老师、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到管理学院谢百三老师。只要在校内很“火”的课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学的本科生,18岁决定休学到复旦旁听。两年间,从复旦到北大,他以“游学”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本科教育。
两年前,樊羽考入了自己的大学,专业与金融相关。他的数学底子不好,被调剂去学数理统计,有些头疼。咨询了学长学姐的经验,发现在这里读到毕业,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无几。考虑到未来的生活,他的厌学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学期课以后,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学习了。上课和考试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热情慢慢没有了。人应该是要学到老的,但是如果现在就觉得学习是件痛苦的事,那毕业以后肯定也不会自己找书去读了。”
看着室友打游戏,坐在课堂上发呆,时间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转过一圈后,他决定来复旦旁听。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学校附近,600块每月,三四个人挤在15平方米的隔间里。
初到上海,在朋友推荐下,他听了哲学系名师张汝伦教授的课,“一听,真的很好”,接下来从《国学概论》到《四书精读》,他连着听了张老师三学期的课。
他还旁听了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哲学系王德峰老师的课。前者讲古典诗词和魏晋风度。后者讲哲学导读和大学精神,樊羽听得很投入,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樊羽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课表。哲学,中文,历史,经济、管理、政治……什么专业的课他都有兴趣去听,只要老师讲得好。每学期,他固定去听的课程有10门之多,还有六七门偶尔去听,连双休日都排满。两年下来,如果算学分,他已经可以本科毕业了。
同时,他也积极地去参加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各种活动和讲座,业余时间排得很满。到北大后也依然如故,参加社团活动,饱览北大百年讲堂的话剧和音乐会,临走的时候,手里还刚买了孟京辉的话剧票。
旁听生们在逃离了功利主义的学分等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师的课堂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沉淀和满足。这些极少数主动求学的“游学”者,作为一种提醒的力量,给校园内为了文凭奔波的大多数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击和反思。从复旦到北大,很多知道樊羽经历后愿意帮助他的学生,都很“羡慕”他。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