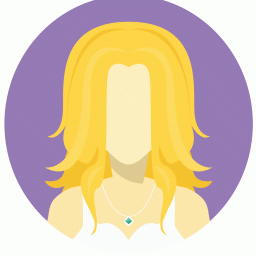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及其民族主义立场
时间:2022-06-21 12:57:18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迅速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史观”作为其启蒙思想的主要方面,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其“文明史观”具有民族主义因素的主要基础。
(一)
福泽谕吉出身于德川幕府末期中津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深受封建领主的压迫,深刻体会到了封建制度的反动腐朽,同时又目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下民族独立和国家受到的严重损害。在内忧外患的逆境中,福泽立志与封建专制作斗争,并以谋取民权独立、国家富强为己任。他早年学习兰学,后又曾作为幕府遣外使节的随行人员,三次游历欧美,谙熟西方文物制度,深受西方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积极介绍西洋各国情况,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他的思想对当时的明治政府影响很大。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把“文明开化”定为国策之一,宣称“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的输入,为日本带来了产业革命的曙光;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人,给传统的旧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空前的混乱。
这时福泽谕吉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一系列著作与言论在当时起到了方向的作用,为日本文明、国家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劝学篇)中主要涉及到福泽有关平等及如何才能平等的话题,虽然其平等的前提是与西方文明国家的平等。
有关文明的观点主要集中于(文明论概略)中。
首先,福泽谕吉比较全面、客观地揭示了“文明”这个概念的内涵,正确地指出了人的智慧、道德在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总体上来说,福泽把文明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加衣食住的外表装饰;从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还要砺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文明”一词,至大至广,无所不包,从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智慧等,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包括在文明这一概念中。
福泽又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文明行了分析。他认为,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说衣食富足、品质高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好比人的身子和影子一样,形影不离。同时,他批判了仅以身体安乐和衣食富足作为文明的错误概念,指出,“人生的目的不单为衣食,若仅以衣食为目的,人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进而,他也批判了仅以道德高尚便可称作文明的偏见,认为如果仅以道德高尚就可称作文明,那“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人类社会就永远停留在原先水平,无法进步到今天。福泽以为,“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他高度重视人的道德、智慧对文明的作用,认为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德、智而取得的。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因此,一个国家的文明,实际上就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要想促进文明,振兴民族,必须首先提高本国人民的道德和智慧。
其次,福泽对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作了比较,分别提出了对日本文明及西洋文明的看法。
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与客观现实,指出,日本的传统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西方有日本没有的东西:一是“有形的数理学”,一是“无形的独立心”。在《劝学篇》中又指出:“今试观我国现势,其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世界文明不外就是这三项。如果这三项不完备,国家就不能独立。”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在一次肯定日本落后,西方先进。指出: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日本没有一样能和西洋比较。当日本还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在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铁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
福泽虽然断定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但并不认为西洋文明登峰造极,尽善尽美。他从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把西洋文明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加以考察。
他认为现在西洋各国为文明,只不过是至目前这个时代“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人的智德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文明的进步也是没有止境的。“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慧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世界上没有“达到顶峰的国家”,也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他指出,文明这个概念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与尚处在野蛮、半开化状态的亚洲、非洲国家相比较,西方可称为“文明”。但仔细分析起来,西方国家不文明的东西很多,还有不少弊端和丑恶。总之,西洋文明绝不是天花乱坠,美好无比,而是有不少的丑恶现象。
接着,福泽又提出了人们应对西洋文明的态度。
福泽认为正视现实、承认落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要使本国进步、繁荣富强,就必须毫不迟疑地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学赶西方。要坚决摒弃那种迷惑于旧习、沉湎于本国古老文明、对西洋文明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愚昧短见,尖锐指出“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珍视,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因而在古老文明的沉重包袱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下不能自拔,只好落后于世界潮流。1885年《脱亚论》中福泽极端蔑视中国和朝鲜的“古来之政教风俗”“自今之后不出数年丧土亡国”,而日本“当今之谋,不可再有等待邻国文明共兴亚细亚之犹豫,不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脱亚入欧”是其后来对亚欧文明鲜明态度的集中表现。
不过,福泽也十分鄙视那种在西洋文明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无所作为的奴才相。他说,文明和落后是相对的、变化的,一切落后国家在西洋文明面前,没有理由悲观泄气、丧失信心。“即使前途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
福泽正确地指出:落后国家在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时,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取舍适宜”,切不可“全盘效法”,更不应该“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要“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即先汲取文明的精神,“变革人心”,“改革政令”,“为汲取外形文
明开辟道路”。他认为今日日本的文明尚不能称为真正的文明,只是“徒具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福泽这些深谋远虑的主张,对日本迅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福泽谕吉所处时代的因素,其文明史观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意味。在《学篇》及《文明论概略》已有明显的反映。
(二)
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确立其统治的时代,也是西方列强挟其文明利器疯狂侵略东方国家的时代。对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来说,确保国家独立、避免印度和中国的覆辙已成为当务之急。围绕民族存亡问题进行思考是19世纪东方诸国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点。生于此时的福泽谕吉,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受到这一时代特点的制约,他对民族与文明变革相互关系的理解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一般都把《劝学篇》中他所提倡的人人平等的独立精神视为该著要阐发的中心思想。并据此认为,这是一篇民权宣言,但认真剖析一下就会发现它同时又是一篇民族独立的宣言。福泽并不是就民权而谈民权,而是把民权从属于国权来认识的。它的深刻寓意在于,通过人的平等独立来论证国家的平等独立。在他看来,“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心国事”,“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国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所以,“为了抵御外辱,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可见,为国权而主张民权是《劝学篇》基本思路。在《文明论概略》中更是提出了“国家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并且一直都把它作为该著的中心思想,即:文明是达到国家独立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
福泽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不存在超国家、超民族的抽象文明。文明只能搭乘于具体的民族国家载体之中,或者说,文明只有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他指出:“如果单提文明,就可能意味着存在某种与国家独立和文明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存在某种危害国家独立和文明的似是而非的文明。举例来说,现在日本各港口的繁荣虽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都是外国的,陆上的贸易大厦也是外国人的建筑,与我国的独立与文明毫不相干。”因此,“总是这种文明能得到高度的发展,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不能成为日本的文明”。
福泽还明确提出了要把国家独立当作日本现阶段面临的首要课题。
他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如前所述),认为“从总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沿着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轨迹前进的,其中,先进的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受制于先进的,并将此视作确定无疑的规律。对于日本的现状,福泽指出,既然已知“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并知道了落后就要被先进压制的道理,这是,我国人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国家的独立问题”。
福泽明确地将国家独立和文明变革的关系确定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他承认“文明的含义非常广泛,……在世界各国中间争取本国的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枝末节”,但又表示对待事物“必须考虑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然后福泽提出了“我是站在当前日本的立场,自然要把议论的范围缩小,只是把有助于本国独立的东西,姑且定为文明。所以现阶段我国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作为事物发展的第一步,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领带第二步,将求再解决。在这样限定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国家独立也就是文明”,“国家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同时,他的这一民族主义的意识还渗透在其思想的其他领域和各种具体的主张中。
他历来主张对外开放,但当一部分外国人杂居日本内地时,他又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给予严厉的批评。认为,对外开放是日本文明变革、国是增强的必要条件,但开放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承受能力。只有等日本国内的法律、贸易等各项建设基本完备以后,方可“允许杂居”。福泽在经济上,竭力主张发展近代产业,“巩固立国之本,充实国力以便对外一战”;在贸易为题上,不同意在日本经济实力上弱于西方国家的现阶段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国输入品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后来,福泽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1878年在《通俗国权论》中说:“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及一筐弹药”,“国家交际之实不过为争权威贪利益”而已。1881年在(时事小言)中写道:“严我军备,张我国权,其武备不在独守日本一国,兼在于保护东洋诸国”。1887年又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朝鲜是日本藩屏》、《与外国战争未必危事凶事》,公然提出变朝鲜为日本殖民地,为此不惜与清一战。在以后的日子里积极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把其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发展为国权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由此,其思想中民族主义的本质才裸地呈现出来。
(三)
尽管福泽谕吉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确实有一些关于国家平等的言论,而且这些言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同时伴随着大量不平等的言论。但在其思想主流表现于中的后期言论更多的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福泽思想具有平等与强权倾向并存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日本民族的最大希望是取得国际地位的独立,首先要废除幕府所签订的,后来明治政府又一定程度上承认的不平等条约,最大的障碍是日本的国力不够强大,于是日本的领导者以及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有着很大的矛盾性。但其一切的目的自然是日本国家的独立,其它都是权宜之计的手段。福泽亦不例外。
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福泽民族主义思想中一度存在的平等与强权的双重性就被民族强权的单一性所取代了。其实这是其思想的继承性表现,而不是所谓的“转折”性。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其―惯性的表现与其他言论的基础。
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它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时代使然,对福泽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其后却发展成为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则是我们必须批判的。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