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走进普通人
时间:2022-06-19 08:3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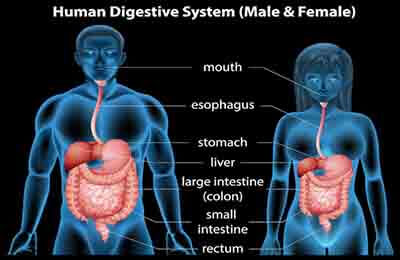
“能用的器官都捐。”这是作家史铁生的生前遗言。去世9小时后,他的肝脏和角膜在两个人的身体里苏醒。
近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
卫生部办公厅近日也下发了,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全面推进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决定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试点时间为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30日。在已有该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的移植医院指导下,开展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捐献者将有望获得物质补偿。
全球性的器官短缺
随着各种致病因素的累加,末期器官功能失灵已经成为困扰现代人健康的一大顽疾,虽然医学科技的进步已经使器官的替代成为可能,但是器官来源紧张却让很多苦苦求生的愿望无法实现。在美国,每16分钟就有一名患者加入到等待移植手术的名单中,每90分钟――一场足球赛的时间,就有一位患者在绝望的等待中死去。内脏器官不同于假肢,无法通过物理复制进行再造。残酷的现实是,每一个焦急等待手术的患者的生存可能,全部系于另外一个人的捐赠意愿。
人体器官就其来源分为死体和活体。前者是以死者生前同意为前提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而后者是从活体身上获得器官。然而,死体器官捐献与一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在东方,为逝者保留遗体完整性的思想根深蒂固,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捐献意愿。在伊斯兰世界里,亦有源自《古兰经》的类似观念。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到,亚洲国家的死体器官捐献率相当低,成为器官移植的最大阻碍。
相较于死体移植,活体器官移植在医学上的优越性已经被一再证实,但是它极易带来器官买卖,在世界范围内,器官贸易已经成为挑战人情、伦理、道德和法律的一个庞大产业链。从墨西哥、巴西成百上千的“失踪”儿童被发现剖肝挖肾葬身魔窟,到巴基斯坦、印度贫民窟里排队接受肾摘除以换取区区几百美金的赤贫百姓;从一个个日本、韩国、台湾“旅行团”来到中国大陆购买肾源进行移植手术,到在菲律宾公然进行的器官交易,活体器官移植在挽救了许多患者垂危生命的同时,正在挑战医学伦理的底线。在基督教国家,人体的神圣性和器官捐献的纯人道主义动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敌不过大把的美金。
在死体器官移植来源增长缓慢的现实下,活体器官买卖的黑市日益繁荣。一边是数以百万计并且还在不断增多的绝望等待器官的患者,一边是低迷的捐献率。
中国器官移植:现状与乱象
我国器官移植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约为15万例,而供应只有1万例。就连最简单的眼角膜移植,患者都有十几年等不到的。另一方面,我国每年突发性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这些宝贵的器官资源化为灰烬。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捐献器官的观念和法律制度。
我国人体器官的移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国内很多医院肝脏移植的一年成活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五年成活率也已接近80%。肾移植的五年成活率已经高达70%。然而,供体的严重不足让医疗技术的进步没有用武之地。按照卫生部统计,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现状为1:150,约有100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他们或只能依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在苦苦的等待期间,每月的治疗费用高达七、八千元。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人中,有400万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1000多个角膜供体。全国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全国只能开展2000例左右的肝移植手术。据统计,全国去年只成功实施了28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手术。
在活体捐献方面,2007年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恰恰是这个“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给非法操作留下了口子。现实中伪造各种文书证明与患者存在亲情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假结婚、假亲戚亦非常普遍,而法律规定的最后一道“把关者”――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也往往形同虚设,无法发挥甄别检验各种“假亲属”的作用。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必须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可是在现实中,金钱交易几乎无处不在,很多城市已经形成由医院和各种掮客组成的器官移植产业链,享受这种服务的前提就是:“你有钱”。在无数人漫长而缺少希望的等待中,稀之又稀的器官给谁,是给有权、有钱的人还是给最需要的人,成为关注的焦点。
更让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器官移植旅行的大行其道。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这种旅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最后的希望在中国”已成为许多国家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都知道的一句话。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和中东国家的患者纷纷来到中国大陆,“为求生赌最后一把”。很多互联网的广告宣称,到中国肝肾移植等待时间为一个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体,而这一时间在美国和欧洲是三到六个月。大量外国人的涌入,让本已捉襟见肘的中国供体库不堪重负,有限的供体本已无法满足本国的需求,还要与富裕的外国人竞争,2008年我国政府开始命令禁止外国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行,可望抑制“外国人与中国人争夺器官”的状况。
向左走?向右走?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关器官移植的种种乱象,说到底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应该以一种符合伦理和法律的方式进行。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供源的努力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提高公民的生前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的比例,扩大死体器官供体库;二是通过提供一定程度的物质回报以激励潜在的活体器官捐献者。前者最有名的例子是“西班牙经验”。1989年时西班牙全国还只有550名器官捐献者,捐献率为全欧洲最低,每百万人中只有14名捐献者。而随着西班牙全国器官移植组织的成立,该国通过一波波的宣教和推广活动,并辅之以有效的制度建设,15年来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2007年西班牙器官捐献总数为1550例,比美国国民的平均捐献率高出8个百万分点,是欧盟平均捐献率的两倍,更多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对器官移植的巨大需求,让很多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对活体器官移植政策作出调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新加坡,该国于2008年修订了人体器官移植法案,允许给予活体捐献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活体器官捐献者获得的补偿将被自动存入其个人医保账户,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折现,大大降低器官买卖发生的可能。
偌大的中国, 供给与需求的巨大鸿沟每天都在加深,这就意味着一个个生命在绝望的等待中逝去。政府已经在努力缩小这个鸿沟,但是挑战艰巨。日前卫生部又出台一系列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来积极鼓励、严格管理活体器官捐献,给那些受伤的生命点燃了活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