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精于勤――读杜滋龄水墨人物画有感
时间:2022-06-14 05:4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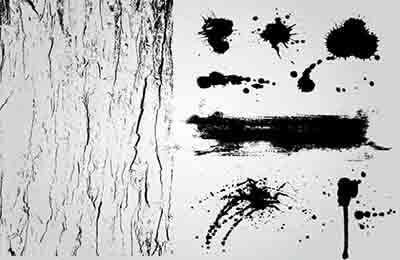
杜滋龄艺术简介
1941年生于天津,1979年考取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曾师承著名画家叶浅予、李震坚先生。在继承中国民族艺术精神的同时,融西法于中国绘画之中,以形写神,立清新、朴厚之风格。作品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风情为主要题材,偶有中国古典题材之作品。许多重要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出版。
曾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系主任、教授。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文联委员,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院杜滋龄工作室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
西方文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惑,可谓道路曲折,步履维艰。但值得欣慰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批新的画坛英才打破了多年的画坛沉寂走了出来,他们经过20年风雨锤炼,如今已成中国画坛的中流砥柱。他们大多生于40至50年代,生活上的困厄,政治上的磨难,使他们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艰涩的滋味,经过艰辛而修远的求索,一批天分卓越、修养深厚、思想活跃而又能头脑冷静、扎根现实而又能登高望远的艺术家脱颖画坛,杜滋龄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名成功的画家,须有扎实的功底。今天,杜滋龄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画写意人物画领域确立自己的地位,与他厚实的艺术功底是密不可分的。年少时,杜滋龄不但酷爱本民族文化,还对西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大量的油画风景写生以及惊人的速写数量,使杜滋龄从小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绘画表现力。当年,为了买一本自己喜爱的画册,他可以省去多日的早点钱;为了寻找一个好的写生地,他可以凌晨3点就起床骑车前往。用画家自己的话说:“为了艺术,我可以舍去一切物质上的享受和诱惑。”业精于勤,是杜滋龄艺术发展道路的最好写照。长期从事美术出版工作也对杜滋龄的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而复杂的编辑工作使他能够看到诸多优秀作品,能有机会向老一辈艺术家讨教。尤其是得到了叶浅予先生的指点,这无疑对杜滋龄的绘画道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9年,他又以极大的毅力和热情考取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成为“”后我国招收的首批研究生。李震坚先生的教诲,又给予杜滋龄以新的艺术启迪。从那时起,杜滋龄在写意人物画方面以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走向成熟和成功,得到老一辈画家们的期许和当代画坛的广泛注目。
细细观赏和品味杜滋龄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以十分诚实的品格和平静、质朴的心态,去感受壮美的山川、人生的美丽,并醉心痴迷地捕捉它们的形与神,然后诉诸于自己的笔墨中。他的画正如他的人一样质朴深沉,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其作品中感受到辽远而永恒的阳光、空气、土地的气息。他从不粉饰生活,更不矫情于表现,他只是深情地把生活中的真善美用心再现出来。从他那浑厚酣畅的笔墨中,流泻出一曲曲生活的赞歌。在那些生机盎然的作品中,既有个性风采的抒写,又有来自生活深处的纯朴和清醇;既有“人迹罕至”的泼墨大写意,又有刚柔相济、妙趣天成的线描。饱览之余,令人为之一振。我们在看到画家充满妙想的精彩笔墨时,也不能不为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那一片深情所陶冶。石涛曾言:“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其中的“受”就是要深入生活,亲身去感受生活,然后从中认识生活的美与爱,来激发画家自己的创作灵感和热情。杜滋龄正是这样的画家。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北方,在他含蓄谦逊的性格背后,也有着豪放豁达的一面,所以在他的笔墨中富含北方人特有的那种痛快淋漓、恢弘磅礴之感,充分继承和体现了北宗水墨的气势。同时,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求学经历,又使他的绘画充满了一种南宗气韵,用笔清劲洒脱,追求墨韵的灵动与润泽,不作拙、涩、怪、险之笔,并大胆借鉴黄宾虹在山水画中“雨淋墙头月移壁”的干而润、润而见骨的画法以及“墨、密、厚、重”的浑厚华滋的画风。在用色方面,他偏爱黑白,善于布白,作品中有意减弱飘忽跳跃的色块,加强黑白对比及韵律,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墨色交融成趣,而又各自分明,将传统水墨的灵性和精要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日复一日的艺术创作中,杜滋龄十分重视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他深深地意识到,笔墨问题是每一个中国画画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作品中的笔墨力度,笔墨自身的品格,笔墨关系的协调完整,都被画家本人提到了重要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难能可贵的是,年逾耳顺的杜滋龄,仍在不断地进行着艺术的探求和尝试,如今从他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笔墨表现手法,最常见的是积墨法,许多墨色不是一遍而成,而是经过反复渲染而成,这样一来,墨色层层浑厚,灵秀动人。再加上色彩的巧妙运用,更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一种迷人的韵调。在注重笔墨的同时,他还在水与色之间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用水或铺或凝或融,充分发挥水的无穷变化,使画作的气韵更加生动。在他的水墨中常常是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色墨互不妨碍,使画面更加丰满强烈,且具备一种特有的厚重感。他还在材料上进行一些新的组合,在不同的纸张上,用秃笔、硬笔、宿墨、焦墨、纯色进行艺术创作,以营造种种特定的艺术表现效果。
除了注重笔墨外,杜滋龄还很注重绘画中的虚实处理。他早年就从艺术前辈那里得到了“实处易,虚处难”的绘画真谛,而且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阴阳虚实相济,正是绘画表现的奥秘所在。黄宾虹先生曾言:“虚是内美。”又曰:“虚中运实,柔内含刚,此笔法也。”“虚中有实,可悟化境。”对于黄宾虹先生的“虚实观”,杜滋龄没有简单地理解成为“虚”即“白”,“实”即“黑”,他认为黄宾虹先生的“虚实观”是指绘画创作高层次上的一种虚实关系的处理,含有画家对创作对象的提炼、认识,这是画所必备的一种表现境界。一般地说,“实”为具象,是对景物的具体描绘;“虚”为抽象,是对事物的一种提炼和升华,寓有精神气韵。杜滋龄认识到应从实到虚,先要有能力画满整张纸,满纸能实,然后求虚。遵循黄宾虹先生对于笔墨运用的精确总结,是杜滋龄对自己的艺术要求之一。在遗貌取神的审美框架中,杜滋龄把手段和目的统一融合,通过绘画中的墨象来表达心象,伴随着50多年的艺术磨炼和对笔墨的研究,杜滋龄的笔墨功力已经近乎成熟完美。
线也是中国画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手段,也是最高造型手段。李可染先生在谈“线”的表现力时说:“线的基本原则就是行笔要稳,留得住,每一笔都要送到底,切忌飘,要控制得住。古人的积点成线就是这个意思。务求每一笔都要代表更多的东西,就必须控制住线,同时还要注意每一笔和整体发生联系。”杜滋龄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在不断地感悟和学习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吴道子的“天衣飞扬”,李公麟的白描,梁楷的减笔,陈洪绶、任伯年的勾勒点抹,叶浅予、黄胄速写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书法临习。在临习书法作品的过程中,研究并借鉴了书法的线条、结体与章法等形式美,故此他的线描功力深厚扎实,精于线的刚、柔、枯、润、虚、实等各种变化。他能紧紧抓住主体形象的特征,用最精练而又富于生机的笔墨线条来表现复杂的内容,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从他一幅幅生动的写意人物和毛笔速写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画家已入妙境的线描功力,同时又可感受那种兔起鹘落、即兴神驰的气势。正是多年的苦行,才有今日笔下的无限生机,翻开杜滋龄的画集,有笔有墨、风格迥然不同的力作比比皆是。
在师古人的同时,杜滋龄更重视师造化。他说过:“中国古代优秀的画家都能够深入大自然中去体验,一味地临摹是得不到大自然的真谛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画家只有生活在这个创作源泉里,才能凝练自己非凡的创造力。生活基础越深厚,其作品才会越隽永、越动人。石涛的“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精辟论述,早就开启了杜滋龄的心扉,并指导他从多彩的现实生活及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技巧。他还铭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创作原则,在艺术实践中融造化和创作于一体,在抒发个人主观情思时,力求做到主观客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