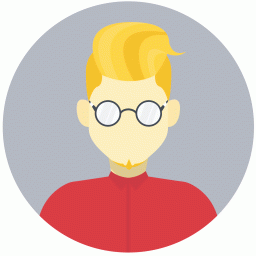隐匿于市的“黑屋子”
时间:2022-04-23 11:47:57
接二连三地有人失踪,电话关机,联系不上。家人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要等多久才会再出现。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被谁带走了。被带走的原因,有时只是去政府或非政府机关反映了问题,递交了材料。多半是来了北京,也有些是去了省会城市。
这些天,有许多莫名的信息突然发到记者的手机上。其中一条这样写道:救救我吧,我是某地的某某某,刚才大约16点30分,我坐公交车485路时,被司机和乘务员举报,现在被民警扣留了。
北京的485路公交是典型的访民线路,永定门站(国家局接访中心位于永定门内西街――编注)始发,第二站是北京南站,虽然老南站已经不在了,但访民们依然以此为据点聚集。平日里,访民上车后说声“上访的”,就不买票,司机们也习惯了。
这里的访民,过去多来自农村,贫穷、文化水平低,而今面貌已有很大不同。许多访民有正当职业,过着稳定甚至体面的生活,因为偶然的事件,成了访民。这些年来,甚至有法官、警察、人大代表、干部等加入访民群体,成为访民中的一员。
身份一旦转换,就会“享受访民待遇”,在维稳重点时期,公交车司机、复印店老板都可以举报他们,举报人会因此得到奖励。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在北京的访民凡是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领馆区等地上访的,都属于非正常上访。只要是非正常上访,就会被送到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访民户籍地的驻京人员则在那里把他们接走。
驻京办并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看护访民,甚至连接出久敬庄也难以做到,于是保安服务公司替代他们,强行带走访民并把他们关押起来。访民们将这些关押他们的地方称为“灰监狱”“黑屋子”。不少访民回到当地后,还会被行政拘留或劳教。
3月的全国“两会”、10月的国庆节期间,是两个重要的“节日”。这些时段,访民们即使哪里也不去,但因为口音被当地驻京人员或被驻京人员委托的保安发现,也会马上被带走关押或送回原籍。
许多人被带走之前,会给亲属或朋友发信息打电话,但稍晚几分钟他的亲属或朋友回拨过去,电话里就只有一个声音:“对不起,您呼叫的电话已关机”――他们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
隐蔽地带
西直门是北京最复杂的交通枢纽之一。从地铁站C口出,往东走,第一个路口往南进入半壁街。在一个并不起眼的院内有个都鑫园招待所,三四层楼高,这里关押着访民。
“还我手机!放我出去!”一个女声从一楼的房间里传出来。两个年轻的男人,一个在走廊悠闲地走动,一个在房门口站着,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
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这里住着一个精神病患者,吵吵闹闹,其他人却当她不存在。
这是一处普通的“灰监狱”,它的特殊在于竟然位于北二环附近,这并不多见。离这里几十米远,有一栋冰心题词的“福州会馆”,同时挂了福州驻京办的牌子,都鑫园招待所被福州驻京办就近用来关押访民。
在一张北京市地图上,一家服务于访民的志愿者组织标明了一处处小黑屋,即曾经关押过访民的地方。有地点,有人证。“南边的小黑屋比北边多。”地图绘制者说。截至2012年2月,已经有37处。
2008年,记者随一群人去举报“灰监狱”。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处荒芜的草地边上,从大院进去,里边有个小院,铁门紧锁,关了十几个人。里面的人从门缝里塞出一个纸团说,“这是里面被关的名单。”当时,哭喊声一片,干部们和举报的志愿者乱作一团。
江苏的一位访民于2010年专程来北京,在北京市成福寺附近,向记者指证曾经关押她的地方。在闹市区,入口的巷道只有两尺宽,外面一个铁皮门,进去之后转弯,里面就是关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小宾馆,正门进去,两个保安把守,里面的人懒洋洋地挤在一起。很快,保安就制止了陌生来客。
有些“灰监狱”相当隐蔽,访民们晚上被带进去,出来的时候眼睛蒙着,只记得“去的路上很多树,里面高高的墙”。即使在里面住了多日,也不知身在何处。
还有一次蔚为壮观,在离北京南站不远的地方,一个小院,竟然一下出来了四五十个人,全是被关押的访民。附近住的人说,旁边还有一个小院,住的也是被关押的访民,但由不同省份的人管理。
相比于这些分布在南四环、五环附近的“灰监狱”,都鑫园招待所的条件已算不错。都鑫园的老板是东北人,高个子,一脸横肉。发现志愿者们举报他们非法拘禁时,他冲着志愿者要动手,志愿者们走的时候他凶狠狠地说:以后别让我看见你们!
后来,这次协助解救被关押访民的志愿者宋泽在北京被以寻衅滋事罪立案调查,他是一个大学生,厌倦了公司的工作,来到北京专门帮助访民。
药剂师程梅云
在都鑫园招待所大喊大叫的人叫程梅云, 30来岁,福建福州人,她没有精神病。为了让志愿者们确认她的关押地点,她故意吵吵嚷嚷。那天早上,她用藏在身体隐蔽地方的手机,在洗手间发出了求救短信。
当志愿者们到来时,程梅云身穿红色羽绒服、绿色的毛线衣、牛仔裤。她留着一头披肩长发,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头也没有换衣服了。
在这里,两个男保安和她同住一个狭小的房间,一个打地铺,一个睡在仅和她相隔一尺的另一张床上。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被关起来。前几次都是一名男保安和她共处一室,最长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换人。
2009年,21岁的安徽姑娘李蕊蕊来北京上访,被关在丰台区聚源宾馆,遭到。后来陆续有女访民在关押处被猥亵的事情传出。程梅云也反映黑保安非礼她,但没有人理她。她的一个手机在进去时就被没收了,放在宾馆的前台。另外一个手机被她悄悄地调到静音状态藏在身上。
在老家,程梅云是药剂师,她开了一家药店,生活还算如意。去年她才成为访民。作为一个新访民,她不知道来北京上访原来如此曲折。
她来一次北京就被关押一次。这次来北京,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寄信:她觉得寄给国家领导人的信,只有在北京才能寄到,其他地方都会被拦下。
她包里带了200份材料,每份约8页纸,工工整整地手写后复印,复印了1500张,然后再用蓝色或绿色水彩笔,将重点地方画线,“方便领导阅读”。这个工作花了她几天时间。
一路上,她小心翼翼,因为她觉得火车上周围都是来监督她的人。一下火车,她就坐公交车来到天安门附近的邮局寄信,每一站都下车,一下车就找邮局,每个邮局寄几封,自己也记不清总共跑了多少家邮局。她的通讯录有五页纸,全部是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委、媒体的地址、办公电话,这是她上次上访时,在国家局外面花5元钱买来的。
第一天寄完信后,第二天她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美国大使馆。她听人家说去那里比较有效,“当地领导扣分比较多”,就会重视她的问题。她不知道那地方怎么走,就打114:“您好,日本大使馆怎么走?”然后,她再问,“对不起,顺便再问一下美国大使馆怎么走?”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这样就不会被怀疑是去美国大使馆上访,否则 “说不定警察马上出现就把你带走了”。她说她很安分守己,去了大使馆门口,也不发材料,也不说话,就往那儿一站,保安就知道她的目的,主动问她:你是来上访的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就被两个保安带到马路对面等车,派出所的车很快就到了。她就被带走了。目的地是久敬庄。那天去美国大使馆的人不多,她就一直在派出所等,直到晚上才有七八个人,被一辆车拉到久敬庄。
进久敬庄的标准程序是登记,电话要没收暂存。许多求救电话、短信就是在去久敬庄的路上发出来的。久敬庄会通知当地驻京办接人。程梅云说,每次她都是被拉上车的,有一次还被白布条绑着手脚,送到都鑫园招待所。她不愿意跟驻京办的人走,因为她知道又要被关起来。
这次,她为了不被接走,就在久敬庄里面的女厕所待了一晚上,直到将近天亮,搞卫生的人进去劝她出来,她一出来就被几个人拉上车带走了。
目的地仍是都鑫园招待所,她熟悉的老地方。一路上,她不和押送她的保安说话。
在安元鼎保安公司专职被查处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禁止保安从事行为。2013年1月,全国工作会议要求,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但的生意没有停止。
一场审判
2013年2月5日上午,河南禹州的一群访民早早来到位于六环外的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这里将宣判一桩涉及的案件。虽然这不是第一起黑保安被判刑的案件,但因为媒体及网民的传播,这个案件被广泛关注。
在2010年以前,保安辅助地方政府是公开的秘密。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其中的领头羊,依靠这项人头生意,年收入上千万元。印有“安元鼎护送”五个字的大巴,在老访民中几乎无人不知。
2010年9月,《财经》杂志披露安元鼎公司的生意后,这家公司被查处,但并未被取缔,更名后继续从事保安服务。北京市公安局则开展保安业大整顿,“是一条高压线,绝对不许碰”。
在都鑫园招待所看守程梅云的人,身穿制服,但他们不承认自己属于保安公司。当天的解救过程中,这些保安起初不愿意让程梅云离开,但是驻京办人员出现后,这些保安们就悄悄地跑了。
温榆河法庭对这起案件的判决书撇清了保安公司和驻京办的责任。据受害人之一贾秋霞称,在被关押的房间看到墙上挂着一个挺大的玻璃框,上面写着“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但判决采信了一份来自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据材料及相关人的证言,称“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与河南驻京办事处没有业务往来,与上访人员没有关系,在王四营乡孛罗营村没有机构和保安人员,营业执照没有丢失或出借过,没有发现有人冒用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
这意味着,这些关押和殴打行为,与保安公司和驻京办都没有关系。
可是,这无法回答访民们的疑问,自己与关押他们的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对方为何要关押他们呢?
贾秋霞来自河南禹州,她比程梅云有更长的上访经历。2012年4月28日,她被带到了久敬庄。当天,她和四个互不相识的女访民被强行押上了一辆车,手机、身份证被没收后,被带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关押。在押上车时发生争执,后来几位访民都反映遭受了黑保安的殴打。贾秋霞说:“嘴被打伤,两天都没吃饭。”
贾秋霞第一次来北京时,见到了禹州市局官员白中兴。经后者安慰,她感觉“像见到了青天一样”,随后返回家乡,等待当地政府处理。但后来她发现,驻京办的话不过是安慰她,当地政府根本不解决问题。
屡次三番,来北京,被关押,再来,再被关。贾秋霞也从新访民变成了老访民。
这次被送回老家后,她们不满自己被关押并被殴打,于是和一同被关押的访民专程到北京报案。为了找到关押地点,她们花了一整天时间。
5月2日傍晚,找到关押她们的“灰监狱”的大致位置后,她们前往附近的派出所报警,和数名警察一起连夜寻找关押地点。在第一个关押点,四名保安被带走,三位访民获得解救。出门时他们意外碰到了其他被关押的访民和看守人员,这样,另一个关押窝点也被捣毁。
宣判当天,北京零下6摄氏度,天上飘着大雪,天地白茫茫一片。总共七名人员被判非法拘禁罪,其中两名为未成年人。受害人和被告人的家属都不满意法院的判决,受害人觉得被判刑的只是替罪羊。被告人的家属们则认为,他们的孩子是为政府做事,不应当判那么重。
在现场的人士看到,法庭外,起初访民和被告人家属分别站在通道两边,互不往来,但很快双方便凑在一起,互相鼓励着对方上诉。有访民安慰流泪的被告人家属说:“我们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