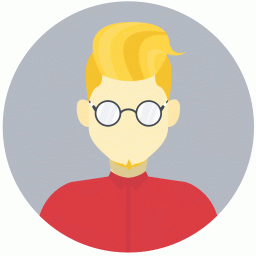苍茫天地之间流淌的灵晕
时间:2022-04-10 07:14:13
苍茫浩淼却又灵光涌动,荒寒寂寂但又灵韵流荡,墨气沉古却又白烟轻逸,荒草蔓蔓但却墨彩斑斓,其中隐约似乎还有一个孤独的生命在苦苦寻求着什么,遒劲的笔墨在激烈的呼喊之后,最终还是归于淡然,而余音却萦绕在画面上,在慷慨的放弃之余,诗意冲和,画面洋溢的轻松带给我们巨大的愉悦。
这是诗人杨键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空灵的水墨世界,那是只有长久浸淫在一个气息尚未断绝的古典诗意世界的文人,有着持久灵性经验的修行者,才可能有着如此非凡的禀赋。
诗歌与水墨之间的关系,是生命品性或情致上的关联,从王维开始的文人画,诗、书、画三者的互动唤醒了一个文人在天地之间书写的意志,元代的文人画,在画上的题诗,让文字与绘画图像的并存,在内在诗意上达到了彼此的渗透,或者平淡或者空寒,或者荒率或者秀润,一个文人要在天地山水之间书写出一种空灵的意境,这几乎成为他们的本能。只是到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焦虑,诗歌与绘画的内在关系断裂了,文人书写的生命本能被压抑,直至二十世纪末,才有所觉醒,从诗人杨健的诗歌写作与水墨绘画上,让我们看到二者再次焕发出内在的生机。杨键的诗歌写作,在日常平凡的书写中,语句舒缓,轻淡,似乎是一个低声行吟的诗人,在倾听周围世界的言说,诗人在古老桥头停驻,芦苇之间,小镇的祠堂之中,久久徘徊留恋,在古老乡村社会的余韵中虔诚地回眸,他依然能够在古老的月光与淡薄的柳丝之间发现诗意,能够在古树的浩然之气与老桥温婉的韵味之间寻找到可以摆脱时代与悲伤的局限的柔情。诗人坚决相信“枯萎的荷枝犹如古人残存的精神”,而就在《满月》一诗中,诗人写道:
满月的光辉,
瓦楞畅快的线条。
他吸收了柳树柔软的部分,
和露水里苍天的辽阔。
古典时代整个诗意的光辉都聚集于月亮,正是月光那种游动的、阅读或浏览一般的视角,似乎是月光她自身在房舍上轻轻地铭写,瓦楞上的线条就是月光自身在书写,而且既有着柳丝的柔软,也有着苍天的辽阔。柔软与辽阔,明亮与苍茫,这就是诗人杨键水墨画的内在精神,也是他建构画面意境的语汇。
古典的诗意来自于月光,那是在天上人间流淌的柔婉深情的抚慰,不仅仅是月亮与月光,而且也是月亮旁边的“月晕”:那几乎并不存在的月亮旁边的微晕,乃是幽光与气色暖昧与含混的交融带来的美感,在高处孤独闪烁,并不迷惑我们,但却让我们在难以企及之中浩然慨叹,诗歌的抒情就在于把这似乎并不存在的月晕(既是光晕也是色晕),看起来似乎是缺陷的月晕,在一次次地歌咏中无尽挽留;而水墨的所谓水晕墨章,也在于表现看起来不经意的水与墨在宣纸上,在笔触的巧妙书写之中,激发的那种渗透晕染的晕化效果。
绘画与诗歌的诗意在月晕的光晕与色晕上达到了内在契合,在一个本雅明所言的灵光消逝的时代,如果还能产生出新的光晕,那无疑就转换了古老的呼吸。而杨键对此有充分自觉,他自问诗人是否有着能力把古老的光线继续传递下去。因而,月光,既是抒发的对象,也是书写的精神材质,让宣纸在墨光的对比中,产生一种近乎于月晕的那种光晕,尽管看起来柔弱,却有着诗人自己所言的——“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挽救。”(《陌生人家墙上的喇叭花》),我们不得不感谢诗人也把这种中
国文人独特发现的拯救方式带入绘画,哪怕是清寒之家,冷落的庭院,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就是一种坦然的放弃之后,却在自然,在卑微之物上,发现了生命的柔韧,这种余让的生命伦理,这种中国文化以“审美代宗教”的独特拯救方式,它一直不为人所知,因为它并不要求我们的知晓,甚至不要求我们的感谢,这股力量如此淡然,平凡,只有在诗意的瞬间,这至善至柔的情致才会来临到我们身上。绘画与诗歌不过是挽留这种情致的一些方式。
当然,杨键的水墨绘画与诗歌的不同还在于,诗歌更为日常,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温良,舒缓与轻淡;而绘画所深入的则是一个冥想的心象世界,一个天地幻化的苍茫之境,在其间,人基本缺席。但二者共有着对人世奥秘与昏暗的关怀,画面上到处弥漫着的那股“未消之雪”的荒寒之气,也是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挚爱。诗人写雪花的句子总让我异常感动:
寂静的雪花为我们缓缓勾勒着
这个小城的暮色的凄凉,
这是我们用苦水盼来的一场大雪。
因此,画面上的雪意,对于诗人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洁净,尽管一直带有一种现代性的忧苦与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