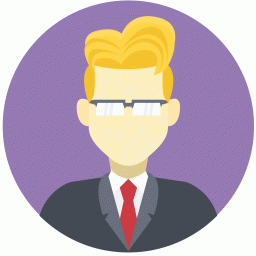征收环境税对社会分配的影响
时间:2022-03-04 01:28:47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资源存在着枯竭的危险。如何解决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国家从上世纪开始就陆续开征了一些环境保护税种,如二氧化碳税、空气污染税、二氧化硫税、能源税、燃油税等,这些环境税种的征收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环境保护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环境税开征的同时不仅会对企业投资以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而且对相关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影响。环境税对社会分配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税负的分配来实现的。环境税负的分配存在于代际之间、高低收入者和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等。国外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的征收对高低收人家庭的影响。本文将对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总结,相信对我国的环境税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代际分配效应(inter-generations distributional effects)
2006年法国的两位学者MireilleChiroleu-Assouline和Mouez Fodha在一篇文章中利用模型分析了环境税改革(即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劳动课税)。通过影响消费和储蓄在一个给定时期内对相互交迭的两代人(overlapping generations)之间造成的分配效应(他们分析的并不是两代人一生的分配效应),认为环境税改革带来的环境改善福利对两代人都是相同的,而分配效应却要根据劳动税率(labor tax rate,对企业或厂商征收,而非对家庭或个人征收)的变化而不同。首先,如果开征环境税的同时政府提高劳动税率,那么年轻一代会遭受一部分福利损失。因为环境税的开征会提高相应的消费品价格,同时劳动税率的提高也会使年轻一代减少工资收入,所以年轻一代会有一部分福利损失。老一代会从中受益,因为劳动税率提高会减少人均资本存量(per capita capital stock),从而利率提高增加了老一代储蓄折现后的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在享有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外又获得了第二重“非环境”收益。如果环境改善带来的收益大于非环境福利损失(non-environmental welfare loss),那么两代人都能获得净福利。其次,如果开征环境税的同时政府降低劳动税率,那么两代人福利增加或是损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由于环境税率提高而引起的负的价格效应(negative price effect)可能被劳动税率降低而引起的正的收入效应(positive revenue effect)补偿,最终的福利效应(welfare effect)是正的,前提是它的初始消费量不是很大。对于老一代来说,由于没有从工资提高的正效应中受益。同时又由于储蓄利率的下降使其消费价格相对提高,所以遭受了经济福利损失(economic welfare loss)。
二、在劳动者和失业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的分配影响
很多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都降低劳动税率,但失业者并没有从降低劳动税率中(这里的劳动税率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征收的企业为其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税,而不是对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征收的所得税)受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税收负担。但是,他们要负担环境税,环境税的征收实际上把税收负担从就业者转嫁到失业者身上。在许多OECD国家,长期失业主要发生在低劳动技能(Low-skilled)工人(这些工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劳动技能很低,因此频频失业,形成“失业陷阱”(Unemployment Trap)现象)身上,低劳动技能又造成低收入。由于税收制度、社会保障金、价格补贴收入等的相互作用,使低劳动技能者所面临的有效税率特别高,于是税收负担又从高劳动技能者转嫁到了低劳动技能者身上(Bovenberg,1995)。
三、对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分配影响
能源税或碳税等环境税的征收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提高,实际工资的下降。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等。OECD在其1995年的报告中提出碳税具有轻微的收入累退性,其税负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承担,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在家用能源和交通燃料上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或总支出的比例要比高收入家庭高(0ECD,1995)。
但是,学者们对于这个累退效应是否存在及存在强度大小进行了深度的实证研究,并且针对不同国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比如,Smith(19921通过计算英国按$10/桶石油征收碳和能源混合税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分配效应后得出,占总样本20%的最低收入家庭每星期支付的额外税收为1.45英镑,最高收入家庭为2.95英镑,中等收入家庭为2.21英镑,分别转换成这些税收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则是2.4%、0.8%和1.4%。所以,他认为这种能源和碳混合税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负担要比高收入家庭重很多,明显具有收入累退效应。Poterba(1991)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对美国如果按照$100/吨碳征收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计算后得出,样本中收入最低的一部分家庭要支付的额外税收占其收入的比例为10%,而收入最高的一部分家庭比例仅为1.5%,这也说明了碳税的收入累退性。Hamilton&Carnemn(1994)和Comwell&Creedv(1996)分别对碳税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后也发现了累退的结果。Barker and Kohlerfl998)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家用能源(用于取暖、做饭、照明等)与交通燃料区分开,并且把征收碳税的动态效应考虑到模型之内,即假设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具有弹性,所以碳税的征收会导致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最后他们得出在大部分欧盟国家对家用能源征收碳税会产生一定的收入分配累退效应,对交通燃料征收碳税会带来比较弱的收入累进效应,总的来说,征收碳税带来的收入累退效应很小。Speck(1999)也认为,虽然碳税或能源税具有一定的收入累退效应,但这种效应相对来说很小,而且效应大小还要看税基(比如对家用取暖燃料、交通燃料等)以及改善了的环境质量对不同收入人群带来的收益大小。
即使在欧洲国家之间,环境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也不同。对此,一些学者也专门做了研究。比如,Symons等(1997)利用一个静态模型分析了CO2税和能源税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产
生的收入分配效应。他们的分析没有考虑税收返还或补偿带来的影响,并且把技术水平和家庭预算固定在一个水平上。研究结果表明,CO2税和能源税在德国和英国具有收入的累退效应。在意大利的累退效应较小。在西班牙则是轻微的。他们分析西班牙累进效应的原因是家庭在交通燃料方面的支出比较大,而对交通燃料征收环境税会产生收入累进效应,这一点正好与Barker and Kohler的分析一致。Smith(1992)和Pearson(1995)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他们对多个欧洲国家碳税和能源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后发现,英国和爱尔兰的累退效应比较明显,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基本上不存在累退效应,甚至还有一点累进效应。在最近的研究中,Tiezzi(2005)证明了碳税在意大利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明显的累进性,而在Wieret al.(2005)对丹麦C02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中发现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
正是由于环境税征收有可能产生的收入分配累退效应使其开征受到了多方面阻力。为此,OECD国家采取三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使这个效应最小化。
一是征税前的减免税来减轻劣势群体的负担。比如对低收入家庭使用的取暖燃料等必需的能源降低税率,对收入水平在制定的标准以下的家庭免征相关的环境税等。荷兰于1996年1月开征的管制能源税(reg,ulatory energy tax)就考虑到对收入者分配的影响而设计了免税标准,即对年消费在800立方米煤气和800千瓦小时电力以下的家庭免税,后来在2001年取消了这个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对低收入家庭采用降低税率的方式,还免除了低收入家庭的市政垃圾收集和排放税。
二是征税后的补偿措施,包括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等。比如,瑞士把对VOC和轻燃油征收的硫税返还给了家庭。2000年,挪威按每千瓦时0.025挪威克朗对家庭用电征收的电力税收的三分之二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中的扣除返还给了家庭。但是,这种补偿机制会降低环境税征收的环境有效性,即影响家庭节能的动机,所以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通过对家庭节能投资或支出进行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能源税返还。
三是减少对收入和劳动的课税。低收入家庭一般支付较低的收入所得税,不如高收入家庭从收入所得税降低中获益大,所以这种措施非但不一定能减轻环境税的收入累退效应。甚至还会加深。这一点在Metcalf(1998)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Metcalf模拟分析了美国实施一个收入中性的环境税改革的效应,改革措施包括按$40/吨碳征收碳税、提高机动车消费税、垃圾处置税以及对SO2和氮氧化物征收的排放税,这一揽子改革措施使政府收入增加了10%,然后政府把这些增加的收入通过降低收入所得税率和社会保险金的方式返还给纳税人,却出现了收入分配累退的结果。Metcalf又分析了把政府所得的额外收入返还给低收入群体的方式,最后发现收入累退效应被抵消,甚至还出现了一点收入累进效应。
所以,在评价环境税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应该考虑到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的补偿措施带来的影响以及环境税产生的环境收益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分配。比如,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大都居住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所以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改善收益对他们来说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