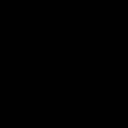汤一介:大时代下的一介书生
时间:2022-10-29 05:24:24

乐黛云为丈夫写下的挽词是:
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
――你的小黛
2014年9月9日,哲学史家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消息一经公布,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国学泰斗”、“国学大师”、“哲学家”等名头被加在汤先生的名字前面,虽是出于尊重,却违背了逝者的意愿。
汤一介生前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不过我仍可,至少我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我想,活着就应该不断地想问题,生活才有意义。”
比“哲学家”更令汤一介反感的称呼是“大师”。他曾多次说:“我们没有提出一套理论,让世界上都承认,你现在研究学问往往用的还是西方的理论,你说我们谁的理论拿到国外去,大家都承认,没有,所以没有大师。”
也许,遵从汤先生的意愿,不去仰视“大师”的风采,而是跟随他的脚步,在他的人生轨迹中追悼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对汤先生最好的纪念。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为其取名“一介”,是“一介书生”之意,而汤一介的一生不忘“书生”的本分。
不是天才
汤家可谓世代书香。太祖父正谊公,一辈子都在湖北黄梅乡下教书,最引以为豪的是教出了三个进士,其中一个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后,汤霖做过几任知县,后赴甘肃任乡试考官,又参与创办新式学堂,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去接受新式教育。汤一介没有见过祖父,但牢记其留下的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霖还留下了一张刻有自己名字的进士碑拓片,那块代表读书人最高荣誉的进士碑至今仍立在孔庙内,只是字迹已经模糊了。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1893年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辛亥革命后考入清华大学,1918年赴美留学,后转入哈佛研究院,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汤用彤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1927年,次子汤一介出生了。
虽然生于学者家庭,小时候的汤一介却似乎没什么读书的天分,小学时成绩平平。1937年,国难当头,北京沦陷,汤用彤带着长子汤一雄先去了昆明西南联大。两年后,妻子张敬平带着自家的三个孩子和北大教授邓以蛰的两个孩子一同经天津、上海、香港、河内,几番辗转才到达昆明。邓家的两个孩子即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他的姐姐邓仲先。
当一家人终于团聚,汤用彤才告诉妻子,长子汤一雄病逝的消息。离乡背井、丧子之痛,大人的痛苦少年汤一介并不完全能够体会,只记得父亲常常会在床边一边抚着他的头,一边吟诵着“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记忆中,孔尚任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一直是父亲最常吟诵的篇章。
汤用彤将家安置在昆明附近的宜良县,周围邻居多是西南联大的同事。汤一介则进入了宜良县立中学读初一,一年后全家搬到昆明,父亲安排他考联大附中。结果,汤一介的成绩很不理想,只能复读初一,这算是他求学生涯遇到的第一个打击。但是课堂之外,汤一介的表现却是格外“出色”。他和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儿子闻立鹤、闻立雕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探险”,有一次还在山上点起了大火。
读初二时,汤一介闯了一个更大的祸。他曾撰文回忆道:“那时我和余绳荪(余冠英先生之子)、游宝谟(游国恩先生之子)、曾宪洛(曾昭抡先生之侄)还有胡旭东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们看了《西行漫记》,觉得延安很不错,就想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余绳荪查了地图,确定了路线,他们决定每个人从家里偷点黄金作路费。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块金表还有一块刻有父亲名字和《清华周刊》总编辑字样的金牌。“但是由昆明到了贵阳后就被当地的警备司令部抓住了。当然我们不敢说要去延安,说是因为对联大附中不满,想去重庆念书。可我们还带着一本《西行漫记》呢!如果这本书被查出来,我们会有很大麻烦。幸好当天没有搜查我们的行李,而把我们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这小屋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了。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后来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最后把我们遣送回昆明了。”
“延安梦”破碎了,联大附中也待不下去了。汤一介被送往重庆南开中学读书。那里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汤一介写信向父亲抱怨,父亲在回信中说:“现在正处在抗战期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艰苦,所以你不要对此有什么抱怨。”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儿子,对他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寒士。”尽管在信中措辞严厉,但是汤用彤还是偷偷地寄钱给汤一介在重庆的堂姐,请她买些猪油给汤一介拌饭。
汤一介在南开中学与同学一起创办了针砭时弊的刊物《文拓》。他曾写文章《一滴汽油一滴血》批评达官贵人用汽车送孩子上学,痛骂他们是王八蛋,结果被反骂为“汤八蛋”。《文拓》后来被迫停刊,汤一介再次惨遭留级。苦闷的汤一介选择回到父母的身边,汤用彤只好把他送到西南联大先修班做一名旁听生,并亲自给他补习文史课程,又请钱学熙教授帮助补习英文。
2004年,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汤一介说:“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第一流成绩的人。”
革命青年
虽然在学校的成绩不佳,但一直以来汤一介的阅读量非常大。中外小说、文史典籍、佛学著作均有涉猎,遇到不懂之处,父亲总是耐心为他讲解。父亲身上的“美国留学的儒学之气”深深地影响着他。
同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都是相似的,而决定他们命运的往往是家人的态度。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汤一介都要被关在哲学楼二楼接受审问或者写检查,往往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当汤一介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楼门,都会看到迎面走来的妻子。因为担心汤一介会被突然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乐黛云每天夜里坐在哲学楼外的石坎上,等待丈夫。
1969年秋天,长女汤丹要去东北插队,汤一介和妻子、儿子则被派往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改造。临行前,一家人在北大照了张合影,难得的是四人都面带笑容,不管外面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们的家庭始终是温暖的。
晚年治学
1980年,汤一介终于重返讲台。他开讲的第一课即为“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方面是汤一介在继承和发扬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哲学研究道路上一个新的探索和突破。
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说:“一听说汤先生要讲‘玄佛道’,学生们都争着来听课”。李中华记得开课那天,他提前从家里跑步赶往教室,但一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座位也没有,就是可以站立的地方也很有限,他与同学开玩笑说:“听汤先生的课,痛感无立锥之地。”最后只好换教室,还是坐不下,再换教室,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说听汤先生的课,有如参加一场思想理论和学术的盛宴。
汤一介曾回忆:“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周一良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国内外著名史学大家。耗时三年完成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是汤一介对中国哲学界的又一贡献。
1984年12月,汤一介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他说:“大家希望我来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兼容并包’。所以我联系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也有李泽厚、庞朴,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有自由的讨论环境,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成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儒藏》是一项集录中国历代儒家思想文化经典的浩大工程。汤一介曾撰文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历来是儒、道、释三分天下。但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就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却唯独没有编出过《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中国在历史上对《佛藏》、《道藏》的编纂是靠寺院经济支持做起来的,但中国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它没有寺院经济,因此,《儒藏》应该由国家来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具有现代的科技手段,这些不仅提供了以前达不到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还为大规模地整理和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虽然主持《儒藏》工程,汤一介并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他说:“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中包含着某种走向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的可能性。”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为汤先生撰写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对汤一介一生追求古今中西文化融合做了生动概括。
乐黛云为丈夫写下的挽词是: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你的小黛。
(参考资料:李娟娟著《汤一介传》、汤双《燕南园童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