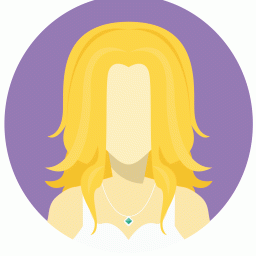用肥皂当触发器的Goele
时间:2022-10-02 02:08:21
比利时艺术家Goele De Bruyn受米念(米念是一个大本营设在厦门的艺术与设计团队)之邀于7月8-16日 在北京开展“安特卫普的肥皂剧”艺术计划。在这期间,Goele将走街串巷收集北京居民洗澡后剩余的肥皂,最后结合她专程从比利时带来的代表作品Soap,于7月16日在米念(北京空间)进行展览。
Goele出生在离安特卫普不远的一个村庄――布莱切特,后来她去了安特卫普上学,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生活。她很喜欢安特卫普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环境和氛围,也喜欢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的艺术家,并且她一直以住在鲁本斯小镇而自豪――她喜欢鲁本斯运用色彩的方式,喜欢他的精湛技艺和作品中的愉悦感。Goele的母亲是一位陶瓷艺人,一直在艺术方面给予她很多支持,后来Goele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开始了解当代艺术,她喜欢的艺术家有瑞士艺术家Peter Fischli&David Weiss、Pipilotti Rist、Roman Signer,比利时艺术家Michel François & Ann Veronica Janssens,美国艺术家Jimmie Durham、Mike Kelley等。有一次Goele在欧洲陶艺中心(EKWC)认识了米念的艺术家侯嘉文,聊得很投机,也促成她如今第一次来到中国做作品,本刊特别对Goele进行了采访。
Q:为了收集这些肥皂头,你去了欧洲很多国家吗?现在收集到多少了?
A:我平时向我的朋友和我遇到的人收集这些肥皂头,所以基本都是比利时的肥皂,另外,加拿大也有一个人为我收集。现在我手头约有360块肥皂头。
Q:为什么你只要用剩下的、小得几乎不能再用的肥皂?
A:它们是残留物,是使用者用手“雕刻”的剩余肥皂,因而带着他们的痕迹。这些肥皂也可以被看作石头,放在一起的时候像考古遗留物――而实际上它们确实如此,这些东西就像人们的工具。这些肥皂像其他任何残留物一样令人感觉很脏,但同时因为它们是肥皂,所以又会令人觉得干净。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在分析事物的很多层关联。我尽量从颜色、形状、质地等各种角度来排列它们、来寻找它们的之间的关联。
Q:在过去10年中除了做这个项目你还从事其他项目和工作吗?
A: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也教书。简单说,向别人讨要一块肥皂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人们使用一块肥皂所花的时间却要长得多。我从1998年开始跟别人要肥皂,2010年我才第一次做了跟肥皂头有关的展览。
Q:当你上门去找人家要肥皂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什么表情?有什么好玩儿的故事吗?
A:其实只是在北京我第一次这样挨家按户上门去找人要肥皂,以前在比利时我从没这么试过。这确实是个很好的经验,人们的反应都各不相同:有的人很耐心地听你说,有的人一声不吭,还有的人觉得像听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有的人很友善地开始说自己的故事,并邀请我们进屋。这个时候,肥皂就像一个触发器,使得人们开始交流。我第一次做肥皂头展览的时候,邀请了所有给过我肥皂的人们,他们在现场彼此交谈,说起有关的故事。
Q:你最初怎么产生这想法的?
A:我做作品时常常使用去污的材料,比如清洁剂或者砂纸。我认为材料是理解一件作品的切入点。带有清洁和去污性质的材料代表一种功能,其实每件东西都像是一个多重功能的综合体,有点像做数学题。为了做一个作品,艺术家得知道他为什么要做以及从作品中他能得到什么。当你用一种特别的材料来做作品的时候,你会在其中找到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联。以前我曾经用肥皂做过一个雕塑,这个收集肥皂的想法应该是从那时候蹦出来的。对我来说,创作来自思考和感觉,是一些特别纯粹的想法和感知的混合体,这些东西对创作者来说必须是纯净的和诚恳的。
Q:你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A: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我的作品就像是我思想的残留物,像我为了找到回家的路而扔在路上的石头。我更喜欢在一个场景里去表达,通过我所创作的物品――其作用如同戏剧中的演员。我感兴趣的是,由艺术和物品综合产生的作品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凝聚人群。我也思考人们怎么看他们自己的美学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怎么把美的和丑的东西并置在一起――我把这套有关想法称为“安慰机制”。
Q:接下来你还有什么工作计划?
A:8月底我在比利时还有一个艺术项目,到时我将展示一个类似会移动的光源的互动作品,将有一束从树木空隙中射下来的光,就像人们通常在森林里见到的那样,当人们靠近这束光,它就会慢慢消失。实际上他们靠近的是一个家用圆形吊灯改装而成的装置发出的光,像清冷的月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