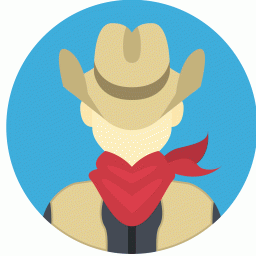士.世风.政风
时间:2022-10-01 04:10:20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是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振翔教授写的一本学术论文汇编。虽说是汇编,前后却也自有联系,代表着教授的学术观点,看了他的论著,结合我个人这多年来所历之世事、所思之疑虑,成此文,献给读者。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有自序和《竹林名士交游考》《读(藏书纪事诗)》《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等四篇学术论文。在自序中,作者言道:“其中《竹林名士交游考》与《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两文较有分量,所以我就参照这两篇的题目为这本论文选取名《竹林名士与陈寅恪》。”作者说,虽然竹林名士与陈寅恪相隔了一千六百多年,但由于陈寅恪先生对魏晋清谈、竹林名士等问题的考究,而他正是靠陈寅恪所指引的方法与途径结合他本人对魏晋史料的研究,较为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了二者,故得此书名。
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知名学者,蔡教授也给研究生上课,开设的课程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听他的课是一次思想的旅程。至今回味起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马寅初、周扬、巴金、陈垣、金岳霖、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人,一个个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彰显一时而他们的命运又无不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紧紧关联着的人物,在蔡教授的讲授中,活生生地再现在我们研究生面前。蔡教授既有讲述他们的生平,又有点明他们各自的观点,对有的人只是寥寥数语,就点明了这些名家的观点及其政治态度,对有的人则点下了浓墨,重重地描上了一卷生动的人物连环画。这个人便是――陈寅恪。
在给我们讲陈寅恪之前,蔡教授先给我们介绍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来源和定义。蔡教授说,其实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舶来品,一个来源“源自于东欧,主要指得是19世纪俄国的一批归国的留学生。俄国人讲的知识分子专指这批从沙皇专制统治下落后的俄罗斯到社会相对昌明的西欧留学回来的学生,他们主张用西欧的社会思想、民主政治、生活方式来改造当时落后的俄国;另一个来源出自西欧,特指1898年以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批人,针对当时轰动一时的德累福斯案,写了《我控诉――为德累福斯鸣不平》,斥责官方的黑暗、民众的冷漠,他们与德累福斯案的主角德累福斯没有半点社会关系,完全是出自社会的良知,站出来为社会上这些蒙受不幸的人、为遗落的社会良知而叫屈、而鸣不平。作为知识分子,“不仅在于读书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必须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他们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情。而经常喜欢对时政和社会发出一些批评性的言论,就是西方式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点”[1]。按西方的标准,知识分子指得是这些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脑力劳动者。这个词在引入中国后,被泛化为读过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蔡教授说:“他们只能称为文化人。”按蔡教授的说法,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呆在实验室做试验的人可以称为学者、杰出的科学家,而不是知识分子。
在分析完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区别后,蔡教授回顾了建国后中国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说1952年所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实际上是将原先的欧美式的教育模式变成苏联式的教育模式,改变了过去培养通才的办学思路,培养出来的只是懂得某一方面知识或技术的工具型的专才,而不是培养有知识、负责任、高素养的公民。更为要命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生活用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控制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而户口制、档案制和个人单位所有制则限制住了人身行动自由,“计划的经济只能导致计划的思想”。蔡教授语:“文教科卫等部门全都行政化、机关化,知识分子实际上变成了国家干部,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是在行政命令下进行的。”
蔡教授介绍了蔡元培、傅斯年等学术界的名人,正是这些学者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使得北京大学和后来的台湾大学成为中国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府,在这两所大学里,人才荟萃,鸿儒云集,各种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产生出中国学术上一片百花齐放的少有景观,结出了硕硕累果。陈寅恪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在此学术自由的背景下产生的。当然,陈寅恪另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但那是以一种相当隐晦的手法写就的,乃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无奈之选。像《论再生缘》当时陈寅恪只是自费油印了一百零五本,托人带一百本到香港,“1958年,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上发表了《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陈寅恪读后,曾感慨说:“作者知我。”[2]这也从反面说明懂得陈寅恪当时写作思想的人并不多。写《柳如是别传》似乎有悖于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作为一个文史大师、一个研究隋唐史的大家,陈寅恪应有更重要的课题去研究,却为一个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妓的身世考证花了十多年的工夫,耗费晚年的诸多心血,颇让人迷惑不解。其实,陈寅恪正是“通过考证陈端生与柳如是的身世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表达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强烈愿望,抒发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热烈颂扬”[3]。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碑文时,写下“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字句来表达他自己的心声。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已非昔比,批斗之势风急雨骤,稍不留神便会惹来灭顶之祸,凭一个学者的良知,对政局的变化又是不吐不为快,故此,只能以撰写诗词和考据历史事实的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这里,我只是简略介绍了陈寅恪晚期的思想,对他的轶闻趣事就不再详解了,有兴趣的读者自会寻书细读。我读完此书,深有感触的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舞台上将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稍微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便会知道,但凡乱世期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之时,便是中国思想最自由、学术最繁盛的时候,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以及近现代的外辱侵华、民国动荡时期,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和流芳百世的学术巨著,反而是在思想大一统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湮灭了,万马齐喑,百派萧条。
我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没做什么深入的研究,也不敢发一些独到之见解,只是稍微翻阅史书,知道魏晋年间有玄学名士阮籍、稽康等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在司马氏以“名教”卫道士身份实行高压政策,镇压异己时,拿起老庄玄学的武器,以藐视礼法的行为进行消极对抗,他们以大胆的理论和行为揭露当权者鼓吹名教的虚伪,在讥评时事、臧否人物、扬清抑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对世风的扭转、政风的改进,功不可没。在世人“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奔走于道”的世俗社会里,在官本位、权钱交易的陋习与俗见下,倘若有那么一批不为名、不为利,关心民生国事,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驱使,能撇开个人身世荣辱,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一点有功于当朝后世的、不负学者良知的益事,便无愧于“士”的称谓了。
注释:
[1][2][3]蔡振翔:《竹林名士与陈寅恪》第242、236、250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