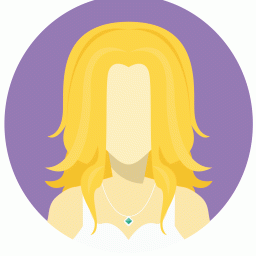奔跑的蔑匠
时间:2022-09-27 04:41:15

1
我记不清楚,怎么走到那间空屋,又辗转走到屋前的那片空地。我和一群亲友,男人和女人,坐在刷过桐油的竹椅上,谈些故乡的事情,牡丹牌香烟、茶、啤酒,永无休止的谈话和酒精,将眼前的光景变得一片烂漫。后来,我竖起衣领,在寒冷中想象,遥远的雪地里是什么东西在奔跑?
1996年小镇的冬天,寒雨连绵,在黯淡的光线里,黑板上的字迹模糊一片。回想起来,彼时的课堂就像一个背景(好比一个空旷的剧场),一位穿墨绿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带着一个瘦弱的少年,站在黑洞洞的教室楼道门口。寒风中,那位中年人带着一股旷野的气息。作为记忆中的事物,我依然记得那天昏昏欲睡的课堂和这对父子所带来的奇异的新鲜感。后来,我在罗伯特・卡帕的摄影集中看到海明威带着小儿子格利戈里,我总会想起那天寒风中一老一小的模样。他们刚从外地迁居于此,与外祖母家相隔不远。我总在周末的时候,不请自到,与我新来的同窗分享一枚刚从树梢上摘下的桃子,我还记得一只黑猫从碧绿的草丛中走来,阴郁的屋檐下,一种缓慢而悠长的潮湿,被阳光的利刃割破。
他有着一副硬朗的容貌,年近四十,却很少皱纹,我很少看到他的笑容,好像在某处见过一帧照片,意气奋发的少年,笑容完全被一种不加遮掩的愉悦心情所打开,而不是蜷缩的、惊恐的,像燃烧时的报纸。正午时分,一道阴影透过破旧的玻璃门,斜斜地落在他的脸上(我记得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一个镜框,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照片)。也许,在大多数的时候,这样的笑容是被漠视的,那个从遥远的年代走过来的年轻人,他满怀梦想,却一头扎进岁月与时代的洪流中,无法自拔。太多的喜怒哀乐被大量复制,末了连那笑容仿佛是被预设的,偶尔在闲谈中瞥见一两回,似乎总带着一丝悲苦与忧伤。
如果你曾在南方的某个乡村生活过许多年,那么总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永远留存在你的脑海里。比方,河流中的游鱼与白鹅、屋前晾晒衣服的麻绳以及屋后苍翠的竹园。它们构成了一座村庄最基本的事物。我们曾经怀着无比安闲的心情在竹园里游戏、看书或者观察河面上浮游的生物,我还记得外祖母竹园里幽凉的石板,那是一块被外祖父捡来的废弃的残碑。我和我的同窗坐在这里一起分享从家里偷来的半包瓜子、一支墨绿色的钢笔、一只钉书机、撕去一半的台历、过期的报纸、抽空的磁带盒、两个不锈钢杯子、一卷透明胶带、一串生锈钥匙、永远不能凑全的扑克牌和豁口的烟灰缸等。春雨潇潇,掩去我们游冶的足迹,却诞生出一簇簇鲜嫩的竹笋。它们令你想到杨万里、冯至的诗句或者废名的小说。每年秋天,外祖父会砍去部分成熟粗壮的竹子,出售给那些制作渔具的人或者如我同窗的父亲一样的篾匠。我们当然想不到这些大片的竹子对于篾匠意味着什么,竹园在河边静静地虚掩着门,更符合记忆中它的形象。
众多由竹子所编制而成的器物,被置于外祖母的厨房、餐桌、卧室内,最常见的是暖瓶的竹壳、装米的筲箕、乘凉的躺椅、竹席、放菖蒲或者花生的篓、捕鱼的罾、光亮的床榻等,它们被阳光粹取了绿色,光滑、细致、柔腻,经久耐用,隐隐中透出久远年代的幽凉。如果仔细观察,才会觉察出那位篾匠艺人的高超手艺,他会在暖瓶的竹壳上编织出图案,惯常的是蜻蜓与草地,筲箕的缝隙绵密而紧致,筛、筐、篮、罾,莫不如是,我甚至见过一块竹匾,上面用隶书编织成“积善庆余”的字样。这些竹器在清贫中散发着一种超脱的味道,就像我曾见过这位同窗的父亲,他将一根根竹丝,绣花一样,穿针引线,成为一件艺术品。然后,在一种满足与自豪的沉默中,他慢慢地点燃一支劣质的烟,用一种的怜爱的眼神,端详这些器物,那神情辽阔而自满,仿佛忘记了贫穷、艰辛、各种岁月强加的压迫以及无边的冷漠。那些竹器在他眼中镀上神性的光芒,它们穿透未来的时光,曲折往复、循环不止,让我想起岁月中一些恒常的风物与习俗,在很长的时间内,你会觉得岁月没有丝毫的改变,就像一种性格,绵长、恒定、久远。
2
也许,我所怀恋的是一种不可复现的生活方式,它触手可及又虚幻无边,它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它的隐秘之处,就在于似乎总有一个幻觉,一个来自于岁月深处的回音,它肯定不存在于书本中,也不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里,而在村庄的遥远的隐痛里。
如果不是由外祖母转述,我无法想象拥有如此技艺的这样灵巧的手,会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丢下竹具,抽出皮带,拿起农具,走上村头,高喊口号,那日夜喧腾的声音,惊起夜归的鸟雀,惊醒冬眠的蛇,它们难以想象,竹园外的那些人为何如此不安。一个下午,我同窗的父亲以及他的众多伙伴们,反复揪斗一名开设碾坊的富农,血液飞溅在曾被纳博科夫称为“中国圣树”的银杏上。我立刻想到去年还曾在江边的那些银杏树下拾取掉落的果子。旁边是一排排茂盛的桑树。风过之处,那簌簌的响声,令人不寒而栗。此后,我很少在那里逗留,曾经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的疯子,从江边猛地窜出来,用一双鱼眼,充满怒气狠狠地瞪着我。他让我联想起那位死去的碾坊主人。
若干年后,一个衣服褴褛的女人送回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从劳改农场返回的篾匠,带着这个孩子远走他乡。直到九六年,那个寒雨连绵的冬天,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出现在眼前。
那个充满悲哀意味的女人最后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令我着迷的是,她竟然是一位画宣传画的女知青,油彩、水彩、炭笔是她的表达方式,许多、雷锋的画像就出自她看似柔弱的纤手,还有诸多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炼钢工人、战士或者女民兵。在仅存的一件充满霉斑与蛀痕的画上,我发现画中那位女民兵,竟梳着两条长辫子,脸色如朝阳,鼻梁挺拔,英姿勃发,可是那双手,却画得像现在我们眼中女明星的手,白嫩、细致,姣好。值得一提的是,背景上那些雪松画得真好,阳光从雪松的尖顶倾泻下来,令人想起伦勃朗笔下的光芒。某种意义上,我的记忆中她的形象就是宣传画中女民兵的形象,庄严而又柔弱,娇媚中含着一丝高贵,有种远离那个特殊年代的耐人寻味的气息。在我眼里,她成了宣传画的“产物”。
某个溽热的夜晚,我在看让・雅克・阿诺拍的《情人》的时候,忽然想到了那个女人。“岁月匆匆,锦瑟难寻,我在十八岁时,我就觉得老了。那年我十五岁,乘船过湄公河,轮渡的笛声由天外传来……”,我不知道这两种形象为何会重叠起来,也许是因为浑浊的湄公河上,令人忧郁的刺目的阳光。有段时间,我总去乡镇电影院前徘徊,门前那些水彩的电影海报,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鲜艳无比。相对而言,那用色与笔法要落后得多了。院内的一排排雪松,落下寂寂无声的墨影,仿佛下面埋着一颗早已苍老的心似的。
我曾经无数次揣测这个女人的各种去向:第一,她受丈夫的牵连,遭遇惨酷的报复,精神最终崩溃,像所有患有疯癫症的人那样,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有位好心人(也许是另一位同病相怜的贫苦的女人)收养了她,并帮她产下了孩子。第二,她并未远走,一直隐藏在某个废弃的窑洞里,直到诞下一子,然后在绝望中离开。第三,在某个炎热的夏天,她悄然随一位云游的货郎,离开了本镇,最终落户于遥远的异地。
或许,我们可以从篾匠那撕去半边的日历上的模糊字迹,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今天她一直在画那张炼钢工人,画得很好,虽然我们其实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炼钢工人。记得上次,我们砍了许多树,支起大锅,土法炼钢,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几块褐色的铁疙瘩。她总是向我抱怨,吃不饱,没有什么力气,画出来的的英雄,也像吃不饱的样子。……这几天温度太高了,站在太阳下吆喝一群人,真有点吃不消。手不小心还被刘大家的红木柜子压出一块血泡。晚上等老于走后,从食堂偷偷带了几块饭锅巴,一直藏在裤兜里,带回去给她。她笑得像门口的那朵丝瓜花。……今天在镇上的桥口,见到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乍一看,似乎有点像她。可等我去找她的时候,她却消失不见了。……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所有那些被认为永久之物,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今天领了一点工资,花了五角钱买了点肉,想要包一顿饺子。四妹走后,我唯一的抱着虚妄的念想就是,也许我们还能再见一面。
3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有十年,也是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竹子的包围中度过的。这里没有北京时间、东京时间、巴黎时间和纽约时间,这里永远是下午。我们把孤寂的心,交给无聊的永逝的河水,把课堂上的书本抛在脑后,把趣味留给自我发明的游戏。维姆・文德斯在《一次》里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记忆中片段,或许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存在的就是那些“一次”,在不同的时候,这些“一次”的颜色也是不同,虽然它是个人化的、碎片的,而当这些“一次”闪现的时候,几乎都是特别的刺眼,犹如正午直射的阳光。
一次(也许是我唯一的一次),我遇见一个同窗的死亡。那个灰色的早逝者,像一缕褐色的云,从我们年幼的头顶飞过。我记得那个孤寂的午后,白花花的阳光令人昏昏欲睡。似乎所有乡村的午后都是这样,细微的风拂过半干的布衣衫裤,动物都藏在树荫下打盹,竹影斑驳,流水静卧于温软的河床,那宁静的影调,令人感觉整个村庄仿佛也是慵懒的。如果不是尖叫声和忽然忙碌的人影,我早已跌入沉沉的梦境。抬眼望去,广阔的天空下,一只用桐油刷过木船,迅速划至岸边,人们从上面抱下一个满脸淤泥的女孩。她是邻村驼背木匠的女儿,智商似乎不正常。这个慵懒的下午,她没有选择从河边的大路走,而是钻进了满是芦苇的细细的圩岸,结果不慎滑入了这条河最深的地方。她那同样弱智的母亲,抱着小小的尸体,失声痛哭。一只红头的苍蝇落在她那满是泪痕的脸上。我感到讶异的是,救人的竟然是那位篾匠,他反复在河中央捞了许久,当他拖着人靠近岸边的船沿的时候,几乎没有气力了。我至今记得他那一脸惊恐的表情,和他昏倒在地,满口吐出的污浊的黄水。
一次,篾匠的儿子偷偷在我的耳边说,他喜欢村里那位穿着的女教师,常常趴在她卧室的后窗口,偷窥她睡午觉的样子。他在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时候,口干舌燥,双手发抖,写在他比我大两岁的通红的脸上,我却感觉有种神圣的意味。那时候,我们刚刚走过那位女教师的家门口。屋内黑的,像一口深不可测的黑洞,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在正午的阳光下走了许久的缘故。女教师穿着花格子的连衣裙,落落大方地从里屋走出来。忽然,我的同窗,像匹受惊的野马,仓皇地飞奔起来。
一次,我和同窗正躲在竹园里午歇。篾匠寻了过来,他满脸的怒气,挥舞着颤抖的手,要去揍他的儿子。而我那位同窗轻而易举就从篾匠的手底下逃走了。自从上次从河中捞出那具幼小的尸体,篾匠仿佛被鬼魂附体,先是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接着出现后遗症,双手颤动,不听使唤。他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衰朽的气味,冷漠、不安,催人逃离。不再有人请他编制竹器,事实上,他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个儿子。他变得越来越自卑懦弱,那天在竹园中,他看着一颗颗新鲜的竹笋,欲言又止,脸上露出犹豫,好像匆匆地掠过了什么,也许是令人震撼的言语。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看到村里的一位姓朱的渔夫,一脸兴奋地奔走相告,他抓住了这些天在村里流窜作案的贼。他下午捕鱼归来,听到房内有声音,知道有人行窃,他蹑手蹑脚地立刻将房门反锁。此刻,偷东西的人正被他锁在屋内。这桩大肆张扬的抓贼案,让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我们都很兴奋地围着他,村长放下手里的摘的棉花,也跟了上来,人越聚越多,最后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乡镇派出所。我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隔壁的修锅匠说,当年揪斗一名反革命分子,也没有这么热闹。远处的竹林在风的吹拂下,发出一阵阵的声音,那是在一种阳光下发出的黑色的声音,竹林湮没了它,但它在黑暗中涌动。最终,在两名派出所民警的命令下,门被打开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贼,让所有人都大为惊讶,他竟然就是篾匠的儿子,那位偷窥女教师午睡的我的同窗。他立刻被戴上锃亮的手铐(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见到真的手铐),在众人的奚落声、惋惜声和叹息声中,带上了警车。后来据说,他在派出所被狠狠拷打了一夜,交代了所有的不法行为,包括过去偷窥女教师的细节等等。
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树木和落日使得那些乡村道路变得无比的柔和。斑驳的人影和我那一脸迷惘的同窗都消失了。我讶异的心情逐渐平静,仿佛一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似的。在竹林的一片片的摇曳声中,我仿佛获得了一个少年对岁月的重新体认,一份在内心不断擦除、不断修改的生命版图。
后来,我们离开村庄越来越远,更多地在城市的树林里徘徊、流连和观望。那个安眠在竹林、树木掩映深处的村庄,消失了,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过往。在这个冬日无所事事寒冷的下午,我仿佛看到那个在漫天的雪地里奔跑的人,也许就是那个带着一身疲惫的篾匠,天色黯淡,雪落四野,他从黑色的雪地里,远远地向我们靠近―也许,那是你我对岁月一息尚存的热情:我们都不想沉默于平凡的生活,而我们同时又多么害怕无依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