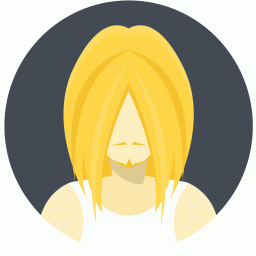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刑法父爱主义之提倡
时间:2022-09-13 10:29:44

摘要:从价值论上分析,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分别倚重自由与秩序,前者立足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因主张刑法在法益保护上只能作为最后手段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后者则侧重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从而规定了大量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犯罪,存在着权力过度扩张的风险。基于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的需要,中国刑法应当倡导一种父爱主义立场,以求刑法干预能够在谦抑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其中,二元化犯罪模式即是这一立场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二元化犯罪模式;刑法谦抑主义;刑法工具主义;刑法父爱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20-009
一、问题的提出:从理论与实践间的裂缝切入
在法律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思考中国法律的“世界观”之同时,还需要通过自主的努力,融入并对域外法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实现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法学知识转型。其中,关系到一个中国命题是,中国刑法应该坚守什么样的刑法立场,并以合理的犯罪模式予以体现。对此,有两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刑法谦抑主义,即立足于自由保障,主张刑法应该保持谦抑精神,正确处理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反对立法中的犯罪化倾向。二是刑法工具主义,它立足于秩序维护,主张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社会治安不好时,需要强化一种重刑主义,这就包含着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重刑化的倾向。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往往运用发端于德日的刑法谦抑主义立场去反驳刑法工具主义,并成为学界公认的评价刑法上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重刑化与轻刑化的标尺。以致97刑法颁布之后,随着刑法修正案的频繁颁布,更多的学者把刑法谦抑主义运用到犯罪化的否定分析中,比如,随着这些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的不断攀升,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人肉搜索等行为犯罪化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立法违反了刑法谦抑主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刑法谦抑主义作为一个学界的“共有财产”被刑法学者所接受,不少学者主张在立法与司法中保持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用意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为了限定国家的目的与任务,防止刑法的干涉性。”[1]
然而,刑法实践却基于刑法工具主义立场,对学界主张的刑法谦抑主义立场进行了反驳。从1997年刑法生效至今,中国已经通过了八部刑法修正案,不仅增设了多个新罪名,而且扩展了原有罪名的犯罪圈,从而快速地实现犯罪化。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刑法工具立场,即刑法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维护良好的金融、经济与社会秩序等,可以用刑法强制公民的自由。
针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缝”,我们亟待理性反思:(1)在学界普遍主张刑法谦抑主义的前提下,刑事立法为何以刑法工具主义立场快速地实现犯罪化?(2)如果单一的刑法谦抑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都存在疑问,那么,现代刑法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本文认为,随着社会复杂化、价值多元化及高涨的犯罪浪潮,单一强调刑法谦抑主义或刑法工具主义都存在风险,比较可行的是,在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立足于刑法父爱主义立场,并以二元化犯罪模式实现犯罪治理模式的时代转型。
二、虚拟的自由:单一刑法谦抑主义的疑问
从学术史上考察,刑法谦抑主义属于“舶来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学者耶林作出“刑罚如两刀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的著名论断。[2]既然刑法是一种恶,那么在动用刑法的时候,就必须流露出“小心求证”的谨慎,这蕴含着刑法谦抑的价值底蕴。而美国学者帕克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对某种行为认定为犯罪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并且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才可以发动刑罚。[3]发端于西方的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立论乃是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一般而言,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在“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意义上,基本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同时,基本权利又被认为是宪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公权力必须自觉遵守这一价值秩序,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意义上,基本权利又是直接约束公权力的“客观规范”或者“客观法”。[4]
在日本,何为刑法谦抑主义,这在学界存在分歧。按照刘淑博士的归纳,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认为谦抑主义的内容包括刑法的补充性、不完整性以及宽容性,如大谷实、川端博、大岛一泰、井田良等学者所坚守;其二,对于谦抑主义的含义,提出了刑法的补充性和二次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刑法调整范围上的不完整性,这为松宫孝明、浅田和茂、立石二六等学者所坚持。这里的“刑法的二次规范性”,是指刑法规范是以民法等第一次规范的权利设定以及法律保护为前提的,纠纷的第一次性法的处理应该交给民事的、行政的法律规范,刑法起到的是第二次的、补充性的作用。[5]284-285也有学者从刑法的补充性论及刑法谦抑主义,比如日本平野龙一教授指出,“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6]在这里,平野龙一将谦抑性的实质定着于补充性,同时,他强调补充性对刑法调整范围所要求的不完整性。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谦抑主义的概念核心是指刑法的立法和适用应当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不能对一切违法行为都发动刑罚来制裁。因此,谦抑主义的实质是指刑法的补充性,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断片性)源于补充性。[5]308
而在国内,有关刑法谦抑主义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甘雨沛教授所提出的“谦抑就是意味着缩减或压缩”这一观点[7],后经刑法学界“发扬光大”,有学者从刑法的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这一价值立场出发,把刑法的谦抑性定位为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8]其言下之意是:如果刑罚因无效果、可替代或太昂贵而导致刑罚可以避免时,则刑法应该保持谦抑。很显然,这是从犯罪圈紧缩和刑罚强调降低的角度,对刑法谦抑主义的解读。此外,对于刑法谦抑主义,有学者将其定位为刑法的特征[9],也有学者将其定位为刑法性质[10],还有学者将其视为刑法机能的拓展。[11]当然,也有学者走得更远,将其归类为刑事法的法理部分。[12]尽管上述学者论述的路径或理由不同,但均认为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刑罚权要保持克制。
刑法谦抑主义的核心观点是非犯罪化,即主张刑法应该立足于经济性、补充性与最后性,首先运用其他法律去调整社会关系,之后在行为具有重大的法益侵害性,且其他法律难以调整之时,刑法才介入其中进行调整。正如平野龙一教授所指出,“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13]国内常有学者把刑法谦抑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联系在一起。1957年,英国议会下院沃尔芬登委员会(同性恋和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被学界视为是非犯罪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性恋和调查委员会报告》。该报告认为,法律的目的纵使是维持公共秩序及美德,然而,除非基于社会要求为了保护个人免受非法侵害及避免堕落和腐化,才能藉由法律的规定达到此目的。至于属于私人道德与不道德问题,并非法律的事务。和同性恋实质上都是私人道德,故无禁止的必要。[14]从此,成年男子相互同意的同性恋和(限制公开)在英国不再作为犯罪。先河既开,便一发不可收拾。之后20年间,西方国家纷纷实现了、堕胎、同性恋、通奸、酗酒等的非犯罪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价值多元化以及在环境风险、经济风险等日趋升高的时代背景下,主张刑法谦抑主义而单一强调非犯罪化,也显得“不合时宜”,这就是立法者对刑法谦抑主义“置之不理”的重要原因。
其一,非犯罪化在各国刑法发展中仅是一个短暂插曲,非犯罪化并非现代刑法发展的趋势。西方国家大多是在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增加犯罪类型的,人们从法律形式上看不出它增加了犯罪类型,事实上由于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层出不穷,犯罪类型不断增加,“犯罪化”的现象大量存在。比如,日本在1958年增加了斡旋,1987年增加了损坏电子计算机等妨害业务罪、使用电子计算机诈欺罪、不正当作出电磁记录罪、不正当供用电磁记录罪等。所以冯军教授曾特别指出,“与非犯罪化相比,这种国际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至今还未在我国产生强烈反响”,因此,“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实行非犯罪化,而是应当推进犯罪化”。[15]
其二,犯罪化的根据是多维度的,并非由刑法的谦抑性这一唯一标准所决定。刑法之补充性、最后性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刑法学中的一大难题,如果对这一问题定位不准,或者说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式,则实难对立法与司法形成强力制约。对此,中日两国的刑法学者通常都会引用到美国学者帕克的观点,即作为犯罪予以处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2)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符合刑罚的目的;(3)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4)对这种行为的处理能够公平地、无差别地进行;(5)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上的处理时,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16]可见,刑法谦抑主义只是衡量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标准之一,但绝非唯一标准,我们决不能任意地扩大其作用的范围。
其三,刑法谦抑主义单一强调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也是片面的。如何协调刑法的自由规制机能与秩序维护机能之间的关系,刑法谦抑主义立足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所提供的标准也是极为片面的,同时也不是社会的。首先,刑法谦抑主义往往把其定位为刑法秩序维护机能的内在限制,把刑法定位为人权保障的大(Magna Charts),从刑法机能角度把自身定位有利于发挥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现代刑法机能不仅保护自由保障机能,而且包括秩序维护机能和行为规制机能。其次,刑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必须充分反映民众共同的价值、当前社会的犯罪结构,并具有相应的法文化基础,这就不是仅仅给出一个强硬的处理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就可以构成非犯罪化正当性论证的基础。最后,历史证明,单一强调自由主义,带来的往往是战争、饥饿、疾病、贫穷、杀戮等不自由状态,这在风险社会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食品安全事件、环境事故、恐怖袭击等风险的增加,都会使人类在处于一种不自由状态的同时,对不自由状态的感受也与日俱增,而这些不自由的状态必须通过对秩序的维护来消除,这就把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之重要性凸显出来。
毋庸置疑,刑法谦抑主义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批判与评析犯罪化的标准,即不仅将其处罚对象限定于值得动用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之上,亦即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无法保护法益时,才迫不得已地动用刑罚,以充分保障公民自由。[5]312然而,这种刑法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以国外的刑法谦抑主义反对国内刑法工具主义的趋势,而没有关注国内刑法工具主义立场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刑法实践,所以,显得过于理想化而无法为立法者所采纳。
三、建构的秩序:刑法工具主义的制度风险
刑法工具主义把秩序作为价值目标。在工具主义之下,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秩序的维护,刑法与教化成为社会管理的必要手段。在工具本位范式之下,刑法过分关注其政治性(政治要素、政治基础、政治功能等),忽视刑法的公理性(正义、平等、自由、道德价值等)。刑法理论不是把政治作为一个理论基础问题来研究,而是把刑法理论总是作为政治问题来研究;不是用审视、反思、批判的态度研究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而是把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简单等同于对政治路线、政策、政令等的解说、宣传与辩护,致使刑法成为政治的“婢女”。[17]
这就带来了犯罪圈膨胀及重刑主义。其一,刑法中强化秩序维护的犯罪大量存在。刑法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建国以后,国家的政治理念可以集中表达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18]又因为犯罪都是稳定的对立面,所以,刑法作为维护秩序最强力的工具而受到执政者的重用。在97刑法中,分则部分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据了刑法中具体犯罪二分之一的“天下”。此外,在97刑法之后所颁布的八部刑法修正案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其二,刑法中的重刑主义趋势明显。这集中体现在死刑罪名过多和针对社会管理的犯罪处罚较重两个方面。
当然,这种刑法工具主义的蔓延也有其特定的制度缘由。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仍然保持着一元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忽视甚至漠视。”[19]事实的确如此,建国之后,中国刑法学接受的是前苏联法学,重视刑法的工具价值。这种法学图式沿袭了维辛斯基等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理念。由于受绝对刑法工具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在国人的观念中,刑法就是“刀把子”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执行阶级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和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20]尽管在当下,我们不能说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刑法的路径依赖特性,加之,国家认为其有能力通观全局、洞察一切,因此通过刑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得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自由,但这一良好愿景却总在政府的自利性与利益集团的主张下,成为以维护社会秩序或保障利益集团利益的砝码,并强有力地制约刑法变革的始末。在这种立论逻辑下,刑罚权扩张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导致了刑法变革中的泛工具化倾向。
问题只在于,刑法工具主义作为一种立场,它注重的是刑法的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注重的是运用刑法强制去建构秩序,而不是依据民众自治形成一种自发秩序,因而往往导致刑法的价值失落。
其一,过于强调刑法的政治性而忽视刑法的道德性。刑法的政治性体现在国家的刑事政策对刑法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刑法的道德性意味着刑法中的犯罪圈设置与刑罚设置不得和民众的集体正义情感相抵触。一般而言,刑法的道德性与政治性具有共同的秩序指向性,但两者又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因为道德代表着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力量、大众意识,而政治则代表着社会秩序中的国家力量、精英意识。[21]过于强调刑法的政治性,则会导致刑法中犯罪圈的快速膨胀,因为只要出现了社会问题,那么强大如“父亲”的国家就可以以社会管理、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维护社会和谐等理由而将其犯罪化。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后果则正如波斯所指出,工具主义的刑法规制可能由于官员们的有限理性而具有反效果,因为国家“官员”作为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具体体现者,作为工具化刑法和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也是具有“三个有限”的现实人,不可能制定出完美的刑法,亦不可能完美无暇地实施刑法。[22]
其二,刑法工具主义是社会不文明的体现。尽管我们常说,文明世界的特征在于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失去对世界的控制,也就没有了满足文明社会的期待。[23]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严刑峻法去对付社会纠纷,而是需要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在刑事法治意义上说,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体制与治理能力,前者是国家治理犯罪的范围与功能,后者则是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组织与实施政策的效能与能力。当国家因治理能力差而造成诸多经济违规、违法行为之时,则往往又把这种责任归结为组织体的不负责,进而对之施以严刑峻法,这是一种双重的不人道。[24]不难看出,刑法工具主义是以社会秩序为核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严厉性的刑罚尤其是死刑为后盾的,对于刑法发展来说,工具主义既是反应装置又是阻碍装置。俗话说,“弱狗常叫”,企图依仗严刑峻法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权,往往是虚弱的政权。同时,还落下了刑罚不人道、刑法不文明的口实。
其三,刑法工具主义是造成刑法认同危机的原因。刑法权威不是一种基于恐吓的权威,而是一种基于认同的权威,这就涉及刑法权威的根源――公众认同。认同是一种制度性的资产,在认知心理学上,认同其实是人类的情感与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感情与理性都高涨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信任是惊人的。比如,宗教领袖及其信徒,集权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等。约翰・密尔指出,“使我们认为不正义的行为得到惩罚,总会给我们带来,并与我们的公平感一拍即合。”[25]涂尔干也指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这种生活体系便是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特别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道德同质性程度较高的共同体或社会中,这种集体意识的力量更为强大。[26]如果说在野蛮的古代社会,刑法权威靠麻醉性的宗教神谕和武力强制尚可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没有社会成员对刑法规范的合法性认同,则寸步难行,刑法权威只有满足了集体意识中的正义情感与价值诉求,获得了普遍的公众认同,才可能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27]长期以来,刑法工具主义借助刑罚的严厉性、残酷性等建立起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然而,这种信任只能是一种“基于吓阻的信任”,并非一种基于知识的信任与基于认同的信任。很显然,如果刑法立足于秩序维护并借助于强制力强迫民众服从,带来的则是自身“公共财产”的丧失。
也因此,针对刑法工具主义这种建构社会秩序之刑法立场的制度风险,哈耶克曾明确批评指出,“建构论唯理主义者所持的这种幻想――亦即理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告诉我们所应当做的事,从而所有具有理性的人也应当能够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而加入到追求共同目的的奋斗行列之中――付诸实施,那么即刻便会破灭。”[28]此外,刑法工具主义也往往是社会管理能力低下的体现,在提倡社会管理创新且逐步向文明过渡发展的当下,刑法工具主义的立场应当被抛弃。
四、困境的突围:中国应该坚守刑法父爱主义
基于刑法谦抑主义的现实难题和刑法工具主义所存在的风险,难道我们就不能寻求一种中间道路吗?其实,刑法谦抑主义重视的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而刑法工具主义则强调的是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现代刑法的机能涉及自由保障机能、秩序维护机能和行为规制机能,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冢仁所指出,“刑法具有的秩序维持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处于密切的互为表里的关系,难免相互矛盾,相互克制……但是,本来是不允许偏向于哪一方,具体如何适正地使两者相调和,应该说正是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29]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刑法理论的应有努力方向是:寻找一种既能确保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又能发挥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的刑法模式。这就需要确立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的立场。
源自西方的刑法父爱主义理论主张国家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30]其基本逻辑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增加,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强制干预,而再考虑公民是否同意。因此,这是一种“国家对公民强制的爱”。[31]一如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 ,在刑法父爱主义看来,刑法之所以干预公民自由的正当性,是为了个体的利益或免于自我伤害,这就涉及刑法目的问题,如果刑法干预公民自由是为了增进个体更大的自由或利益,那么这种动机是父爱主义立场,而相反,如果刑法干预公民自由是为了行政管理方面或某些利益集团自利性的考虑,则属于刑法工具主义的范畴。比如,国家对非法持有的犯罪化,是为了避免持有的人吸毒而伤害自我健康,这乃是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立场,而国家对聚众行为的犯罪化,则完全是基于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这就并非刑法父爱主义的范畴。
其实,在刑法父爱主义内部亦有进一步划分,即将其划分为刚性刑法父爱主义与柔性刑法父爱主义。[32]从保护公民免受自我伤害来看,如果人们由于能力不足无法从自己最佳利益出发来行动,并且当认知障碍清除后很可能同意刑法对于自己行动的干预,那么刑法的这种干预就是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立场。[33]正如Feinberg所说,软家长主义保护行为人不受“不真实反映其意志的危险的选择”的危害。[34]哈特也指出,“在谋杀案或者伤害案的指控中,排除受害者的同意作为辩护理由的规定,堪谓一种家长主义的极佳典范。”[35]而倘若无论选择是否出于人们的清醒认知,只要刑法为防止其做出有悖于自身最佳利益的选择而径直限制人们的行动,就是刚性父爱主义的体现。[36]不难看出,无论是刚性刑法父爱主义抑或柔性刑法父爱主义,都是刑法对公民强制的爱,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与刑法谦抑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刑法父爱主义并非出于政府的自利性而将所有破坏秩序的行为纳入犯罪圈,而只是将危及社群利益的行为纳入犯罪圈,以保护民众利益,因而和刑法工具主义不同;另一方面,刑法父爱主义反对刑法谦抑主义消极干预的立场,主张为了公民利益可以积极进行刑法干预。
笔者认为,在犯罪控制有余、人权保障程度不高,但又需要增进民众福利和建构良好社会秩序的中国当下,我们应该坚守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立场。
其一,由法益侵害说这一犯罪本质所决定。法益侵害说意味着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与之对应,刑法的任务是借助于不法与有责判断,将值得处罚的行为纳入犯罪圈,而将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排除在刑法大门之外。为何刑法要保护法益?这与刑法谦抑主义与刑法工具主义无关,而是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立场。如前所述,刑法谦抑主义立足于公民的自由保障,而刑法工具主义则看重社会秩序维护。其实,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从社会生活出发,即首先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或危险,然后,立法者再将这种法益侵害的程度进行评估,并在其他法律调整无效的情况下,转而由刑法调整。这是刑法家长主义之保护原则的体现,考虑到个体的脆弱以及现代法律对个体私立救济的禁止,刑法应该保护个体免受外界伤害。这只是问题的一端,问题的另一端是,刑法的家长形象应当面向公民整体和组织体,保护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这里的例外是,对于破坏管理秩序行为的入罪,并非刑法父爱主义的立场,因为作为管理者及其所属的组织,本就被国家授予了一定的权力,如果再以刑法强化这种权力的行使,则无异于扩大了“家长”的权力,进而会造成公民自由的萎缩。也因此,在国外判例与学界看来,警察机关的公务行为,法律已经赋予了公务人员通过自力排除抵抗的权利,此时对威力妨害公务的行为以犯罪定罪处罚,也为不当。这就是日本只规定威力妨害业务罪,并把权力性公务排除在其适用对象之外的重要原因。[37]
其二,国家治理战略的功能导向所决定。如何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不仅是一个刑事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圈与刑罚强度与种类的设定问题。刑法父爱主义所描述的法律图景,是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社会秩序的再建构过程。通过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甚至是对个体利益的剥夺,减少、排除因个体不负责行为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从而将个体利益分割整合进更大的秩序控制战略之中,并借助于刑事政策的功利取向去推行有利于增进社会安全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等的犯罪治理策略安排。由此可见,在刑法父爱主义的语境里,自由、自治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最高权利,它们也并不天然地享有优先于其他价值考虑的地位,它们与强制、干预力图实现的“福利”是可以通约换算的:如果个体自由或社会自治所失去的利益可以用社会总体福利(比如安全、健康等)的增量来抵偿,那么自治、自由就应当向国家干预、强制让步。[38]这就蕴含着国家立足于功利主义立场而扩大犯罪圈的正当性。
其三,由现代刑法的机能所决定。尽管存在着价值判断多元化,但在一个走向法治的社会里,公民对法的忠诚与信赖是一个应然的追求目标,而非实然的现实描述,这需要借助刑法机能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刑法学界主流观点一般把刑法的机能定位为:法益保护机能(与秩序维护机能基本上同义)、自由保障机能和行为规制机能。[39]尽管在风险社会时代,刑法更加看重法益保护机能,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甚至被置于比个人法益更为优先的地位,并且出现了法益保护前置化和抽象化的倾向[40],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刑法还肩负着自由保障机能与行为规制机能。无疑,刑法谦抑主义立足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而刑法工具主义意图以强化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而同时实现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应该成为当代刑法理论的追求。笔者认为,刑法父爱主义即可实现两者的最佳平衡,一方面,刑法父爱主义立足于保护原则对行为人的自由进行干预(比如,对行为人吸毒行为的刑法规制),这不仅有利于防止行为人利益的被侵害,也有利于保障行为人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刑法父爱主义即使为了公民整体和组织体而限制个体自由(比如,刑法对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规制),这也是一种基于更多人的自由之考虑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因而也能达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的最佳平衡点。
所以,哈特曾特别指出,“父爱主义的例子环绕我们的法律,无论民法还是刑法。”[41]当然,这也使国家和政府的身份逐渐从“夜警”或“守夜人”转变成“家长”或“慈父”,以致于在当代,法律父爱主义深度渗入劳动刑法、环境刑法、经济刑法、风险刑法等领域。影响所致,我们必须立足于刑法父爱主义立场,寻求一种更加能够实现刑法之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的犯罪化模式。
五、二元化犯罪模式:刑法父爱主义的刑法实践
一般认为,立法模式和具体立法方案的科学性,取决于立法者对立法环境、目的等的正确认知和把握。随着国家理性大写神话的破灭,国家本位观又逐步被国家与社会二元观所替代,并分别建构自身的内在规则与价值,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国家、社会与公民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社会。这反映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领域,则要求我们打破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实现犯罪模式与刑罚模式的多样性,以应对多元化社会下的犯罪治理需求。其中,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根据与标准的建构中,立足于刑法父爱主义立场而提倡一种二元化犯罪模式,才是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重要抉择。
就概念而言,二元化犯罪模式是一种以犯罪化为后盾保障行为积极履行义务或弥补被害人损失,并在行为人积极履行义务或弥补被害人损失后不以犯罪处理的犯罪模式。它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统一,其中,非犯罪化是优先模式,即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犯罪化是保障,即在不符合法定的非犯罪化的情况下,又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犯罪模式集中体现在刑法第201条有关偷税罪的立法中,即“有第1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在这里,因“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且接受行政处罚”而导致的非犯罪化是一个向度,而因“不补缴应纳税款,或不缴纳滞纳金,或不接受行政处罚”而导致的犯罪化则是另一向度,这是一种“行政处罚优先的非犯罪化”和“刑罚处罚保障的犯罪化”并存的犯罪模式。[42]
不难看出,二元化犯罪模式体现了刑法父爱主义立场,十分有利于在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应该成为中国今后增加新罪名的首要选择。随着社会利益分割的复杂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冲突的急剧增长,民众自然对强大起来的国家责任寄予厚望,于是,近代行政刑法得以产生,并独占了以制裁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日本刑法学家福田平认为,在法律秩序的内部有两个层面:一为国民生活秩序的层面,即基本生活秩序;一为根据行政作用不断创造出的层面,即派生生活秩序。[43]这大致涉及刑法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言,它大致包括纯正的贪利性犯罪和不纯正的贪利性犯罪。前者是指行为人违反行政法义务的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并不会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等法益的情形,比如偷税、单纯走私、伪造货币等;而后者则是行为人在违反行政法的义务,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又侵害了他人的生命、健康等法益的情形,比如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等。[44]而就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言,涉及派生生活秩序的犯罪主要是基于强化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犯罪,比如刑法第六章之下的“妨害司法罪”、“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妨害文物管理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节罪名涉及的具体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根据行政作用不断创造的派生生活秩序,如果仅仅是具体强化行政管理的需要而犯罪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刑法工具主义立场,如果是为了维护民众利益或组织体的利益,则是一种刑法软父爱主义立场。然而,在具体的立法策略展开中,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别清楚,因为立法者也具有自利性,缺乏民主机制保障的立法者往往会打着司法为民等口号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阴谋”。所以,与其在两个之间的界限上纠缠不清,并避免立法者主张的立法为民在实践中滑向刑法工具主义,我们不如在制度上避免过度的刑法工具主义倾向,即对纯正的贪利性行政犯和基于强化行政管理的犯罪,按照二元化犯罪模式设计其犯罪标准问题,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后,能够积极弥补被害人损失,并且接受国家行政处罚的,则可以不按照犯罪处理,以体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而相反,如果行为人不愿意积极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也不愿意接受国家行政处罚的,则以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以体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事实上,立法者对刑事和解的法定化,也预示着以犯罪后行为人的行为为标准二次界定犯罪是否追究,具有明显的谦抑、效能与激励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可以推广的犯罪化模式。
这样的一种刑法学思考显然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与规范意义。置身于法律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刑法学在经历了刑法谦抑主义对刑法工具主义的“解构”之后如何发展?在我看来,其答案便在于坚持一种刑法父爱主义立场,并以二元化犯罪模式对此予以体现。也许,这能够成为中国法对世界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
[2]林山田.刑罚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127.
[3]See Paeker,The Limit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M],1968:296.
[4][德]Robert Alexy.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规范之基本权[J].程明修,译.时代,1999,(4).
[5]刘淑.日本刑法学中的谦抑主义之考察[A].陈兴良.刑事法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M].有斐阁,1972:47.
[7]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 (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1984:175.
[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52-356;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3-78.
[9]赵秉志.刑法基础理论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17.
[10]张小虎.刑法的基本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54.
[11]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32-35.
[12]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6-112.
[13][日]平野龙一.现代法II――现代法与刑罚[M].岩波书店,1965:21-22.
[14]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419-420.
[15]冯军.犯罪化的思考[J],法学研究,2008,(3).
[16]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145.
[17]姜涛.死刑制度改革与工具本位转换[J].刑法论丛,2011,(3).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19]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21世纪刑法学研究展望[J].人民检察,1999,(11).
[20]姜涛.全球化时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发展路径[J].环球法律评论,2007,(3).
[21]刘远.刑法的道德性与政治性[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5).
[22][美]科林・凯莫勒,萨缪尔,伊萨查罗夫,乔治・罗文斯坦,特德・奥多诺霍,马修・拉宾.偏好与理性选择:保守主义人士也能接受的规制――行为经济学与‘非对称父爱主义’的案例[J].郭春镇,译.北大法律评论,2008,(1).
[23]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10.
[24]姜涛.社会管理创新与经济刑法双重体系建构[J].政治与法律,2011,(6).
[25]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in John Stuart Mill and Bentham,Utili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M],ed.Alan Ryan,Harmond-sworth,Penguin,1987:321.
[26][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2-56.
[27]梁根林.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4.
[28][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37.
[29][日]大冢仁.刑法概说 (总论)[M].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23.
[30]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31]Cass R.Sunstein and Richard H.Thaler,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J],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70,2003:1165.
[32]John Kleinig,Paternalism[M],New Jersey:Rowman & Allanheld,1983:8-14.
[33]David L.Shapiro,Courts,Legislatures,and Paternalism[J],Virginia Law Review,Vol.74,1988:528.
[34]Joel Feinberg,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Harm to Self Vol 3[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99.
[35][英]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0.
[36]Anthony T.Kronman,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J],Yale Law Journal,Vol.92,1983:763.
[37][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0.
[38]吴元元.法律父爱主义与侵权法之失[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3).
[3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7;[日]内藤谦.刑法总论讲义[M].有斐阁,1991:43-48.
[40]姜涛.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现代转型[J].现代法学,2010,(4);姜涛.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J].当代法学,2014,(1).
[41]H.L.A.Hart,Law,Liberty,and Moralit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32.
[42]姜涛.激励、效能、谦抑:二元化犯罪模式的法理审视[J].时代法学,2010,(3).
[43]金泽刚,黄明儒.日本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J].政治与法律,2004,(6).
[44]姜涛.行政犯与二元化犯罪模式[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