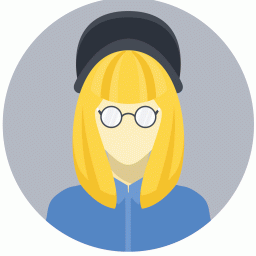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企业集群
时间:2022-06-28 06:36:45

摘要:企业集群是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或某特定领域内大量互相联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其支持机构在该区域空间内的集合。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形成了自己的企业集群,产生了人才集聚效应、学习与创新效应、制度效应。这种企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至今对于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晚清;民国;上海;出版;企业集群
亚当?斯密很早就注意到了企业集群这种现象。他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企业集群”的概念,但进行了实质性论述。在他看来,由于社会分工,产生了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以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为目的而结成的群体。韦伯则在企业集群的概念中引入集聚因素,强调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相互联系的集聚体。后来还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例如威廉姆森把企业集群界定为介于纯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罗森斐尔德侧重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企业集群活力的决定性影响,而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垂直企业集群和水平企业集群的定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关于企业集群的基本认识:企业集群是指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或某特定领域内大量互相联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其支持机构在该区域空间内的集合。企业集群有自身的类型、特征和效应,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我们以企业集群理论来观照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企业,无疑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出版企业的建设、出版产业的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国务院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鼓励打造文化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在打造产业集群方面无疑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从历史发展中吸取有益经验的。
一、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无可争议的出版中心。其中心地位既体现在上海出版业的社会影响、文化贡献,又体现在它的企业业态、产业规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而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一个城市作为全国出版文化中心的重要标志。老上海出版企业集群就是在沪上妇孺皆知、闻名遐迩的福州路文化街上孕育、成长和壮大的。
福州路东起中山东一路,西到中路,全长1453米。19世纪50年代筑成界路(今河南中路)以东一段,早期称劳勃三渥克路,后因附近有基督教伦敦会传教机构,故又称布道路、教会路。1864年筑完全程,1965年以福建省福州市命名,老上海称其为四马路。福州路文化街一般指河南中路以西,福建中路以东的福州路及其周围的山东中路麦家圈、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山西南路和昭通路一带。自1845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在今福州路南的山东中路路口开设墨海書馆起,19世纪中期在棋盘街上先后涌现了文瑞楼、著易堂、扫叶山房、乐善堂、万卷楼書坊、广益書局及吴鞠潭,胡开文、曹素功、周虎臣墨庄,荣宝斋、大吉楼笺扇,西泠印社等。到20世纪初叶福州路文化街初步形成,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全国書店调查录》序中载,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福州路一带有报纸数十家、杂志数百种、新旧書肆三百余家,可谓九州皆知,天下共晓,影响波及于海内外。
从福州路到南京东路的山东中路一段早期叫庙街、望平街,在该街附近有1850年由字林洋行创办的沪上第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后改名为《字林西报》。1861年字林洋行又创设了沪上第一份商业中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2年创刊的《申报》、1893年创刊的《新闻报》等数十家报馆、报纸集中在此出版发行,这条街便有了报馆街之称。福州路書店(出版社)的源头是1844年的隆泰洋行,它经营乐谱、商业辞典、航海历、中国海岸水路图等,后来才有了由上海县城迁来的墨海書馆。1897年商务印書馆成立,申城書店向北移至河南中路福州路,20世纪以来先后开设了中华書局、大东書局、世界書局、传薪書局、开明書店等。由于福州路書业日趋繁荣,又有有正書局、生活書店等一批创设于外路段的出版发行机构云集到该路段谋求发展。到抗战爆发前,福州路一带的新旧書店已有三百多家。此时,资本雄厚的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在福州路。上海出版的图書占全国的90%,福州路的商务、中华、世界書局三大巨头就占全市的60%以上。福州路不仅是上海,也是全国图書出版、印刷、发行的中心。
老上海的出版文化企业集群既有迈克尔?波特说定义的“水平企业集群”,众多“扎堆”的出版机构共同享有终端产品市场,使用共同的技术、技巧以及相似的自然、人文资源;同时,也有所谓的“垂直企业集群”,即通过买卖关系来连接的众多关联企业集群。除了报馆、書业机构云集,福州路一带文化用品业、文化娱乐业也异常发达。如仪器文具业方面,起初是隆泰洋行开其端绪,后在河南中路棋盘街出现,有以经营传统文房四宝的鸿宝斋、文瑞楼等。1870年屯镇胡开文笔墨社在河南中路开业。19世纪后期有德隆昌、万亨和纸号,商务、美生印書馆(兼营文具)的相继开设,使该路的仪器文具业初露端倪。20世纪初期,我国首创唯一的科学仪器馆在河南中路开办,使该路传统文房四宝向现代仪器文具转化。接着有周虎臣、周兆昌、曹素功笔墨庄云集福州路附近,该行业的营业规模日益扩大。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具仪器的需求日趋增加,加之周围新闻业、出版业的蒸蒸日上,市内外文具业进一步向这一中心地带聚集。抗日战争前后,著名笔墨庄和日商掘井誊写堂,大正、大井洋行等又一次在此落户,至上海解放前夕福州路及附近仪器文具店鳞次栉比,成为中西文具兼备、文化用品齐全、批发和零售兼顾的仪器及文化用品集散地。
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除了与其他企业集群相同的成因外,租界的出现与发展也是重要的缘由。朱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所记出版单位(主要是图書机构)近600家,空间以上海市区为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租界时起,至上海解放后私营書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止。作者在列于该書卷首的《漫谈旧上海图書出版业》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二三年,上海县城外北面郊区,辟为租界,后被英、法帝国主义蚕食扩充到西北郊区。外国传教士来上海在租界内所设出版机构先后有数十家,有称書馆(如墨海書馆)、書院(如林华書院)、書室(如格致書室)、書会(如同文書会)等。这些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从好的方面说,是把西方社会科学思想、自然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出版了一批启蒙读物;从坏的方面说,他们是进行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平心而论,我国人在租界内经营出版事业比较方便些,这是事实。”作者通过列举20世纪30年代文化街一带不同路段出版机构的名称,充分展示这里企业集群的繁盛景象。这些出版发行单位,大多是在本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有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朱联保说:“群益書社是1907年由长沙分设到上海的(该社曾设分社于日本)。美华書馆是先在宁波而后于1895年移到上海,新学会社也是辛亥革命前由宁波移来上海的。宁波与上海通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地理位置、人文经济等均不及上海港发展之快,故有由宁波移来上海的。”还有北新書局因军阀的迫害由北京南迁上海后,在鲁迅大力扶持下创造了不俗的业绩,更是書业佳话。新月書店、《语丝》、《现代评论》等新文学出版机构,也在20年代后期纷纷离开北平,移驻上海,开辟了新的出版天地。
至于汪孟邹开办于芜湖的科学图書社,后又把大本营搬到上海创建亚东图書馆,更是出版企业集群的典型表现。亚东图書馆一度在福州路江西路口福华里内经营。“陈独秀认为亚东设在里弄内营业不能开展,由于他的建议,乃于1919年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租得门面,坐北朝南问。那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他介绍经售北京大学出版部的書籍,营业很好。”天时地利人和,亚东图書馆成为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一份子,才创造了自己新文化出版的辉煌。出版产业的专业化和地理集中,使得上海不仅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绝对中心,也成为亚洲最富活力与影响力的出版中心之一。
二、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效应
地域性的企业集群能够释放出一种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既是企业集群存在的合理基础,也是企业集群不断完善的推动力。迈克尔?波特认为这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能获得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经济外部效应、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学习和创新效应以及品牌与广告效应。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福州路一带出版企业集群的效应主要表现为人才集聚效应、学习与创新效应以及制度效应。
先说人才集聚效应
作为内容产业的现代出版对文化人才有着特殊的需求。新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固然离不开新的印刷复制技术、新的经营方式与盈利模式、新的读者群体与市场空间,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新型的献身出版事业的各类文化人。晚清时期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形成企业集群,除了工商业发展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大面积租界的形成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海开埠以后崛起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吴永贵这样论述这个群体的来源:“其中有来自欧美的文化人,他们大多有教会背景,传教之外,从事着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方面工作,其出版活动对中国新式出版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有因为战乱而来上海的中国各地知识分子,先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使受战争破坏严重的江、浙、皖地区的文化人涌入上海,继而19世纪末的和庚子事变,又有一批知识分子进入上海避难;也有出于谋生需要而来上海的文人,他们多身具一技之长,考虑上海文化市场发达,主动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另外,在津浦铁路通车以前,四川、两湖等内地人到京师去,要经过上海转海轮北上,内地青年若到日本留学,上海更是必经之地,上海以其特殊的地位,在当时简直成了西学在中国的‘批发站’和‘中转站’,求西学,奔上海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心理。”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的士大夫无论是价值观念、人生理想,还是知识结构、谋生手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或从事著译,或参与出版,构成了新式出版最为重要的作者群体和出版力量”。有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又集聚了人才——这个出版事业最重要的无形资本,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便水到渠成。
文化人才的汇聚为出版企业的创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其中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企业创业的动力之源;反过来,众多出版企业的成立、迁入、发展和壮大,也起到了筑巢引凤的效果。晚清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出版的第一个人才群体荟萃之地,留学生群体则成为最广泛的报人群体,前者根据地就在上海,后者的集群效应于沪上也有所体现。而更为典型的商务印書馆,汇聚了近代出版最大的人才群体于此,并影响到出版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各类人才的凝聚。商务的各路英豪中,不乏企业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印刷技术人才,最能导引出版业的还是其编译所的编辑著译人才群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商务编译所拥有的专家学者型人才多达三百多人,不逊于国内任何一家知名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用今天的话说,商务的人才队伍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以商务印書馆为人才的母体,现代几大出版机构的创办人都是从商务印書馆掊离出来的,如中华書局的陆费逵、开明書店的章锡琛、大东書局的吕子泉、世界書局的沈知方,以商务印書馆为近代中国出版人才的母体,分蘖了诸多的出版人才群体。这成为新出版的一个特点。”如果用胡适的话说,一家大的出版文化机构是一种“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一个出版企业集群就是一个“磁场”,一个海纳百川、吸引人才的“磁场”。
次说学习与创新效应
企业集群是培育企业进行学习和创新的温床。企业位置相互毗邻,企业类型彼此相同或相关,客观上为它们的互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竞争的压力也自然而然成为企业探求与创新的动力。企业如要生存以及更好地、更持久地发展,则必须在模仿中创造,在学习中超越,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近现代上海出版企业间往往通过模仿中的学习来克服新生企业的某些缺陷,迅速提升自我,发展壮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说,商务模式对上海出版业具有示范效应。“商务印書馆开辟了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事业,商务的成功带动了上海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涌现。有人把中华書局、世界書局的创立,看作是商务模式的延续和扩大。”除了中华、世界,还有大东、开明等重要書局,一些中等规模的出版机构,也大都学习商务模式,创业初或为独资,或为合伙,后来先后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即便是在内部管理机制、机构设置、人员晋用,以及市场布局、营销手段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借鉴了商务的成功经验。
企业集群的学习创新效应有时也表现为竞争中的学习与开拓。中华在与商务展开教科書全面竞争的同时,在辞書、古籍、期刊诸多领域也发力角逐。商务有《辞源》,中华则编《辞海》;商务有《四部丛刊》,中华则出《四部备要》;商务有《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名刊,中华也刊行《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杂志”。针锋相对,虽似“拷贝”,其实又多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内容形式皆有突破。
还有沪上群星璀璨的中小書局,在大社名社的挤压下,更是向专、精、特、新的方向拓展。出版企业集群的存在,克服了新企业因新而有的不利,推动了创业,也使后来者不断学习和探索。亚东图書馆的古代白话小说标点分段、泰东图書局与创造社的联姻、良友图書印刷公司的新型画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文学丛刊、上海杂志公司的主打期刊营销、生活書店的大胆作风等,无不体现出现代企业集群的特殊效应。不学习无以生,不创新唯有死。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上海滩众多出版文化企业在市场中各展长才。而大型書局如“五大書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的市场份额远胜他家,产业集中度之高也远胜于今日之中国出版界。
再说制度效应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企业集群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有合约、产权等,后者有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这种制度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企业集群中都有明显体现。
企业集群运行机制的基础是信任与承诺。这种人文因素是维持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长期关系的纽带,并使集群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与沪上出版企业集群相伴而生的是書业同业公会。自1874年以来,随着上海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和相关企业集群的出现,出版行业协会纷纷成立并不断发展,先后组建的書业公会有上海書业公所、上海書业商会、上海新書业公会、上海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华商書业联合会、上海書业联合会、上海特别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書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書业同业公会、上海特别市装订書业同业公会、上海市铅印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簿册装订商业同业公会、译書公会、译書交通公会等等。这些由出版经营者自发建立并经政府核准的行业组织旨在“谋求同业之利益,维护同业之信用”。汪耀华编著的《上海書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收录了上海書业同业公会各组织1906年到1953年的重要章程、业规、划一图書价目实施办法及相关应用附件等。这些書业同业公会通过道德自律与法规行规他律的相互协调,对于出版企业集群建立公平的交易市场,维护行业的经济利益,保护出版者的合法版权,加强经营者的道德自律,最终促进出版业良好生态环境的形成,推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新書业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出版企业集群内,除了通过行业协会加以协调和管理外,企业相互之间也自觉加强沟通,以协议等方式来共同维护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例如,1921年底商务印書馆和中华書局就签订了销售小学教科書的协议,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发行折扣、回佣、赠品、对分局补贴限制以及违约罚款等,十分细致,具有可操作性。“为了减少竞争的负面影响,1935年陆费逵代表中华書局多次约商务印書馆、世界書局、大东書局、开明書店几家主要的出版社,商讨同行业规,试图用一种行规来约束彼此的行为。”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也是企业集群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它通过政策制定,选择合适的厂商进驻集群,维护集群秩序,并通过特定的集群政策,形成适合有利的制度来促进集群的发展。“在近现代出版史上,不论先前的清朝政府,还是后来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在出版管理上,基本上都采用了预防制中的注册登记制,并同时通过制定各种相关出版法律,建立各种审查机构,采取各种追惩手段,增加其管控力度。另外,政府鼓励甚至要求各地建立报业和書业公会,通过行业协会进行管理,也是政府管理出版业的主要手段之一。”近现代史上三个不同政府对待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的态度不尽相同,但登记制而非审批制的基本企业设立制度,法律的、经济的而非主要是政治的、行政的管理方式,加之租界这个“特区”的特殊保护,使得沪上出版企业在并不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仍然创造了書业奇迹,企业集群的效应也得以充分展现。
三、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企业集群深处的思考
通过企业集群的理论来反观渐行渐远的晚清民国上海出版业,我们顿生无限感慨,也有一些困惑。从出版企业集群来看,老上海留给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其一,出版的中心是不是一定要靠近甚或同化为政治的中心。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心逐步移至上海,告别北京和南京,对出版业应该是幸事。过浓的政治氛围、过强的政府干预、过多的计划管制,往往不利于出版企业的发展。其二,出版企业集群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都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和经济的规律,自发性和内生性是它的特点。现今的北京聚集了全中国差不多40%以上的出版机构,但并没有显示出企业集群的特色和效应。其三,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需要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政策和适合的法律保障。企业没有自主创设、优胜劣汰乃至自生自灭的权力,就不可能由少而多,集聚成群,汇涓涓细流成大江大河。其四,企业集群特别是中小企业集群并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它作为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现在除了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一律按省(直辖市)级设立大型出版发行集团,未必比中小企业集群更有活力,更能抗击风险。国外如美国纽约新媒体及其产业高度集聚,意大利、印度的一些中小企业集群成效显著,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快速发展,也大多是得益于中小企业集群。此外,出版企业集群的出现有利于人才群体性的形成。一个出版机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人才群体,没有自身的人才高地,要想在国内国际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不乏教训。老上海出版企业集群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有益的启示。今天的出版业应从前人那里学习些什么、怎么学习,实在还很值得深思。出版产业的壮大、出版事业的繁荣,企业是载体,人才是根本,制度是关键。克服急功近利的政绩思想,遵循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积极营造良好的适宜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政治环境、文化政策和产业生态,刻不容缓。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史版话
印刷术发明前的手抄本書籍
从大约公元6世纪,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書籍都是由抄写员依据一系列常规来复制的。这些复制员通常身为修道士,在被称为抄写室(scriptoria)的修道院工场里工作。他们的一部分工作是抄写复制宗教仪式方面的著作,以满足教育新教徒和礼拜活动之需,但他们也曾复制同样用拉丁文写作的世俗書籍。抄写工作在羊皮纸或牛皮纸上进行,这些纸事先要折成页,标上记号,打上格线。然后,纸张会被切割成页,再摞成层叠状。如果需要复制很多本,母本就会被分给多个抄写员,每个抄写员就他自己的那部分提供多个复本。工作由一个主事负责监管,他给抄写员提供羊皮纸、笔、墨和尺子。为了防范火灾,禁止使用人工光源,抄写只在白天进行。抄写员只负责用黑墨水抄写正文,留下書名、标题和首字母由文字装饰匠(rubricastor)用红笔填上。
为了提高速度,一本書的抄写会分派给多个小组承担,因此不同风格的書写方式会在同一本書中出现。
(摘编自[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書史导论》,商务印刷馆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