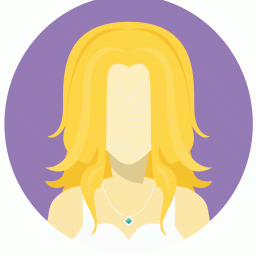我是传奇 11期
时间:2022-06-19 05:44:39
寡人有疾
生人死人,乃帝王之权。帝王虽自可借君主之威权,持黎庶万民之生死于掌中,然而,帝王既身为天子,虽然仰承天命,治理万民,但于己而言,内中也不过凡俗肉身,对自己的死生运命,却也只得听诸天意。
1730年,爱新觉罗·胤禛——后世所称的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已历八载。他此时年已五十有二,过了古人所谓天命之年,尽管每日受到臣僚三呼万岁的恭维,但雍正自知古来并无万年天子,而且体中究竟何如,也只有自己方才知晓。作为被后人誉为最勤政的清代君主,雍正勤求治理,每日除临朝听政,引对臣工外,更通宵达旦,批阅奏章数以百计。这位忌刻多疑之君主,一向以明察为能,故今人检视昔日雍正朱批奏折,会发现奏折末尾留白处,乃是皇帝驰骋圣裁天意之所,常常下笔一气千言,对一些宠信近臣甚至还会夹杂谩骂调侃,如对家人叙谈,以彰显推心置腹之心,尽管也许未过几日,申饬责骂就会如同暴风疾雨一样射向同一名臣僚,如视寇雠。
李卫就是这些时而仰承圣恩,时而领受天威的皇帝心腹臣僚之一。他行年不过四十,正值壮年,却已然官居浙江总督。李卫非是靠科举正途步入官场,乃是纳捐出身,故并无文章资望可为凭恃,唯一端赖者只有皇帝恩眷,故李卫既被皇帝视为心腹臂膂,也是皇帝待以家人,倾吐体己话的对象,自然感戴圣恩,鞠躬尽瘁。
当裹着黄绫的折匣于7月5日送达李卫坐镇的杭州衙署时,李卫自然毕恭毕敬,面朝北京叩首行礼,仰接上谕。
折匣中的上谕是通过廷寄这种秘密而迅捷的传达管道发送李卫等少数几名心腹大臣的特谕,足见雍正不愿让此事播扬开来,暗示臣僚当仰体君心,机密从事,不可少有懈怠,不然就像雍正先前颁发群臣上谕中所裸威胁的那样——“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君”。而此道圣谕的书写方式,更加彰明皇帝用心良苦——通常分颁群臣上谕,大抵由皇帝口述,值日翰林恭书,但此道上谕,却是雍正亲自用朱笔御书,更加暗示接旨臣僚不可怠慢。但值得玩味的,却是这道上谕的内容非军国大事,而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私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
在上谕的最后,雍正写道:
慎密为之!
在李卫看来,皇帝的上谕似乎坐实了自年初以来官场间的一个传闻——皇帝龙体欠安。尽管月复一月,各省疆臣大吏都会给皇上递上请安折子,而皇帝的批答也总是一个简单的“朕安”,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应故事。君主既身系天下之安危,故身体状况更属机密,如今雍正却发来访求医生方士之密谕,足证皇帝病势已难掩饰,不然不会如此明确暗示其迫切求医之心。
尽管雍正在上谕中已明确表示“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但如此勖勉恳切之辞,对李卫这样深谙君心之臣来说,不过是驱策鞭仆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倘若真的信其所言,一旦访求非人,则皇帝盛怒之下,诛罚加之,非同儿戏。
如何拿捏分寸乃是一门学问,在李卫之前,已有许多臣工因为不善拿捏而罹遭申饬,甚至丢官去职。就在两个月前,雍正的另一名宠臣,四川巡抚宪德就因为推荐了一位诨号“王神仙”的道士,而被皇帝斥为“捏骗棍徒”,大加申斥。
究竟应当如何行事方能在满足上意和保全己身之间掌握平衡?自1730年起,皇帝忽然连发谕旨,征访民间奇人异士,有时甚至以名索人。这恰与皇帝圣体违和的传言相一致,就更让人窦疑丛生。
以名索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寻访有“龚仙人”之称的龚纶,雍正对寻访此人的热忱可以从1730年3月8日四川巡抚宪德密折的两件附片中略窥端倪。这两件附片一件是雍正御笔亲书的上谕,要求宪德寻访到此人后,要“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而且还特意嘱咐宪德“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另一张附片则是龚纶的简历,从这张简历中可以约略看出雍正的目的所在。在这份不足二百字的简历中,除了对龚纶的姓氏籍贯简要介绍外,就是龚纶令人称异的长寿和健壮:“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但最令雍正感兴趣,也是证明其养生之术灵验的是简历中所称的“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
从雍正对龚纶的兴趣中也许可以看出皇帝病灶的真正所在——积年劳于政事,加之年过半百,使皇帝的精力不济,圣躬违和。就在李卫接到雍正访求名医方士上谕前一天,雍正就在一次诸王文武大臣俱在的朝会上,承认自己“自去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间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
但这究竟是何病症?这也许恰恰是雍正所隐秘讳言之处。而朝鲜使节回国的报告中,则直指长期以来困扰雍正的疾病,乃是因好色戕贼身体所致,“皇后则弃置京城,只与宠姬辈出居圆明园,日事荒淫”,如此几年,最后甚至到了“下部及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尸,不能运用云”的地步。
皇帝如此阳刚不振,自然需要龚纶这样在八十六岁还能生出孩子的“龚仙人”亲来传授经验。但宪德的奏覆却让雍正大失所望——“龚仙人”已于两年前身故,余下子孙并没有人得传其父养生秘方,雍正只好另寻它途。李卫作为雍正寄予厚望的宠臣,自然当仰圣意,排解圣忧。
就在李卫收到雍正密谕的第二天,一份工工整整誊缮好的奏折被小心装进折匣中,快马加鞭,送抵京师,直达御前。在奏折中,李卫用尽可能审慎小心的文辞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他“向曾闻得”的“深通数学,亦明性理”的河南方士。为了尽可能推脱责任,李卫声称自己“未见其人”,但是此人曾为已去世的清代名医刘璐所“深服”,并且曾与李卫的同僚,雍正的另一名宠臣田文镜有过来往。
贾士芳就在此时,以贾文儒的名字登场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雍正御前时,前途似乎乃是一片祥和喜乐。雍正的欣喜之情在给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上谕中溢于言表:“闻此人甚高博,可令踊跃鼓舞”,汲汲要求田文镜“密送至京,朕试看”。田文镜的回奏更是令雍正大喜过望,在田文镜的奏覆中,贾士芳不仅“颇知数学,言多应验”,而且“言论深远,非高博者不能”,有“贾神仙”之称。
但此时,无论是雍正,还是李卫、田文镜都无法逆料这个开端将会导致何种样的结局,对一个长久以来跪伏在雍正这位敏感多疑君主恩威不常的影子中的臣子来说,无论发生任何变数都应以常理视之。只有那个已经被这三个人以不同心态写下名字的贾士芳,尚被蒙在五里雾中,他更不知道,他将要前往治疗的这名非常病人,罹患的真正疾病是如此的凶险和致命。
神仙?妖道!
1730年8月28日,贾士芳在河东总督田文镜的殷勤款送下,启程前往帝国京师。他并非第一次进京,京城的一所著名道观白云观,就曾经是他的客居之所,外间则传闻他曾是驻节江苏清江浦的河道总督嵇曾筠的座上宾。荐送贾士芳的田文镜则在奏折中称,贾曾在1721年因“言多应验”而被前任河南巡抚杨宗义访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贾士芳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方道士。
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比一个游走各地之人更令人感到惊疑的了。这些游走各地的陌生人搅扰了当地居民熟悉的社会空间,将不安的涟漪层层扩散到大街小巷——传统中国的社会并不开放,民众对闯入这个封闭空间的人宁可保持警戒拒斥的态度,游方僧道更是其中最值得疑惧的一类,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可以通过所谓的“法术”,将超自然力量带入人们所熟知的平常世界中。其所带来的超自然力量,尽管有时确能起到益处,但更多时候,一如明清文人笔下的志异怪谭一样,会给人带来灾殃,甚至是剥夺人的生命。贾士芳正是这样一个给人带来恐惧、不安的道士,在一个相信鬼神灵异之说的时代,贾士芳模糊不明的出身更被渲染了神秘色彩。据贾士芳同时的文人袁枚和顾公燮记述,贾的出身便灵异非常,年少时曾被一名叫王紫珍的“尤有神通”的道士携上天宫半日,但回家时却发现已过数年,而他精于术数,预言灵验的本领,正是因为在天上饮了半杯酒所致。
贾士芳神乎其神的出身及其神验灵异的传闻,都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但也同时成为一个众人竞逐的对象,因为他手中握有的超自然的力量——法术,在带来灾祸的同时也同样能给人带来吉祥。而现在,毫无疑问,官僚机构希望将这种未知的力量握于己手——在李卫、田文镜这样的帝国官员眼中,贾士芳唯一的真正作用与平日呈送皇帝取悦圣意的贡品一样,都是用以固宠升迁的本钱。但有鉴于这种神秘力量远非凡俗之人所能操控,所以他们无法预知送往皇宫大内的贾士芳究竟是一件取悦龙颜的精巧,还是一颗随时可能将他们仕途前程甚至性命都炸毁的定时炸弹。
李卫忐忑虚悬的心在两个月后才安定下来。10月17日,李卫收到皇帝的上谕,告知“圣躬大安全愈”,而这一切都是贾士芳悉心调治的结果。李卫对自己推荐贾士芳一事颇为得意,没有什么比治愈帝王疾患更易邀宠,但他显然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消息传递的速度。帝国疆域如此广大,以至于任何一条消息从京师传到地方都需费数日,而朝堂政事朝夕变化,从京师到李卫所在的杭州衙署,一般需要20天的时间,这20天的时间,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确实就在这20天内发生了。11月5日,雍正皇帝突然颁发谕旨,宣布使他“圣躬大安全愈”的贾士芳乃是一个“胸怀叵测”的“妖邪之人”。此时距贾士芳赴京给雍正治病尚不足两月,距雍正颁给李卫称赞贾士芳疗病奇效的上谕亦不足一月,除了雍正本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贾士芳究竟因何事开罪皇帝。两月来变故的唯一亲历者,就只有雍正本人。没有人胆敢质询皇帝,所以,这道上谕既是皇帝的一面之词,也是对此事的唯一解释。
在这份后来被编入“不”字号,也就是不许刊出的上谕中,雍正声称早在一年前就因其弟怡亲王的推荐而召见过客居京城白云观的贾士芳,因其“虚诈”“中无所有”故略加赏赐遣出。但自这次召见以后,雍正就感觉圣躬违和,而举荐贾士芳的怡亲王也病势加重,最终不治去世。尽管从一开始,雍正就圣明烛照,识破了贾士芳“挟其左道邪术,暗中播弄”的险恶嘴脸,但是在贾声称长于疗病之法后,雍正仍决定把这个危险人物留在身边,为其调治。
按照雍正的说法,贾士芳“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还将一种密咒教给雍正,使雍正在试行之后“顿觉心神豫畅,肢体安和”,而雍正也对贾士芳“深为喜慰,加以隆礼”。
雍正承认,经过贾士芳一个多月的治疗,自己身体确已大愈。而恰在此时,贾士芳露出了其凶险邪僻的一面——他居然利用邪术将皇帝健康把玩于股掌之间:“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致令安与不安之时,伊必预先露意”。更令雍正愤懑的是,贾士芳居然大放厥词,在念诵咒语时竟声称“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故意“诈露有先天而天弗违之意”。
雍正对贾士芳的最后一项指控,是他的左道妖术已拂逆天意,导致天降灾祸——就在这一年的9月30日,京师发生地震,雍正此时恰在圆明园乘船游乐,泛舟水上逃过一劫,对此,雍正的解释是,上天因为他任用妖人而用地震加以告儆,又因其长久以来替天行道所以护佑他毫发无伤。而贾士芳,这个“市井无赖之匹夫,狗彘不如者”,正是引发这场地震的罪魁祸首。
在上谕的最后,雍正的愤怒已经出离理性变成了一连串的切齿谩骂。尽管依刑律所定,此案当交三法司同大学士会审拟定判决,但雍正已以明确意志干预了司法的最终裁断:“若伊之邪术果能操祸福之柄,贻患于朕躬,则伊父祖之坟茔悉行掘发,其叔伯兄弟子孙族人等悉行诛戮,以为异常大道之炯戒。”
而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一句,雍正突然笔锋一转,为他所深信的宠臣李卫开脱:“李卫不必以此抱歉于中,天下之人亦不得以此议李卫之失人也”——李卫的举荐失当的罪责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
法律机器在雍正的催逼之下以异乎寻常的效率高速运转,由于皇帝已对贾士芳的处置做出如此明确的指示,所以会审臣僚只需秉承上意即可。不到一周,臣僚便做出最终裁决:贾士芳本人以大逆罪凌迟处死。贾士芳的眷属中,男子十六岁以上皆处以斩首,十五岁以下并母女妻妾皆给付功臣家中为奴——这不过是皇帝那道切齿上谕的法律版而已。
但雍正再一次出人意料地展示出为君者恩威不常的一面,在怒称要对贾士芳株连九族的六天后,皇帝却决定法外施仁,宽贷贾氏一族,只是将其监押,严加看守。至于贾士芳本人,却仍难逃一死,但改为仁慈的斩首之刑——对居上位者而言,予生抑或予杀,一如贾士芳是“神仙”还是“妖道”一样,不过是一张纸牌的两面,而转死为生,由神变妖,如此翻覆巨变,亦不过片语间事耳。
我是传奇
贾士芳在刑场上,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此时是1730年11月11日,就像每一个行刑杀人的日子一样,在被民众围观品评一番之后,随即便在坊市悠悠众口间渐被遗忘——帝国国祚如此长久,足以将任何奇哉怪也的事情消解于无形,“神仙”贾士芳的传奇故事不过是帝国交响曲中一个走调的音符。只是它的尾韵拖得长些而已。贾士芳死后不足一月,另一位名唤娄近垣的道士又被雍正召进宫来,以驱散贾士芳缠绕未尽的“余邪”。在经过了一系列仪式和法力的较量后,贾士芳对皇帝最后的威胁也涣然冰释了,“朕躬悦豫,举体安和”,这句曾用来称颂贾士芳奇术的赞语,再次被安到娄近垣的身上。娄取代了贾的位置,但他足够幸运地一直得到雍正的恩宠,被封为“真人”,并且成功地活过了那位阴晴不定的主子。
贾士芳的余孽也被有计划地遗忘,所有关于贾士芳的档案,包括上谕、奏折和记录都被一一封存,不得刊出。唯一可能将贾士芳从遗忘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就是坊间的好事文人,但在他们的笔下,贾本是个得道高人,深通易理,有预知因果未来之能力,倍受世人尊崇。他本可位列仙班,却倚仗法术,自甘堕落,终于被皇帝洞破其奸,及时诛戮,以防这名“妖人”继续祸害人间——“贾既伏诛,天下称快……天威独断,诛不逾时,能哲而惠,虽尧舜何加焉!”
贾士芳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书中,是在他被斩首三年以后。三年前的往事再次涌上雍正皇帝的心头,他降谕河东总督王士俊,要其如实查报被羁押的贾士芳眷属如今情形如何。王的覆奏中称贾的三个孙子只是在家读书,对其祖的悖逆行为一无所知,而其他人也是安分守己。言下已有开脱之意。雍正的批复很快回来——谕令将贾氏眷属悉行释放。
王士俊的奏折和皇帝的上谕都没有收入史官编订的雍正一朝《实录》之中,大抵史官认为此事与国事民生无关紧要,实在不值得浪费笔墨了。